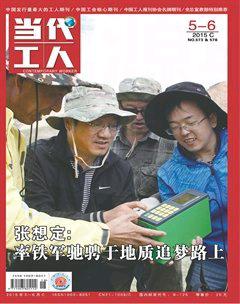陌生人成為壞人的邏輯
楚云
在很長一個時期,我們常聽到對孩子這樣的訓誡:出去要注意,別搭理不認識的人。社會、老師、家長的腔調都是如此。這樣一種內容的訓誡在1998年那個流星雨的晚上,北京一女孩被害后,更是甚囂塵上。它的積極效果顯而易見,讓少不更事的孩子多一些自保意識;負面效應也很明顯,陌生人都是壞人,至少在沒認清他是好人前,應該把他當成壞人。
許多人可能都忘記了,那是1998年11月18日凌晨3時許。
14歲的少女馬某和堂弟到家附近大操場看流星雨,被一手提黑色橡膠警棍的陌生男人攔截。這個男人以檢查為名,讓馬某的堂弟回家去取學生證。堂弟被支走后,這個男人說要先行檢查,帶著馬某來到高碑店興隆莊片林公園,欲行不軌,遭馬某反抗。這個男人持橡膠棍猛擊馬某面部,狠掐脖頸,并撕下她的背心塞進她嘴里,然后猥褻。馬某因窒息死亡。
在傳媒盡可能多地把刑事案公之于眾的年代,在家長唯恐自己的孩子會成為某個刑事案受害者的恐懼中,陌生人不可避免地要等于壞人。
應該說,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都無法杜絕犯罪,任何一家媒體都不可能不登載這方面的新聞,這是現實,也是常理。不知這種現實和常理在其他國家和地區生發出了什么樣的續聞,我們只知道,在我們國家,就在這幾十年中,這種現實和常理至少推演出了“陌生人等于壞人”的結果。
這一過程或許應該是這樣的:也許我們國家的犯罪率照比有些國家和地區不是很高,但發生在某一地血淋淋的案件,足以使全國人民驚悸,尤其當這個案件中的受害者是孩子時,這種驚悸在家長心中,就更是呈指數增長。在計劃生育國策下,我國很多家庭幾乎都是父母加獨生子女結構,孩子的安全是家長最大的憂思。當別的孩子受到傷害,甚至失去生命,家長不得不把目光投到自己孩子身上。但是孩子不能時時都在家長的視野之中,保護方法窮盡之后,家長們所能做的,只能是一遍遍地告訴孩子:不要搭理不認識的人。其邏輯是:我們無法斷定他是一個好人,但為了安全,我們可以先假定他是一個壞人。陌生人等于壞人的結果就此產生。
對此,我們感到無奈,也感到悲哀。我們不愿意,尤其是不愿意孩子們生活在“陌生人等于壞人”的現實里,但我們又能做什么呢?無非是持續地向孩子重復這個邏輯而已。這樣一樣,孩子的安全也許會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但他們的心里,就此也就存下了“這個社會陷阱密布,陌生人都是壞人”的潛意識,并將影響他們一生和對這個世界的看法。陌生人等于壞人后,社會該有多恐怖,絕非一兩句別一種訓誡能挽救得了的。
我們不愿意這樣教育孩子,我們又不能不考慮孩子的安全。怎么辦?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