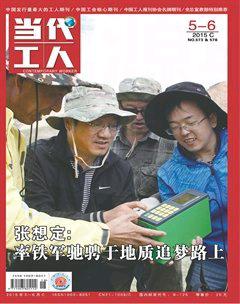減輕噪音,人人有責
胡文輝
從個人自由的立場,噪音問題的性質,可以歸結為對他人擁有安靜空間的權利的侵犯。但問題的復雜性和特殊性在于,這種侵犯客觀上幾乎是無可避免的。
在理念上,我們首先要承認,每個人都應擁有聽覺權利的私有空間,或者說應擁有獨立的、不受侵犯的聽覺空間。但在實踐上,聲音的物理性質決定了,它作為個人行為的延伸,無法像個人行為本身那樣可以自限于權利邊界之內。個人行為所造成的聲音,比如私宅中的影音、寵物吵鬧、裝修,比如開放性公共空間中的汽車喇叭或防盜器、廣場舞、爆竹;比如封閉性公共空間(公交、地鐵、電梯、公廁、餐館、會議室)中的喧嘩、手機通話、玩游戲、兒童吵鬧,幾乎總要超越個人所應有的聽覺空間,總要輻射到他人所應有的聽覺空間。而一旦如此,我之聲音,就成為彼之噪音了。
同時,這種侵犯又是互為性的、雙向度的,不僅個人總會侵犯他人的聽覺空間,個人的聽覺空間也總會被他人侵犯。一句話,在聽覺上,我們無法不逾邊界,我們必然會相互侵犯,聽覺的相互侵犯可以說是我們生活的常態。我們各自造成的聲音,必然會成為彼此的噪音。
我以為,還可以由此進一步申論:個人的自由,在現實中難免會侵害到他人的自由;個人行為或個人行為的后果,客觀上總會溢出其權利邊界,幾乎無人可以做到絕對不侵害他人的權利空間。
在此意義上,所謂“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為界”,很多時候是無從落實的。這可以說是“群己權界論”的困境,甚至也是自由的困境。這就意味著,穆勒、嚴復將自由定義為“群己權界”,在觀念上不論如何正大如何精辟,其可操作的范圍卻是有限的,現實總要比理論復雜得多。
一項行為或事物引發的糾紛,只有當此行為或事物可以清晰地確定其權利邊界,才適宜通過法律方式解決;而聲音作為一種行為或者說行為的后果,恰恰無法清晰地確定其權利邊界,無法清晰地確定其侵犯他人權利空間的程度。因此,我們不難想象,極端化的噪音問題,固然可付諸法律或行政手段以求救濟;但日常化的噪音問題,無論從成本角度還是從執行角度,都不易依憑法律或行政手段去應對。也就是說,在理論上個人雖擁有維護安靜空間的權利,但在實踐上個人卻難以采取有效的強制手段以保護這一權利。噪音問題固然可以歸結為權利問題,卻不能僅依賴捍衛權利的方式來解決。
我想,噪音問題是無法根除、只能減輕的,而歸根結底,最有效的方法無非是最簡單的方法:作為個人,我們在行使自身的權利時,也要設身處地,尊重他人的權利;只有養成自律的意識,盡可能減少對他人權利空間的侵犯,才可能最終減少他人對自身權利空間的侵犯。易言之,噪音的應付之道,不在法律,而在倫理;不在短期的手段,而在長期的習慣;不在強調個人權利,而在提升個人素質。最重要的是我們彼此的尊重,彼此的體諒,彼此的自律。作為噪音的施者,其行為的力度應盡量減輕,時間應盡量減短;而作為噪音的受者,也應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他人因自由行為而造成的聽覺侵害——畢竟,這種侵害與容忍是相互的,我們每個人都同時是侵害者和容忍者,我們也會侵害他人,我們自然也得容忍他人的侵害。
比如,具體到放爆竹的問題,我的意見如此:放爆竹作為一種越來越“少數派”的權利,確實侵犯了“沉默的大多數”的權利,放爆竹者很應當注意時間和地點,以減輕對他者的干擾。但另一方面,放爆竹作為一種傳統,即使不是一種好傳統,也不過是一年一度的放縱,厭煩爆竹者是不是也應忍讓一時,尊重一下這種“過于喧囂的孤獨”的權利呢?
關于噪音問題,去年有兩本翻譯過來的調查報告:一本是贏得書評人力捧的《一平方英寸的寂靜》,屬于環保主義性質,主要針對噪音對自然界的破壞;另一本是似乎無人喝彩的《噪音書》,屬于社會問題性質,更關注噪音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在我,更認同后一本書的取向。我覺得,追求大自然的寧靜,是過分奢侈的理想。我的期望,只是降低人世間的喧囂,贏得最低限度的城市寧靜而已。
人類已經太多了,我們只能生活在“擁擠社會”之中,個人是無法置外于人群的。就形而上的意義來說,我們各有各的權利,各有各的安靜空間。但究其實,我們個人的安靜空間其實是錯雜地鑲嵌在一起的,我們擁有的不如說是同一個安靜空間。若想獲得一個屬于個人的安靜空間,取決于擁有一個屬于所有人的安靜空間——只要一個人的任性,就可以破壞屬于所有人的安靜空間;而非得所有人的自律,才可能維持屬于個人的安靜空間。“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多少只是修辭,但在噪音問題上“匹夫有責”就絕非虛言了。
如果說,在商業領域,所有人的自私可能造就一個繁榮的社會(這一點其實也頗有人質疑。事實上,英、美的經濟繁榮都得力于“看得見的手”,并非完全憑借“看不見的手”);但在生活領域,所有人的自私只會造成一個災難的社會吧。
如此,抵制噪音,保有安靜,出發點是個人權利問題,但最終要歸結為個人責任問題。這似乎是個悖論。但實際上,自由問題總是如此的。權利作為一種價值終有其止境,人與人的關系,共同體的秩序,是無法僅通過爭取權利的方式來維系的。沒有責任,也沒有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