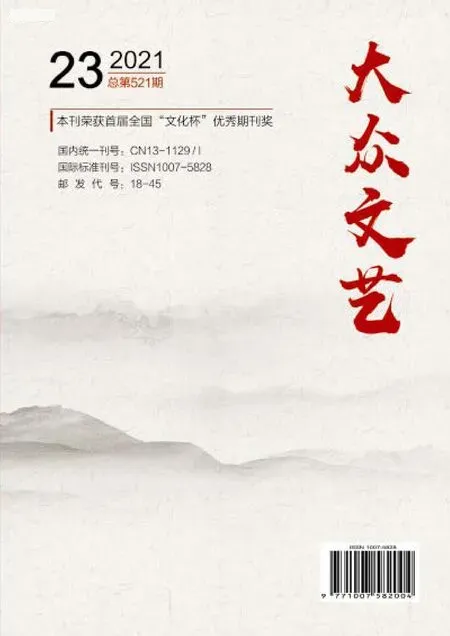中國古典悲劇的哲學觀照
董霖鐘 (寧夏司法警官職業學院 750021)
中國古典悲劇的哲學觀照
董霖鐘 (寧夏司法警官職業學院 750021)
閱讀中國古典悲劇的時候,我們能得到這樣一點:處在審美觀照的時刻,讓我們對悲劇產生快感的不是所謂的應用于悲劇的“心理距離”,而是沉浮于悲劇之迂回曲折、滌蕩出內心無限靈感氣韻,使心靈通暢,對生命肅然起敬。這是中國古典悲劇的哲學觀照。具體表現在道德同情、詩化之境與大和精神三個方面。
悲劇;道德同情;哲學觀照
戲劇本為歷史的鏡子,但悲劇卻是歷史的傷疤。演悲劇,恰如揭示歷史的荒誕,誠所謂現實荒誕,所以藝術才有可能比現實更荒誕。直到人們把悲劇改作藝術來欣賞的時候,或才讀懂了悲劇在歷史中的意義。寫悲劇的人其實是怕悲劇的人,悲劇家總是不愿意見到有一樣的悲劇在現世發生,盡管他們曾經是以多么大的內心“邪惡”來窺視靈魂和估價浮世,但當觀眾幾番走進或者離開劇院的時候,悲劇家卻孕育著比任何人要強大的焦慮和期待。這樣一來,悲劇藝術就不僅成為了歷史的、社會的觀照,而是更加重要地成為了靈魂的觀照。閱讀中國古典悲劇的時候就能得到這樣一點:處在審美觀照的時刻,讓我們對悲劇產生快感的不是所謂的應用于悲劇的“心理距離”,而是沉浮于悲劇之迂回曲折,滌蕩出內心無限靈感氣韻,使心靈通暢,對生命肅然起敬。這是中國古典悲劇的哲學表達。具體來說,主要表現在道德同情、詩化之境與大和精神三個方面。
一、道德同情
作為文藝出現的悲劇一定是道德的產物,它的出現本已賦予了人世間以深廣的同情心。而中國古典悲劇就此表現得又尤為突出。當善良走向毀滅的時候,邪惡就會橫行于世。此時,悲劇如同如同醒世清鐘,喚醒世人。悲劇家的作品便有了對世人精神困惑和情感困惑的道德同情,以此治療現實中的絕望和精神上的迷茫。因此,中國古典悲劇的欣賞著也自覺不自覺的被道德同情所包圍。
中國古典悲劇中的道德同情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來源于悲劇家的同情悲憫之心,另一方面來源于觀眾的悲苦情結。悲劇家的創作也是目的性明確的創作,他們將目光投向廣闊的社會歷史,體驗在艱難困苦的絕境中求生的糾結,并將其在煎熬的內心里形成生命經驗。當他從生命經驗中走出來的時,如同經歷了生死劫難,體悟的全是生命的偉大與高貴。人格經過悲劇藝術的升華呈現為悲劇人生的壯美。很顯然,悲劇家深厚的道德同情溢于整個悲劇之中。然而,一旦談及大眾的悲苦情結,卻有不少理論家質疑悲劇的道德同情,甚至認為悲劇審美中存在幸災樂禍的惡意,展現著人類惡劣的品性,喚起欣賞者的優越感。針對上述問題,朱光潛先生在他的《悲劇心理學》一書中進行了精彩的反駁。令人遺憾的是,朱先生在回答悲劇快感因由問題時,將道德同情拒之門外。朱光潛先生說:“在悲劇的欣賞中起重大作用的,是審美意義上而非倫理或道德意義上的同情”“道德同情常常消除距離,從而破壞悲劇效果”“我們欣賞悲劇時常常體驗到的是審美同情,不是道德同情。道德同情由于與悲劇行動的動機和趨勢相抵觸,往往不利于悲劇的欣賞”。1其實并非如此,且不說悲劇本身傳達的文化價值和歷史意義,單就觀眾功利性的審美情趣來說,超功利的理想化審美是不存在的。悲劇欣賞時,人們產生的快感歸根到底來源于道德同情而不是其他方面。
我們常常要被悲劇的情節所打動,心靈就會跟著迂回曲折的故事一起沉浮,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我們自由面對悲劇之時,心中充滿對生命的敬畏與同情,正是道德同情讓我們敞開自己的心扉,走進別人的心靈,體驗別人的世界。從這個層面上而言,中國古典悲劇的創作能從道德理想出發,恰巧是迎合了悲劇欣賞者的審美需求,進而才可能使悲劇藝術的審美價值最大化。正如《竇娥冤》里廣為傳吟的唱詞:“有日月朝暮懸,有鬼神掌著生死權。天地也只合把清濁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盜跖顏淵:為善的受貧窮更命短,造惡的享富貴又壽延。天地也,做得個怕硬欺軟,卻原來也這般順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為地;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哎,只落得兩淚漣漣。”2在這滿含淚水的傾訴中,道德同情凸顯出中國古典悲劇的精神品格,塑造了一個個經典作品,深入人心,植入骨髓。
二、詩化之境
詩化藝術在中國古典悲劇中起到了音樂一樣的美,相應的,詩化之境成就了中國古典悲劇最為獨特的美學氛圍。說詩化,是指由詩化語言引起的悲劇情景的詩化。而應用到悲劇中間的詩化語言,又往往回旋往復、一唱三嘆,其旨意多為詠嘆人生無常,韶華不再,來日無多。所以更能引起悲劇欣賞者對人生命運與生命意義展開新的咀嚼和審視。如此一來,悲劇的意義也就突顯了出來。
詩化之境在中國古典悲劇中恰如夕陽挽歌,秋風落葉。飄灑之間營造著精神的曲折:在衰朽處獲得人生前進的力量。李商隱的一句“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紅燭賞殘花”,朱良志先生做出了精彩的解釋:“殘花雖衰敗,它仍然是花,它是最后的花,就要消逝在永恒的寂寞之中,所以詩人‘更持紅燭賞殘花’,是一種含淚的欣賞,是走向終極之時對自己生命傷痛的絕望撫摸。殘花作為一個最后時間之意象,將過去、現在和未來聯系在一起,詩人正是在這時間之流中審視現在的‘存留價值’。李商隱的‘更持紅燭’似乎是一生命的祭儀,在這祭儀中,詩人頑強的‘賞’表現了與那股將生命推向衰朽的力量的奮力抗爭,展現了人與時間的極度緊張之關系”。3悲劇不正是含淚賞殘花的詩化之境么?詩化之境,作為藝術的鍛造,讓我們感受到的不在于所謂的悲極泣涕,以為使人覺出痛感就達到了悲劇欣賞的全部目的,而是在于通過這樣一門獨特的藝術,讓我們置入一個從容自由的境界,來與生命真相照面。所以,詩化之境在營造悲劇氛圍的同時,加強了悲劇的意義。悲劇的意義是什么?就是在結束觀看、走出劇院的時候,我們再也看不到了真正的悲劇。
詩化之境在中國古典悲劇中體現出的是詩歌的力量,是由詩之觀照走向了哲學的觀照。就此,可以以馬致遠的《漢宮秋》為例。《漢宮秋》本如一首長詩,期間不乏膾炙人口的佳句。譬如一句“誰承望月自空明水自流,恨思悠悠”,4月自空明、水自流,斯人已去,獨留一窗寂寞,與誰共言?詩化之妙就妙在讓詩歌意象來替悲劇說話,打通了現世時間與空間的障礙,拓展了悲劇欣賞者的心靈空間,使之悠然進入一派詩化之境,從而冥想到人生跌宕起伏,生命之故于胸襟間迂回曲折。像“胡地風霜”“關山鼓角”“斷腸柳”“送路酒”等意象,都如一葉扁舟,渡悲劇欣賞者之心追向生命之岸。再如一句“他部從入窮荒;我鑾輿返咸陽。返咸陽,過宮墻;過宮墻,繞回廊;繞回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黃;月昏黃,夜生涼;夜生涼,泣寒螀;泣寒螀,綠紗窗;綠紗窗,不思量”,5往復回旋,境界高妙,意味悠長。《漢宮秋》末尾處又引入了“孤雁”的隱喻,“尤其是用孤雁哀鳴的描寫,更是雙關式地表現了漢元帝孤獨失落心境。窗外一孤雁,房內一寡人,一個哀鳴不斷,一個嘆息不止,這孤雁是昭君?還是昭君似孤雁?頗如‘莊生夢蝶’,雁叫聲中,景境越濃,心境越深,達到一種‘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其出口’的有意境的高度。”6其實都是借詩化之境的妙造,來使悲劇欣賞者更好地把握悲劇精神。
三、大和精神
中國古典悲劇的大和精神是不言自明的,它透露出的不僅是悲劇家作為歷史見證人而具有的審美理想,更是一個苦難民族理想化的精神出路。有不少理論家就此做過深入探討,結論不外乎兩種:一是認為中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悲劇,大團圓的“尾巴”大大消弱了悲劇的力量,并且使得中國古典悲劇開始走向喜劇;二是認為大團圓結局對中國古典悲劇精神有強化作用。其實后者抓住了中國古典悲劇的美學本質,悲劇審美的終極價值就是培養吾人存在的力量,更志于培養一個時代民族的精神信仰。大和精神,作為一種宇宙意識被運用到中國古典悲劇中的時候,正如含淚的微笑,是在悲劇收場之時祛除悲劇欣賞者心靈陰霾,還愿與肯定一個應然的生命理想。所以,中國古典悲劇的“尾巴”非但沒有消弱悲劇的力量,反倒是增強了悲劇的歷史使命感與時代價值。不僅中國古典悲劇如此,中國書法、繪畫等其他藝術也一樣,都致力于挖掘蘊藏在生命深處的蓬勃無盡的氣韻,這是中國藝術的智慧。
在中國哲學里,生命的最高境界莫不歸于“和”。和者,圓融無礙,全然一個至善至美的境界。用“和”來為悲劇作結,埋伏于期間的便是對廣大自由之生命的向往。“慘烈”與“死亡”等本身只作為悲劇的符號而出現,當悲劇在一片蕭殺的沉寂中結束的時候,我們何嘗不是在對悲劇做另一番斷想?而“和”,恰是為我們的斷想做了一回向導。更何況,中國古典悲劇歷來都背靠著它的歷史主題,在庸臣誤國、黑白顛倒與是非不明的專制社會,無論是悲劇家還是悲劇欣賞者,確真都在以理想化的悲劇效果來消解現實悲劇所致的莫大陣痛。中國古典悲劇是時代悲劇的藝術化,它的悲劇效果首先屬于它的時代。所以,我們在探討一個文化系統中悲劇之藝術結構是否成立的時候,還不能忽略一個民族的歷史特點。“真正中國悲劇的大團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現實世界的延續和發展。在這個延展的世界中,不但悲劇沖突還在繼續發展,而且悲劇人物的反抗性格也在深化和豐富。因此,真正的中國悲劇的大團圓對于中國悲劇來說,既不是強弩之末,也不是‘俗套’,而是中國悲劇的內在主題的完成和深化,是中國悲劇精神和境界的強化和提升。”7
大和精神是對中國古典悲劇的撫慰,或者更像是對中國歷史悲劇的撫慰,包括撫慰悲劇家自己和他的時代的一切觀眾。譬如洪升的《長生殿》,“他已經表露出深深的大廈將傾的危機感,而為這個無可挽回的墜落的夕陽唱著如訴如泣的無盡的挽歌,并且想從一片廢墟中尋出一點希望的曙色,從而走出失望與懷疑的泥淖,逃避著最終陷入絕望的命運。這種失望和懷疑的悲劇性在于,人無法阻止自己而又難以接受眼睜睜地看著自己心中原本美好的東西被一點點地敲碎,撕裂”。8或者在他的《長生殿》中,洪升已經找到了精神出路。
注釋:
1.朱光潛.悲劇心理學[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8):58,69.
2.4.5.王季思主編.中國十大古典悲劇集[M].濟南:齊魯書社.1991 (9):20,52,56.
3.朱良志.曲院風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3):132-133.
6.8.葉桂剛,王貴元主編.中國古代十大悲劇賞析[M].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3(6):114,1567.
7.熊元義.中國悲劇引論[M].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7(8):51.
董霖鐘(1963.10- )男,陜西華陰人,寧夏司法警官職業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漢語言文學、語文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