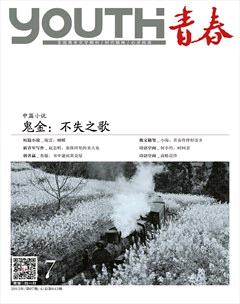書中建成黃金屋
魯敏
一、前傳
性格決定命運。留著一把大胡子的繆炳文,從骨子里,就不是一個滿足于現狀的人。
在南京大學,他學的是化學專業,這在當年,也算是炙手可熱的實用專業。如果他愿意跟當年大部分的同學一樣按部就班地進入人生軌道,今天,他應當在一家化學研究所里終日與試驗數據為伍,或是成為某個化工廠分管業務的頭目。
但歷史已被覆蓋、被改寫,這是繆炳文性格中不安分的因素使然,是風起云涌的時勢使然,是天欲降大任的機遇使然——也可能沒那么玄乎,一切只是源自某一瞬間他頭腦中不經意閃過的念頭,卻如閃電劃破天空,生成了一個最驚人的化學裂變——而今的繆炳文,已是鴻國文化產業有限公司的總經理,大眾書局的董事長,首屆“南京市十大文化名人”。與化學離題萬里,他以一名民營文化產業先行軍的身份知名于世,并成功打造出了“中國民族書業二代品牌”——大眾書局。
一個人,其體質源自他的食物,其氣質源自他的閱讀,其運勢,則源自他所有留下的足跡。我們來看看,在2002年12月之前,在創立國內最大民營書城之前的繆炳文,曾經走過怎樣的一條羊腸小道或陽關大道?
1988年,剛剛進入社會的繆炳文成了一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國家海洋局東海分局,工作待遇很不錯,出差一天可休息一天,一同畢業的同學每個月只有80多塊,他的收入已經有三四百了,相當于現今的外資小白領。
但這種溫飽安逸、風平浪靜、一眼可以望到頭的生活顯然不是繆炳文的理想。不久后,在眾人不可理解的目光中,他離職去了海南。海南其時剛剛建省,尚處在滿目荒痍、萬物待興的起步階段,繆炳文與伙伴們在那里自得其樂,做做業務、辦辦報紙、交交朋友,既帶著純真的文人氣,又初步體驗到弄潮商海的迷人滋味。但等到1991年底,當海南省已成為全國人民盲目向往的淘金熱土時,繆炳文卻又反其道而行之,重新回到南京大學,到科技開發研究院重新干起了科研。
“這樣的選擇自己也很難解釋得清,也許是偶然,也許是必然。”繆炳文如是說。
但機會不會錯過有準備的人,正如命運總垂青于智慧的頭腦。在南京大學的四年間,他給同事的印象似乎總是不安分的,業余時間,總見他四處游走、忙碌不停,像在對自己的綜合能量進行一次自我測試,像拉伸一根彈力繩,看看其長度與強度、深度與廣度。
四年之后,一切有意無意的經歷開始顯現出初步的結果:他與另外兩個伙伴創立了美麗華實業公司,主營“千百度”女鞋。
1995年,這是生命中值得劃上刻度的重要年份,繆炳文,從書生一變而為商人。
從物理角度來看,他還是他,可能只是體形稍胖,胡子稍亂;但從化學角度來看,顯然,這可以算得上是一次質的飛躍。人生從此別樣天,在沒有人注意到的內心角落,他是躊躇滿志的,更是如履薄冰的。
此后六年多的時間,三個伙伴同心同力,建生產基地,上生產線,成立精英設計中心,建成工業園區。2003年6月,鴻國國際在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主板成功上市,成為南京第一家海外上市企業——像拔河一樣,他們一步步把成功的長繩從彼岸拉到了此岸。
這一期間,繆炳文的運轉曲線是一個商人的典型寫照,決策與跟進、競爭與合作、叛逆與妥協、風險與收益、資本積累與擴大再生產……所有的摸滾打拼、跌宕起伏,他均身臨其境,對于百貨零售、對于企業管理、對于多元化發展、對于市場戰略定位,繆炳文開始慢慢摸索出一套成熟的思路。
時間到了2002年年底,來自物質的、心理的、理念的,所有的鋪墊與積蓄已如水到渠成,“大眾書局”,在這個時候,像一粒種子一樣,開始進入了前途未卜、詭譎多變的孕育期。作為這粒種子的播撒者與培育者,繆炳文開始邁出了他涉足文化產業領域的第一小步。
二、正史
南京新街口,全國知名商業中心,吃喝玩樂、物質華美;熙熙攘攘、利來利往。這樣一個紅塵萬丈的喧囂之所,到底還缺點什么?或許是讀書人的天性在潛意識里作怪,或許是商人智慧的靈感突至,或許是對精神家園的暗中渴求。2002年底,經過第N次的市場調研,繆炳文確立下“錯位經營”的總體思路:做文化,做圖書。
從鞋業的“行萬里路”,到圖書的“讀萬卷書”,這僅僅是一種純商業性的巧合?還是命運之手在暗中推波助瀾?沒有人能說得清楚。
但此方案一出來,就遭遇到了眾多業界同仁的善意勸阻:做圖書,吃力不討好,周期漫長,十有九賠,別的不說,就連國營一字號新華書店,雖有強大后臺支撐及免房租、好市口、主渠道等一些利好背景,其結果仍然是青燈微照,收益薄微乃至“正當虧損”;再說現在是網上閱讀時代,又是物質崇拜時代,精神消費已成奢侈品。大趨勢在此,你繆炳文明知其深淺,偏偏還要趟進這條河流,弄不好會把數年英名毀于小小圖書呢!
但繆炳文自有其思路:天生萬物,有其短,必有其長。從尋常意義上講,圖書似是窮途末路,但一個市場在長期壟斷之后,其競爭力必將有所削弱,其思維與模式難免有所僵化。而弱點就是增長點,就是無量的商業上升空間。
此種背景之下,以民營身份進入圖書業,乍看可以說是無知者無畏,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實質上,是知其短、攻其弱,是知其可為而為之。再說,繆炳文心中有一組數據,當年,中國一年的圖書零售總額為800億—900億人民幣,但在德國、美國這些出版業發達的國家,僅一個大型出版機構銷售的圖書總額就是中國全部市場的2—3倍。可見,中國圖書零售市場未來的發展空間相當可觀。
2003年1月1日,南京書城(大眾書局前身)正式開業,其超過7000平方米的單體獨立書城和3000平方米的綜合區域創下了國內民營書店的面積之最。當時南京雖有1000多家書店,但大都是“小舢板”,航空母艦式的南京書城一下子脫穎而出,立刻引起了全國業界的關注。
引起關注的,還不僅僅是體量上的大與巨,還有董事長繆炳文的全新思路,這也許得歸功于他多年的零售業經驗積累以及開放式的市場理念。繆炳文給自己的圖書經營定下一個調子:把圖書做成商品,把商品升華成文化。
別看這簡簡單單一句話,卻創新出了不同的風暴。
創新一:在書店中開設“店中店”
長期以來,書店的排列布局都是按照“中圖法”的傳統分類法進行店堂布置,雖然科學嚴謹,但缺乏應有的個性與風格。這一方面,擁有高級發行員資歷的繆炳文,從讀者的消費角度打破了這一視角,他大膽創新,突出風尚與流行,突出個性化,突出消費主體,在書店中打造“店中店”,派生出諸如“女性書店”、“旅游書店”、“生活書店”、“工具書書店”、“經濟書店”等類別型專柜,引導和方便消費者在相對集中的區域內選購自己所需的產品。
這一源自零售百貨業的做法在店堂甫一亮相,即贏得了碰頭彩,長期以來被忽略掉的主體意識突然被如此體貼地照顧起來,讀者無不感到耳目一新,購買欲也就順勢水漲船高起來。
創新二:借鑒百貨業營銷理念
長期以來,書店便是賣書,這似乎是千古一條道走到黑了,但所謂突破與創新,也僅在一念之間、在一墻之隔,繆炳文伸出他的手,輕輕推倒了這堵約定俗成的墻。
從南京書城(大眾書局)開門第一天起,他就開創了一個“文化百貨”的理念,全方位引進各類與文化相關的零售百貨,做成一個“culture mall”。此舉的確如春風撲面,教育資訊、人才培訓、軟件產品、電腦賣場、動漫體驗、旅游產品、電子數碼、數字閱讀、品牌咖啡、茶文化、眼鏡等無一不可,只要與文化消費有關,統統召入麾下,引入了少兒手工館、游樂場、玩具館、KFC等,并配有英語角、韓語角、抄書臺、休息區、閱讀島及經典電影回放等綜合休閑區域——就像一個高明而狡黠的大廚,將教育、閱讀、娛樂、休閑等統統揉成一個大面團兒,再做成一只只精致美味的點心,捧到面前,一家幾口,可各取所需。不同人群的文化休閑都可在這里得到“一站式”的滿足,感受傳統文化與都市趣味的流通與互補。
創新三:周邊衍生平臺
圖書是商品,更是有溫度有氣質有生命力的文化。作為文創產業的先行軍,繆炳文夢想著要為水泥森林中的都市人構建一塊萋萋家園!以書為圓心,大眾書局畫了兩個大圓,先后開設了“大眾夢幻劇場”和“大眾講堂”。
“大眾夢幻劇場”名字叫得夢幻,先后推出的活動也充滿了魔力。2004、2005年,劇場分別邀請了中央芭蕾舞團、西班牙皇家樂團來南京獻演,為南京人送上了高品質的文化演出。2006年7月,還通過全國選拔大學生演員、群眾演員,將都市漫畫《澀女郎》改編成現代話劇,轟動了南京話劇界。
相對而言,“大眾講堂”則更為貼近百姓大眾,力爭讓每一位讀者都可以通過這個課堂走進更為立體的閱讀世界。這些年,“大眾講堂”先后開展過“女性讀書沙龍”、“關注孩子成長”、“學術大師講座”、“金秋謝師恩”、詩歌大賽、“企業家讀書會”、“出租車英語培訓”等活動,而設在廳堂內的“藝文空間”多功能室,更成為一個面向會員和社會的公益性文化沙龍,講座、展覽常年不斷,打造了大眾書局“視、聽、味、觸、嗅”五覺享受的藝術空間。
創新四:“逆市”更名
繆炳文一向堅信,“只有不好的企業沒有不好的行業。”雖然圖書經營的確存在投資回報周期較長的問題,但通過多種文化業態的引進,可全面分擔經營成本,取得多贏效果。但一個現實的問題接踵而至。原“南京書城”的品牌雖已廣為人知,但有地域限制,不適于連鎖開拓,且放棄已經成熟的“書城”品牌雖然意味著無形資產的損耗,似是“逆市”之舉,但長痛不如短痛,有舍才有得,這也是區域品牌走向全國化的必要成本。
為此,繆炳文先后找過北京、上海等多家書店,多番尋覓,都沒有合作成功。就在焦慮之時,他們突然注意到一個沉寂多年的老字號:大眾書局。這曾是民國時期中華書業的老字號之一,但后來流失了。他們當機立斷,立即在國家工商總局進行了商標注冊,搶下這個古風猶存的金字招牌——可謂鴻國最得意的“快手筆”——并迅速以細胞“繁殖”般的活力與速度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大規模的擴張。
在每一個城市的連鎖店,大眾書局都會邀請一流設計師設計,本著“連鎖而不復制”的原則,整體格局上追求歐洲圖書館風格,并兼顧地區文化差異,每個店在主題、材質、色彩運用上略有不同。這些用心良苦的細微之處都得到了當地讀者的熱烈響應,書城每開到一處,即迅速成為當地的文化活動中心和都市文化新坐標。
以南京為例,國貿大眾書局便是新街口的絕對地標,一些“80后”、“90后”更是笑言:“多少年了,每次約路癡、臉盲,接頭暗號都是:我在大眾書局門口等你!”正因為此,2013年10月31日,大眾書局國貿店搬至附近的國藥大廈,雖然新舊店之隔步行僅需十分鐘,但還是在全城引發了一場洶涌的懷舊潮——大眾書局在南京人心中的影響力可見一斑。
真正令人心悅誠服的是這些創新模式在盈利上的實戰力。開業后,南京書城年銷售額節節攀升,第一年站穩腳跟,第二年即在全國優秀大型書店中占有一席之地并開始進入良性循環。2004年,南京書城被江蘇省委宣傳部主編的《江蘇文化產業藍皮書》作為個案研究,也是唯一一個民營企業入選其中;同年,才兩歲的南京書城還當選為中華全國工商聯書業商會副會長單位。2004年,大眾書局獲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批準的“書報刊及電子出版物國內總發行權”。2005年,大眾書局又獲“全國性出版物連鎖經營許可權”。
這樣,大眾書局成為江蘇省內首家同時獲得“雙權”的圖書連鎖零售企業。2005年6月,大眾書局斥巨資建立了圖書自動化物流流水線,這是省內也是全國民營書店中首次引入這種流水線,其吞吐量能滿足100家經營面積在1000平方米以上、年銷售最高額達10億碼洋的連鎖店配貨需求。
三、野史
說完了創業史,讓我們重新回到繆炳文其人,除了那把較為引人注目的小胡子,抽煙喜歡用銅煙斗,一派紳士風,他的身上還有什么與眾不同之處?
這是一個鼓勵好奇心的時代,也是一個注重隱私的時代,關于他私人氣質的各種演繹,我們只能以一種野史的角度進行邊緣化的觸摸。
關于讀書
既然是做書的,不可避免的,繆炳文常常會被問起關于書的問題。
在繆炳文看來,書分長期有用和短期有用兩種,“有些書,可能在短時間里,你看不出它對你會有什么作用,但說不定哪天它又能促成你某方面的靈感,比如《禪的202個人生智慧》、比如《二十四史》,這都是長期可以陪伴在側的良師益友,每看必有收獲;而一些實用類的圖書則屬于短期有用。”不僅讀書,他本人還開始“玩”起了藏書,每月藏書百余本:“為讀,為藏,亦為了解商品,增加專業領域的競爭力。”
作為企業高層,繆炳文的閱讀中,有相當一部分偏重于管理、財務、法律、人力資源等方面,他給自己定下的“硬杠杠”是每年必讀48本圖書,平均一個月要讀4本。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時間,他喜歡在各個角落都放上書,床頭放兩本,工作室放兩本,汽車上放兩本……“只要有機會坐定的地方都有書的影蹤。”讀書已成為他融入血液的本能。
“我知道,有些企業高層會因為過分繁忙而放棄閱讀,事實上,讀書也可以理解為另一種投資。當你通過廣泛閱讀掌握一些技能的時候,在關鍵時候這些知識就能有用武之地,在生意談判上我就明顯感覺讀書作為一種投資的重要性。比如在談判初期,往往會有出奇制勝的效果:當對方談到體育的時候,你能快速地講出當前最紅的球星;當對方談到文學著作的時候,你可以把當前最暢銷的書中內容與對方展開討論。這樣不論別人談論什么話題,你都能巧妙作答,對手必然感到敬佩,那在談判桌上就掌握了主動權。”
關于困難
任何一條成功之道,在看得見的風光與鮮花之后,必定都有看不見的溝溝坎坎,在彼時彼地,如何應對困境?
“總的說來,自然是‘逢山開道,遇水架橋,最大限度地把困難給踩到腳下。幸運的是,我不是一個人在奮斗,公司的經營和管理團隊也是我最大的資本和自豪所在。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實踐證明,三人團隊是最為科學合理的組合模式,比一人兩人強大,又比四人五人團結和諧。也許,就像物理學中的三角,這是最穩定、最能夠承受外力的結構。”
“我們的事業一步步走到今天,有一些困難是大家都能看到的。比如,當年國貿中心裙樓部分的虧損,比如,剛剛做圖書時所碰到的歧視與阻力,比如,與同行及上級管理部門之間的溝通障礙等等。但還有更多的困難,是不足與外人道的,但有了這個‘鐵三角,有了強大的團隊在后面支撐,總會迎刃而解了。打個比方,就好像是,一個人走夜路,或許會害怕,但如果三個人在一起,有說有笑的,恐懼感就會灰飛煙滅。”
關于自由
提到生活中幾次重大的轉折與改變,比如當初離開政府機關到海南,比如離開海南重回校園,再比如離開南京大學自立門戶,這一系列重大的抉擇,到底動力何在?內因何在?
繆炳文的回答頗具“四兩撥千斤”的意味:“不為什么,只為追求更高的生活質量。”
那他所指的“高質量生活”又是指什么?錦衣美食?豪宅香車?非也,繆炳文進一步的解釋可能超出大家的想象:很簡單,好的生活,就是不想上班時,就可以不上班。當然,更重要的是,想什么時候上班就能上班。
這看似玩笑的回答,往深里剖解下去,其實就是一個詞:自由。
回看繆炳文前面四十年的人生,對自由元素的向往與渴望,可能已成為他血液的一種顏色。如果現有的生活,過分安逸或過分循規蹈矩或者缺乏挑戰,對他而言,都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樊籠,他就得打破它,沖出它,去投入另一個未知的空間。
有人注意到繆炳文的一個細節,在他的手掌心上,常常會寫滿當天所要辦的各種事務,相當于備忘錄,或美其名曰“掌上電腦”。
“是啊,想起什么事情了就記下來,記在報紙上,記在紙片上,記在手上,都一樣嘛,反正把事情辦好就行。形式或載體有那么重要嗎?只要方便就行。”這樣的細節,足可以一孔窺豹,看出繆炳文對形式主義、對條條框框下意識的回避。
他是一個追求簡潔的實用主義者。對他而言,生活的品質,自由的含義,外延極廣,有對機制束縛的不滿,有對程式化工作的厭倦,有對高枕無憂現狀的否定與輕蔑。
正如雄鷹。鷹擊長空,不是為了覓食,而是為了飛翔的樂趣,為了接近高遠的藍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