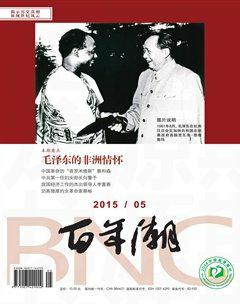功高德厚的女革命家蔡暢
蘇平
蔡暢,1900年生于湖南農(nóng)村,1990年逝于北京。漫長的90年里,她從一個普通的農(nóng)村女孩成長為一個忠誠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杰出的中國婦女運(yùn)動領(lǐng)袖,見證了中國跌宕起伏的20世紀(jì)。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創(chuàng)建歷程的參與者,她并沒有留下多少“傳奇”的故事。但蔡暢崇高的思想品德、對共產(chǎn)主義事業(yè)的堅貞不渝、平易近人的作風(fēng),以及甘為人民公仆的本色,使她不僅獲得“功高德厚”這樣堪稱完美的評價,在其生前身后更贏得了來自基層婦女普遍而真誠的愛戴。因為她用一生踏踏實(shí)實(shí)地做了一件事——開辟了婦女解放的道路,而這件事,改變了無數(shù)人的命運(yùn)。
“毛妹子”:唯抗?fàn)帲浅砷L
蔡暢,原名蔡咸熙,父親蔡蓉峰,母親葛健豪。共有兄弟姐妹四人,她最小,大家都叫她“毛妹子”。6歲,到了纏小腳的年紀(jì)。那個時代每個鄉(xiāng)下女孩“到了歲數(shù)”,都要過這一關(guān)。可是毛妹子偏偏不想“過關(guān)”,6歲的小女孩當(dāng)然不懂什么進(jìn)步意識,可是裹腳的過程無異于一次酷刑。承受不了強(qiáng)加的疼痛,她連哭帶鬧的不依。這小小的抗?fàn)幰膊凰愠銎妫畈欢嗨行∨⒍荚鵀楣_而哭鬧,可最后在家長的權(quán)威下還是要屈服。毛妹子特殊的幸運(yùn),是她有一個開明而且能在家里做主的母親,還有一個讀了書還一心向著妹妹的三哥。三哥勸說,加上母親心疼,毛妹子居然贏得了不裹腳的特權(quán)。直到老年,蔡暢還會提起這次“反封建”的勝利。她說,她從那時起才懂得女娃子要學(xué)會反抗來保護(hù)自己。
此后的9年,毛妹子一天天走上和其他鄉(xiāng)下女孩不同的道路。除了農(nóng)村勞動,她還曾經(jīng)隨著同樣日漸進(jìn)步的母親葛健豪、三哥蔡和森到縣城讀書,甚至十三四歲就在母親創(chuàng)辦的學(xué)校里成了小教員,還在體育課上帶著小伙伴們撕掉裹腳布。也許是天足讓她能走出家門更多的接觸社會,也許是第一次反抗的勝利教給她超出常人的勇敢,毛妹子的心悄悄飛出小小的雙峰縣。在三哥去長沙讀書以后,她更意識到外面還有一個更大的世界,這個世界里可能有自己更大的未來。心靈已經(jīng)悄悄地打開一扇窗,她注定不會再低下頭,去走別人的老路了。
可是15歲那年,毛妹子還是迎來了一“劫”。15歲,在中國鄉(xiāng)間已經(jīng)是個大姑娘,可以真的“放人家”(結(jié)婚嫁人)了。何況,讀書識字、品貌端莊的蔡咸熙早就是家鄉(xiāng)的小小名人。于是,父親以500大洋的代價,要把她許給一個地主家做媳婦。平心而論,這在那個年代是小戶鄉(xiāng)紳的慣常做法。不過,這個已經(jīng)讀了一些書、有了一些自我意識,滿心憧憬著未來世界的小女孩再次拒絕“慣常”,她不要和千百萬鄉(xiāng)間女子一樣,成為封建禮教的奴隸。“抗婚”,在“父為子綱”的時代,已經(jīng)觸犯到了封建倫理道德的基本原則,難度遠(yuǎn)遠(yuǎn)大于9年前的“放腳”。這一次,怒不可遏的父親不僅固執(zhí)己見,甚至不惜提刀追砍又一次支持女兒的母親。毛妹子的三哥為她指出了新的道路:“逃婚、出走、遠(yuǎn)行、求學(xué)”。那一年在母親的支持下,15歲的毛妹子沿湘江離開了故土。也是那一年,考入周南女校的她改名為“蔡暢”。毛妹子的時代結(jié)束了,蔡暢走向了新的生活。
少女時代,開眼看世界
1918年11月28日,湖南《大公報》曾有這樣的報道:“周南女校運(yùn)動會自上午九時起、下午三時止,其指揮者為該校體育教員蔡暢女士。她精神愉快,深得兒童心理……鼓掌之聲,響徹云霄。”其時,18歲的蔡暢已經(jīng)在長沙生活了三年。
蔡暢的長沙生涯并不輕松。她15歲入周南女校音體專業(yè)讀書,16歲畢業(yè)。此時,和兒女同期畢業(yè)的母親葛健豪淪入了“畢業(yè)即失業(yè)”的窘境中;三哥蔡和森完成學(xué)業(yè)后,和同學(xué)結(jié)社自學(xué),不但毫無收入,還要增加若干開支。恰在這時,周南附小為蔡暢提供了體育教師的位置。在周南女校的幾年里,她八塊大洋的微薄月薪要應(yīng)付全家人的開銷。經(jīng)過艱苦生活的打磨,蔡暢愈發(fā)顯得穩(wěn)重堅定。
當(dāng)時,幾千年中華文明正處在前所未有的危局中,列強(qiáng)虎視眈眈于外,儒家思想式微于內(nèi),促成了新文化運(yùn)動的興起。長沙既是四方通衢,又有愛國主義傳統(tǒng),社會思潮風(fēng)起云涌。蔡暢初來長沙,原本只是謀求個人的自由解放。但置身于火熱的時代,接觸到《新青年》這樣的進(jìn)步讀物,又親身體會到人民對于國事危亡的痛心和激憤,以她勇敢堅強(qiáng)的個性,不可能不受到當(dāng)時社會上各種思潮影響,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國家民族“救亡圖存”這個大主題上。結(jié)合國家的不幸和自身的遭遇,蔡暢開始意識到,國家命運(yùn)和個人命運(yùn)之間,存在著某種緊密的聯(lián)系,要解決個人問題,非從解決國家的社會問題入手不可。雖然這種認(rèn)識還只是處在模模糊糊的階段,卻為她日后的探索邁出了至關(guān)重要的第一步。
1918年,蔡和森、毛澤東、蕭子升等人在長沙組織的新民學(xué)會成立。當(dāng)時,蔡暢并不是學(xué)會會員,而是學(xué)會最熱心的“旁聽生”。旁聽“大哥哥”們思想的感悟、交鋒和碰撞,讓蔡暢大開眼界。更主要的收獲,則是她得以和一直關(guān)愛自己的三哥蔡和森朝夕相處,近距離接受他的思想熏陶和學(xué)業(yè)指點(diǎn)。以后的十多年中,蔡和森不但常常充當(dāng)蔡暢工作上的領(lǐng)導(dǎo)和同志,更是她思想上無可爭議的導(dǎo)師。70年后,蔡暢為新民學(xué)會題詞:“毛蔡寄廬流芳千載,新民學(xué)會建黨先聲”,以此紀(jì)念這個讓自己人生“轉(zhuǎn)彎”的關(guān)口。
學(xué)會成立只有兩個月時,蔡和森突然離開長沙,遠(yuǎn)赴北京。整整一年之后,三哥從北京給蔡暢來信,傳來一個重要信息:他在這一年里為自己、為蔡暢、也為眾多同志找到了新的努力方向:留法勤工儉學(xué),去尋求改造中國的良方,了解外部更廣闊的世界。
異域生涯,戰(zhàn)士是怎樣煉成的
從1919年10月離開長沙,到1925年8月回到上海,蔡暢的異國“取經(jīng)”之路將近6年,其中除了1925年受中共中央安排在蘇聯(lián)學(xué)習(xí)的半年,其他時間都是在法國度過的。雖然后世通稱這段在法經(jīng)歷為“勤工儉學(xué)”,但單就求學(xué)而言,所占的時間并不長。赴法生1920年2月才到巴黎,真正上學(xué)頭尾不過一兩年,其中多半還用來學(xué)習(xí)語言。1921年2月,在法國,留學(xué)生為反抗北洋政府對留法生的迫害而與之發(fā)生大規(guī)模沖突,6月、9月又接連爆發(fā)了兩次沖突,赴法生連續(xù)沖擊中國駐法公使館和中法合作的大學(xué),以致北洋政府停發(fā)赴法生的生活費(fèi)。到1921年10月,蔡和森在內(nèi)的多數(shù)留學(xué)生被強(qiáng)制遣返,蔡暢和留下的同學(xué)靠做工自食其力,稍有余力再互助學(xué)習(xí)。雖然不能算是正式的“學(xué)生”,卻在實(shí)實(shí)在在的生活中取得了更大的進(jìn)步。
其實(shí)蔡暢和她的同學(xué)們,原本就不是為了學(xué)習(xí)某一科專門的學(xué)業(yè)而赴法。他們的目的,是要在當(dāng)時比東方更加先進(jìn)的歐洲社會中,尋找中國的,同時也是自己的方向。來到法國不久,新民學(xué)會徹底分裂成共產(chǎn)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兩個分支。蔡暢運(yùn)用生澀的法文,依靠字典的幫助研讀理論書籍,在三哥的影響下,最終選擇了共產(chǎn)主義作為自己的信仰,從此,蔡暢一生也沒有背棄自己的信仰。在三次和北洋政府面對面的沖突中,她作為蒙達(dá)尼公學(xué)的女生領(lǐng)袖,直接走到了隊伍的最前面。對她的工作,周恩來曾有“女學(xué)生之加入運(yùn)動,是長男學(xué)生之勢,壯男學(xué)生之氣也”的評價。特別是在三哥回國之后,遠(yuǎn)離“主心骨”又被斷絕經(jīng)濟(jì)來源的蔡暢并沒有慌亂,她一邊在電燈廠、膠鞋廠做工,用一天十個小時的苦工換取留在法國的經(jīng)濟(jì)條件,一邊苦讀馬列著作,還擔(dān)負(fù)起中共旅法小組的宣傳工作。跳出中國旅法生的圈子,她還在身邊的法國工人和留學(xué)生中廣交朋友。就是在這個階段,她贏得了與加香(后為法共領(lǐng)導(dǎo)人)、胡志明(后為越共領(lǐng)導(dǎo)人)的終身友誼。在此期間,蔡暢實(shí)現(xiàn)了自主婚姻的理想,與李富春結(jié)為夫妻。
旅歐生涯里,另一件觸動蔡暢的事情是歐洲婦女地位的解放。法國和蘇聯(lián)當(dāng)時的社會制度差異很大,實(shí)現(xiàn)婦女解放的方式也相去甚遠(yuǎn)。但在兩種不同甚至是沖突的制度之下,男女平等都已經(jīng)作為基本原則被法律保護(hù),也成為社會大眾所公認(rèn)的準(zhǔn)則。相比之下,中國的一般群眾已經(jīng)飽受壓迫,而婦女的地位則更低。通過學(xué)習(xí)和實(shí)踐,蔡暢初步認(rèn)識到婦女問題不僅僅是女性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問題。只有男女平等,社會才能健康發(fā)展。于是,如何解決中國的婦女問題,達(dá)到全社會的男女平等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課題。
帶著這個問題,在蘇聯(lián)的半年里,蔡暢全力以赴研究蘇聯(lián)的婦女兒童工作。除了鉆研理論著作和法律文件,她還到工廠、農(nóng)村、學(xué)校、醫(yī)院,觀摩蘇聯(lián)的基層選舉,考察蘇聯(lián)的兒童托養(yǎng)。她不但看到社會對婦女的解放,也進(jìn)一步去了解婦女的貢獻(xiàn),認(rèn)識婦女的價值,對于“婦女對社會所具有的價值”這個命題,得出了清晰的認(rèn)識,對于“婦女如何求解放”這件事情,形成了自己的思路。在心中,她把共產(chǎn)主義信仰和婦女解放事業(yè)連接在一起,執(zhí)著地追求了一生。
1925年8月,蔡暢受中共中央指派回到上海。此時的蔡暢在異國艱難的歲月里,找到了自己前進(jìn)的方向。她的思想、才華和意志已經(jīng)做好了準(zhǔn)備,作為一個戰(zhàn)士,即將走上屬于她的征途。
轉(zhuǎn)戰(zhàn)之路,不忘初心
1925年8月,蔡暢回國,旋即從上海趕赴廣州,擔(dān)任中共兩廣區(qū)委婦委書記,從此以后就再沒有離開婦女工作。最初幾年,擁有豐富的工廠、農(nóng)村生活經(jīng)驗的蔡暢和戰(zhàn)友們,把精力投入到更具活力的底層婦女運(yùn)動之中。隨著北伐軍在軍事上的節(jié)節(jié)勝利,蔡暢作為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宣傳科科長、北伐軍唯一的女軍官,隨軍一路南下,在一塊塊新開辟的土地上宣講和實(shí)踐她婦女解放的理想。
正當(dāng)勝利看上去觸手可及時,南京“清黨”、武漢“分共”。捕殺、戰(zhàn)爭、流血無處不在,年輕的中國共產(chǎn)黨幾入絕境,無數(shù)親密的戰(zhàn)友犧牲。四年后,更大的一次傷害不期而至:1931年6月,蔡和森在香港被捕,同年8月,在廣州被殺害。對中國革命而言,中國共產(chǎn)黨失去了一位創(chuàng)始者和極其出色的理論家,而對于蔡暢而言,失去了自己的三哥。
面對災(zāi)難,蔡暢選擇了堅強(qiáng)。蔡暢知道,輪到她去舉起火炬,照亮自己,也照亮別人。
在1927年到1949年這22年的戰(zhàn)爭中,蔡暢輾轉(zhuǎn)中國許多地方,留下了這樣一份復(fù)雜的“年表”:
1927年,中共湖北省委婦女部部長、中共中央婦委委員、上海總工會女工部部長;
1930年,婦女部部長;
1931年,中共江西省委組織部部長、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工農(nóng)監(jiān)察委員會主席;
1934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zhí)委會委員,參加長征;
1935年,中共陜甘省委婦女部部長、組織部部長;
1936年,中共陜甘寧省委白區(qū)工作部部長、組織部部長;
1938年,中共中央婦女運(yùn)動委員會常委、書記;
1941年,中共中央婦委書記;
1945年,中共中央婦女運(yùn)動委員會書記;
1946年,中共中央婦女運(yùn)動委員會書記、中共中央西滿分局常務(wù)委員;
1947年,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東北局婦女運(yùn)動委員會書記;
1948年,全國總工會執(zhí)委會委員、女工部部長;
1949年,第一屆全國婦聯(lián)主席、黨組書記。
時局讓蔡暢走過太多地方,擔(dān)任過太多職務(wù),她幾乎沒辦法在一個“專職”的崗位待上幾年。但是每到一地,她都要做同樣的事情:
首先,掃除封建禮教、破棄買賣婚姻,教婦女能獨(dú)立自主;興辦學(xué)校、進(jìn)行教育,教婦女能自尊明理;組織生產(chǎn)、傳授技術(shù),教婦女能自食其力。
接下來,把婦女訓(xùn)練成工人、農(nóng)夫、教員,還有戰(zhàn)士,前方出力、后方生產(chǎn),讓女性的力量得以彰顯。
在政權(quán)穩(wěn)固的地方,制定政策和法律,使種地的婦女有田可耕,做工的婦女同工同酬,家庭里的婦女有平等的繼承權(quán)和財產(chǎn)權(quán)。
培養(yǎng)她們中的一部分和自己一樣的干部,讓從前的村姑媳婦能夠施展身手,做其他千萬個村姑媳婦的榜樣。
22年的轉(zhuǎn)戰(zhàn),她幫助無數(shù)受欺凌與受壓迫者,幫她們自立和成長,成為名副其實(shí)的戰(zhàn)士。這些戰(zhàn)士迸發(fā)出巨大的力量,又推動她們的事業(yè)不斷前進(jìn)。
1949年4月,蔡暢當(dāng)選中華全國婦女聯(lián)合會主席,9月又當(dāng)選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半百之年,她走到了自己事業(yè)新的高峰,等待她的將是一個嶄新的舞臺。
蔡大姐,把名字寫進(jìn)歷史
中國婦女被輕視和壓迫了幾千年,新中國成立后,在很多地區(qū),“男尊女卑”的觀念和做法仍然存在。面對根深蒂固的社會觀念和風(fēng)俗禮法,婦女工作者必須想出更多辦法,來徹底清除封建思想的影響。
195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出臺,明確把重婚、納妾、童養(yǎng)媳、買賣婚姻等封建惡習(xí),統(tǒng)統(tǒng)掃進(jìn)歷史的垃圾堆。家庭是中國社會最重要的單位,《婚姻法》的實(shí)行,讓每個婦女感受到自己地位和權(quán)利的變化,中國的婦女事業(yè),從這每個成員的變化中煥然一新。
種過地、做過工、留過洋的蔡暢認(rèn)為,婦女要得到真正的解放,就要經(jīng)濟(jì)獨(dú)立。全國婦聯(lián)提出“以生產(chǎn)為中心的婦運(yùn)方針”。在農(nóng)村,隨著《土地法》的出臺,蔡暢明確提出,未婚女子要分“姑娘田”,出嫁、改嫁還要把自己的土地帶走。在城市,她大力發(fā)展女工、促進(jìn)同工同酬,還督促普遍建立保育院托兒所為女職工解除后顧之憂。隨著女工、女司機(jī)、女測量員、女子列車組等層出不窮,廣大女性在社會生產(chǎn)中不僅提高了生產(chǎn)技能,為社會作出了貢獻(xiàn),自身也獲得了經(jīng)濟(jì)上的獨(dú)立。
與此同時,她還重視婦女精神的獨(dú)立。短短幾年之間,無數(shù)為女性開設(shè)的學(xué)校建立起來,無數(shù)歷史悠久的學(xué)校對女性打開了大門。婦女們學(xué)到的不僅是科學(xué)知識和一技之長,更學(xué)到了自尊和自信,增強(qiáng)了做自己命運(yùn)主人的覺悟。
1954年普選,蔡暢回想起30年前考察蘇聯(lián)普選的經(jīng)驗,把參選當(dāng)成了婦女權(quán)利教育的大講堂。一張“選民證”,成了婦女口中的“當(dāng)家證”,女選民投票率高達(dá)84%,全國選出各級婦女人大代表98萬人。中國婦女在歷史上第一次真正實(shí)現(xiàn)了“當(dāng)家做主”。
年紀(jì)和職務(wù)的變化,已經(jīng)不允許此時的蔡暢繼續(xù)行走在基層工作的第一線。她所能做的,除了把握黨關(guān)于婦女工作大的政治方向,當(dāng)好中央的參謀,把婦女工作的需求隨時融進(jìn)國家法律政策,以及抓住一切機(jī)會向國際宣傳中國婦女的新形象之外,更多的是放在選拔、任用年輕婦女干部上。紡織工郝建秀、赤衛(wèi)隊隊長李友秀、公社社員申紀(jì)蘭、種棉能手張秋香,以及其他許多本來名不見經(jīng)傳的小人物,從此走上了歷史舞臺。
遺憾的是,在其后一二十年起起伏伏的政治斗爭中,婦女工作受到了沖擊和影響。對于蔡暢本人而言,雖然由于她一貫的溫和厚道,以及和毛澤東多年來如兄妹一般的親密關(guān)系,讓她免遭許多傷害,但仍不可避免地受到那個時代的巨大沖擊。當(dāng)國家逐漸恢復(fù)正常后,75歲的蔡暢當(dāng)選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78歲時連任。這個職務(wù)是對她過去幾十年革命生涯的充分肯定。1980年,80歲的蔡暢提出辭職,從此再未擔(dān)任過任何有實(shí)際職責(zé)的職務(wù)。
此后的蔡暢淡出了大眾的視野,卻沒有走出人們的記憶。從二十幾歲起,她就被身邊的戰(zhàn)友稱為“蔡大姐”,這個稱呼也許是對蔡暢最合適的概括,她質(zhì)樸、溫和與厚重的品格,雖然不見棱角,卻能不受環(huán)境、職位和歲月的侵蝕,始終如一。美國作家索爾斯伯里曾在其《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中說:“如果說長征有什么‘圣徒的話,那么,蔡暢便是。”20世紀(jì) 80年代末,《蔡暢傳》的作者曾走訪了多位她舊日的同事和部下,這些人提及多年前幫助和關(guān)心自己的“蔡大姐”,都毫不掩飾心中的尊重和愛戴。1983年,在蔡暢徹底退休3年之后,40位曾在陜甘寧邊區(qū)工作的婦女干部聚會,聯(lián)署給她這位40年前的老領(lǐng)導(dǎo)發(fā)出慰問信,信中寫道,“大姐:每當(dāng)我們婦女集會的時候,自然而然地就想起了您。大家非常懷念您,因為您和我們婦女的解放、和我們婦女干部的成長是分不開的。大姐:您年事已高,望你多多保重!祝您健康長壽!”
晚年的蔡暢,就這樣在故人的敬愛當(dāng)中,安靜地享受了10年退休時光。1990年,90歲的蔡暢病逝。此時,她曾窮盡一生去追尋的目標(biāo)已逐漸成為現(xiàn)實(shí)。
現(xiàn)在,蔡暢的名字,對許多讀者已經(jīng)有些陌生了。也許未來若干年之后,還會有更多的名字變得陌生。但他們共同寫下的、屬于20世紀(jì)中國的歷史將會長存,因為所有的不屈、抗?fàn)帯^斗和堅持,所有拋灑的血汗和淚水,已經(jīng)匯進(jìn)了民族的血脈之中。
(編輯 王 雪)
(作者是原中國婦女運(yùn)動歷史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