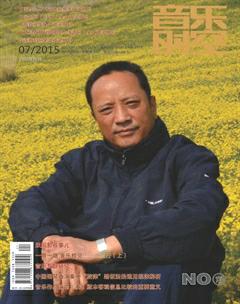淺論魏晉音樂與文學關系
陳玉瑤
摘要:文學與音樂的關系一直以來都是相輔相成、相互影響的。古代的《毛詩序》就記載:“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甚至有人認為,文學的基本特征就是音樂。本文將通過對魏晉時期音樂理論、音樂文學作品等相關資料的解讀,看看音樂與文學是如何相互影響的。
關鍵詞:魏晉音樂 文學
一、魏晉時期的社會背景
魏晉時期(220-420)是中國歷史上最動蕩、最混亂、最黑暗的時期之一,在這個戰亂紛爭、災連禍結的時代,社會中到處彌漫著戰爭的跡象,慘不忍睹。當時的文人用“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來形容當時動亂的社會,何等凄慘。在《魏晉南北朝史》里面我們可以看到,在東漢到晉宋,由于戰亂不止,中國的人口從5600萬減少到了1600萬,這個數目里面包括了很大一批文人。在這個時期,文人們不僅僅要面對自然災害和戰爭,還要面對非常殘酷的政治黑暗,他們不得不對生命進行思考。許多人士面對只要只字片語就可能招致滅頂之災的政治現實,選擇了另外一種方式來曲折表達自己的精神懷抱、超凡脫俗的高潔人格。宗白華先生曾經評價:“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苦痛的時代,然后卻是精神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濃于熱情的一個時代”。
有人選擇了人生如夢,不如及時行樂,比如“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也有人選擇了或藥或酒;再比如“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生年不滿百,常懷千年憂”,也有曹操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陶淵明的《飲酒詩》、阮籍的《詠懷》等等,雖然表達了人生無常,及時享樂的人生態度,但是絕不是一種消極的頹廢,魏晉時代是一個最壞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最好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里面的文人珍惜個體生命,自覺積極思考生命的價值,并用最好的方式來保全并完善生命。因此,在這樣的一個時代,思想活躍、文化多元繁榮、心靈凈化返璞歸真。
二、音樂主流文人化,文人音樂得到長足發展
在魏晉短短不足360的年間,音樂和文學上大有建樹的人可謂是群星閃耀。曹操、曹丕、諸葛亮、以曹植和阮籍為首的”建安七子“,以嵇康為首的”竹林七賢“,以及蔡文姬、左思、陶淵明、謝靈運、陸機等等,都名垂文學和音樂的歷史。在魏晉時期,就已經出現了主流音樂文人化的傾向。我們可以看到魏武帝曹操重視文學,他不僅親自創作詩歌,將其用音樂形式表演,還重視人才,把全國有才華的文人聚集身邊;建安七子,竹林七賢,金谷二十四友及王羲之、謝安郊游式文學沙龍等應運而生。文人地位的提高,使文學和音樂創作發展迅速,大批的文學家都來從事樂府詩歌創作,讓中國文學出現了樂府詩歌創作的高峰。
三、音樂是魏晉文人的精神寄托
音樂是魏晉士人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選取“琴”這個樂器作為了解魏晉音樂的切入口。我們在閱讀這一時期的史料和文學作品,特別是《三國志》《世說新語》《晉書》等可以發現,魏晉時期有姓名可考的知音、愛樂、解律人士多達140余人,善操琴者30余人,魏晉文人愛琴成風。
琴者,先王所有修身、理性、禁邪、防淫者也,是故君子無故不去其身。琴有四美(良質、善斫、妙指、正心)。連嵇康也說:眾器之中,琴德最優。我們可以看到,在魏晉時期彈琴的文人志士頗多,除開琴是一種好聽的樂器以外,更多的應該是琴與當時文人的人格精神相契合的原因,以琴比德,琴是文人的一種情結,魏晉這個動蕩多變的時代,琴所代表的意義就是:孤高、寂寞、激憤的悲劇人格。文人無從選擇,他們在這樣一個無法抱負于天下的時代,只能夠選擇在自然山水之間,寄情于琴弦之上,發千古憂思,抒孤憤之情懷。
看看《廣陵散》。它是中國古代漢族一首大型琴曲,中國音樂史上非常著名的古琴曲,著名十大古琴曲之一。即古時的《聶政刺韓王曲》,魏晉琴家嵇康以善彈此曲著稱,刑前仍從容不迫,索琴彈奏此曲,并慨然長嘆:“《廣陵散》于今絕矣!”我們可以看看,《廣陵散》這首琴曲,嵇康這個極具人格魅力的人物,在這樣一個悲情時代,現實太殘酷,無法直面,他們如果要實現濟世的志向,就不得不委屈自己的性情,置身于各種各樣的政治斗爭與沖突之中,但是這些又是作為孤傲的文人知識分子群體所不能接受的,因此,嵇康用瀟灑面對死亡的姿態,展示出來文人的一種突圍,雖然不是一種好方式但是也是在那種情形之下無奈的一種方式,至少精神突圍了。
所以,有人說琴與魏晉人士的悲劇人格是契合的也是歷史的,是偶然之中的必然反映。在這樣一個虛假、殘酷、冰冷的世界里面,魏晉人士用音樂守護自己獨立高尚的人格,追求生命的真道。
四、音樂影響了魏晉文學
在魏晉時期文人獨具的曠世悲情,必然升華成為獨特的“悲”的審美范式。音樂影響文學,文學也反作用于音樂。他們的互相影響,共同促進,來回應時代的“悲”聲。
晉王謂孫息曰:“子鼓琴能令寡人悲乎?”息曰:“今處高臺邃宇,連屋重戶,藿肉漿酒,倡樂在前。難可使悲者。”乃謂少失父母,長無兄嫂,當道獨坐,暮無所止。于此者,乃可悲耳。乃援琴而鼓之。晉王酸心哀涕曰:“何子來遲也。”(西漢·揚雄《琴清英》)音樂的悲傷是可以影響文學創作的。
魏晉時期的音樂影響了文學理論以及主張。比如曹丕在敘說他的“文氣”說里面就以音樂為比喻寫到“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如音樂,曲度雖均勻,節奏同檢,至于引起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弟子”。
魏晉時期的音樂和文學同情,讓魏晉時期音樂文學作品的情感內涵得以豐富。正是由于音樂的介入,使得在建安時期就已經顯示出來的文學重情傾向得到進一步加強。嵇康在《琴賦》里面說:“歌舞之象,歷世才士,并為之賦頌。其體制風流,莫不相襲。稱其材干,則以危苦為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為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為貴。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也”。
參考文獻:
[1]張少康.先秦兩漢文論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
[2]宗白華.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美學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3]郁沅,張明高.魏晉南北朝文論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