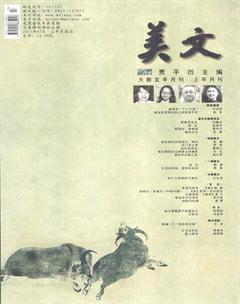清代的公路小說
《儒林外史》第三十五回寫到“莊征君辭爵還家”,看遍官場總總,離開京城,半途想寄宿一老者家,是夜卻撞見了一怪異的場面:
那老爹道:“客官,你行路的人,誰家頂著房子走?借住不妨。只是我家只得一間屋,夫妻兩口住著,都有七十多歲,不幸今早又把個老妻死了,沒錢買棺材,現停在屋里。客官卻在那里住?況你又有車子,如何拿得進來?”莊征君道:“不妨,我只須一席之地,將就過一夜,車子叫他在門外罷了。”那老爹道:“這等,只有同我一床睡。”莊征君道:“也好。”
當下走進屋里,見那老婦人尸首直僵僵停著,旁邊一張土炕。莊征君鋪下行李,叫小廝同車夫睡在車上,讓那老爹睡在炕里邊。莊征君在炕外睡下,翻來覆去睡不著。到三更半后,只見那死尸漸漸動起來。莊征君嚇了一跳,定睛細看,只見那手也動起來了,竟有一個坐起來的意思。莊征君道:“這人活了!”忙去推那老爹,推了一會,總不得醒。莊征君道:“年高人怎的這樣好睡!”便坐起來看那老爹時,見他口里只有出的氣,沒有進的氣,已是死了。回頭看那老婦人,已站起來了,直著腿,白瞪著眼。原來不是活,是走了尸。莊征君慌了,跑出門來,叫起車夫,把車攔了門,不放他出去。莊征君獨自在門外徘徊,心里懊悔道:“吉兇悔吝生乎動,我若坐在家里,不出來走這一番,今日也不得受這一場虛驚!”又想道:“生死亦是常事,我到底義禮不深,故此害怕。”定了神,坐在車子上。一直等到天色大亮,那走的尸也倒了,一間屋里,只橫著兩個尸首。莊征君感傷道:“這兩個老人家就窮苦到這個地步!我雖則在此一宿,我不殯葬他,誰人殯葬?”因叫小廝、車夫前去尋了一個市井,莊征君拿幾十兩銀子來買了棺木,市上僱了些人抬到這里,把兩人殮了。又尋了一塊地,也是左近人家的,莊征君拿出銀子去買。買了,看著掩埋了這兩個老人家。掩埋已畢,莊征君買了些牲醴紙錢,又做了一篇文。莊征君灑淚祭奠了。一市上的人,都來羅拜在地下,謝莊征君。
這兩天讀布魯諾·舒爾茨的書信選《與撒旦的約定》(瓦當編),在他寫給斯坦尼斯瓦夫·伊格納齊·維特凱維奇的信中,有一段話:
……生活的本質就是要使用無數的面具。這里游移似的形態其實才是生活的本質。因此,從這一實體中顯示出帶有一種普遍的諷刺意味的氣氛。在那里彌漫著劇院幕后的氣氛,就是在舞臺后面,當演員脫去戲裝后在那里譏笑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事實上這里也包含著某種嘲諷、欺騙和挖苦。
……但是我說不清楚這種對現實普遍失望的意義何在。我只能說,如果對現實的普遍失望不能在某種空間(維度)得到補償的話,那么,現實就會令人無法忍受。有的時候我們可以從缺憾的現實中獲得一種滿足,我們甚至會對現實的毀滅很感興趣。
我年輕時第一次在大銀幕(應該是臺北的某次金馬獎外片影展其中一部吧)看了安哲羅普洛斯的《霧中風景》:那哀戚像玻璃管的配樂,沉鈍絕望,那對小姐弟在那受創的公路、城市、河岸、火車站展開小小幻燈片里的“父的處所”,所有觀看者都知道他們必然像天葬臺上的肉屑,被這本身也被更巨大的暴力擊打凹歪的大人世界,一步步吞噬,強暴,把那創傷一層層染進他們靈魂里,但又坐在黑暗觀眾席無能為力。某一個片段,電影里那遼闊的廢墟(或科幻意象)的海港,突然超出人類感受尺度,一架直升機用繩索垂吊著一只巨大的、少了兩只指頭的手,螺旋槳扇的風切打著水面的波漣,那巨大如海神的手從水面上突然冒出,以那鉛灰色、憂郁、層積云的天空為背景,那直升機愈飛高遠愈像小小黑點,真的像一只巨靈神的(受創的)手孤獨在空中飛過。
我記得那時我終于被這一幕突破了感情的防線,在那黑暗觀眾席熱淚漫流。
那是什么?突然出現的,和前后文似乎無關的一個驚訝、怪異、無以名狀的景觀。那似乎是許多公路電影的效果,譬如《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那年輕的切·格瓦拉和他堂哥,還不知自己將迎向的是怎樣的“未來的死亡傳奇”,還是兩位拉丁小伙,突然在他們眼前展列的麻風村,壞毀卻仍活著的人形。但那像整片墻落地窗的窗簾被嘩地拉開,讓我們目瞪口呆愣視的怪異風景,似乎在之前,便如細索埋在土里的春蟄、或沉悶厚云層里的靜電,爛床墊翻開前便已聽見許久上萬只白蟻整窩啃嚙著底下的雜志堆或紙箱……
以《儒林外史》來說,那發生在十八世紀清代,短短非意識的一段“公路電影”,一個被敘事置放在那整套官場、酬祚、科舉、敘輩并權力交涉、一種倫理體系語言如無數齒輪咬死、機械運轉,無個人心靈自由空間的“俯瞰式白描”,人物如傀偶在這精密秩序矩陣中命運交織、陽奉陰違,但參與著那巨大“儒教之鐘”的運轉。這時突然冒出這段,岔出敘事默契之外的,半夜走尸。那并不是在讀《聊齋志異》《封神演義》《西游記》的神或鬼之狂想劇場,而是如商偉在這書中所說:“那些自命風雅的詩人、牢騷不平的公子、還有江湖上的騙子、冒名頂替的做假好手,鄉間的一曲之士和不著調的讀書人……那突然闖入的,悲慘且超現實的‘仲夏夜之夢、驚嚇、卻又將之前繁文縟節的‘偽的儀典像激靈靈打了個冷顫,嘩啦啦灑落甩去,而驟進入一孤獨清冷的‘落單的體悟。”仔細想想,我腦海浮現了幾部kuso的日本電影:《重金搖滾雙面人》《下妻物語》、北野武的《阿奇里斯與龜》。他們流連、執迷于我們這時代幾種心靈寄托、形上飛行幻夢的重金屬搖滾癡狂舞臺、想象之境洛可可風戀物癖展廊里的農村少女或是二十世紀后半全球化市場建構的藝術家——終于那進出“偽扮符號體系”之路發生堵塞與短路,在妄夢與難堪現實的引渡之河擱淺,困陷泥灘、發生人格分裂、自我崩解。
在商偉的《禮與十八世紀的文化轉折——〈儒林外史研究〉》中,第二章“秦伯祠:苦行禮與二元禮”有一段話:
和顏元一樣,吳敬梓將文人的喋喋不休的言說看成是空洞的修辭練習,或語言游戲,不過,他也暴露出構成這一游戲和造成言行落差的隱秘力量。在多數情況下,吳敬梓并沒有將他筆下的人物描寫成現存社會政治體制和象征系統的僭越者,而是寫成假冒者、偽君子、騙子和不可救藥的名利之徒。他們與體制周旋,利用規則換取他們能夠撈到的一切好處。因此,他們的墮落并非個人現象,而是暗示了他們身在其中的那個體制允許甚至鼓勵他們往那個方向走,以及最終可以走多遠。在對文人世界的反諷描述中,吳敬梓不只是揭露了個人如何挪用儒家的語言,或者對言辭無法應對現實感到無奈;他還將儒禮自身無可挽回的解體呈現給我們看。
于是,作為二十一世紀的讀者,閱讀著十八世紀(也就是二百五十年前)的這本《儒林外史》,很奇怪的那憂郁、鐵桶覆蓋、像傀偶小人機械運轉說著那層層復瓣、結構森嚴的禮樂、秩序、權力位階間的酬涉與關系網絡的建構,那應該是一個古典、內向、雪花球或博物櫥窗里的微型宇宙模型,但不斷從書頁中翻出的是那書里的小人兒如何精熟老練,和這整套繁瑣“禮教機器”虛與委蛇、陽奉陰違;像附加于這個封密靜態宇宙之外的,更巨大的一個鬼臉的,偽仿(如吳敬梓所反諷的)的資料庫(微博海洋?),這個充滿生命力的,附生于那以死的萎癟老祖宗尸骸骨架上的巨嬰,完全沒有被二十世紀這仿若進入科幻電影的“后來的世界”(如果以十八世紀吳敬梓這些人眼中所看)所滅殺,它們以一種另一視覺、電影剪接的切面,不同時挨擠著,或在魯迅的小說、張愛玲的《雷峰塔》、錢鐘書的小說露一下臉;乃至后來在莫言的某些“晚期風格”小說(譬如《蛙》)、格非的《春盡江南》、金宇澄的《繁花》……又嘻嘩猙獰在某些時刻,過場跑過更現代小說的場景布置。
我們突然發現他們那么熟悉,在閱讀《儒林外史》的時候,仍然包圍在我們“現在”的任何情境,任何場所的“空洞的修辭練習和語言游戲”。這種內向的糾結與蜷縮,某種對集體性的恐懼、世故,因為個體對文明的學習精力全消耗燒盡在那層層累聚、命運交織的繁復體系之交涉、趨吉避兇,或“因為理解,所以自我戲劇化成可以在這樣空洞運轉的偽情感大拼裝機器中,被傳遞、交換、存在得以延續的‘簡化的我”……那一章回一章回十八世紀古代文人臉色明滅不定的“話中有話”的語言交涉,既在小說閱讀中進入我們腦額葉,但同時我們背脊發冷感到我們仍活在那“小說仍延續的世界”中,“到處存在的場所,到處不存在的我”。
駱以軍
臺灣中生代最重要的小說家,作品以小說為主,兼及隨筆、詩歌。長篇小說《西夏旅館》2010年獲得“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首獎。著有《經濟大蕭條時期的夢游街》《西夏旅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