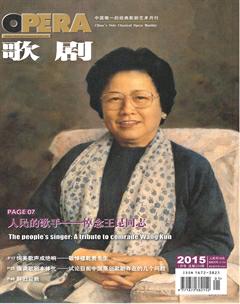辭舊迎新
司馬勤

如果思維正常的話,沒有人會把位于北京的國家大劇院與孟買的國家大劇院這二者混淆起來。前者是為迎接奧運,于2007年開張的,配備了嶄新的舞臺技術設備的宏偉建筑;后者雖早在1969年就動工開建,但到了今天,大堂與場館設計都顯得不合時宜,設備也殘破不全。北京國家大劇院可以說是面向國際的演藝中心;后者,盡管這些年來曾經主辦過一些國際項目,但也只能算是專注于印度本土節目的國家大劇院。
上個月,我走進國家大劇院欣賞了一場精彩絕倫的中國戲曲演出,全場觀眾都被臺上的演員給迷住了。坦白告訴你吧,我其實是在孟買。
這次中國戲曲得以在印度亮相,歸功于薩迪爾戲劇節(Sadir Theatre Festival)的誠意邀請。這個在印度舉辦的藝術節擁有名副其實的國際視野,傳統中國戲曲因而有機會踏上南亞地區的舞臺。這可能是中國經典戲曲亮相于印度國土的第一次。令我感到驚喜的是,這一次遠征印度的不是京劇團(被視為中國“國粹”的戲種),劇目也不是關于《西游記》中的故事(《西游記》的故事不就是記錄中國人到印度的旅程嗎?)。主辦方的選擇經過深思熟慮,他們邀請的是來自北京的中國北方昆曲劇院,演出劇目為《牡丹亭》。
影響主辦方決策的各種因素,其實很簡單。印度悠久的文化歷史著重長篇經典故事,觀眾必定很有耐性。[兩年前,孟買國家大劇院主席孫圖克(K.N.Suntook)出席北京國家大劇院主辦的世界歌劇院發展論壇時,曾經這樣說:“寶萊塢只不過是配上粗劣音樂的歌劇罷了!”]而中國戲曲之中,昆曲文本特有的文學性,與印度文學經典最為接近。薩迪爾戲劇節創始人蘇爾蒂·比塞(Swati Bhise)是一位杰出的傳統舞蹈家。她深知印度觀眾從小就受到傳統藝術的熏陶,懂得欣賞音樂韻律、動作造型與優雅文本的統一性。換上另一個國家的傳統音樂、動作、文本,結合天衣無縫的舞臺藝術,他們盡管不一定明白臺上發生的每一個細節,但必定會有所共鳴。
讓我直說吧,印度的觀眾不但欣賞臺上的昆劇演出,他們確確實實地看懂了這門藝術。或許你會懷疑印度觀眾對于中國傳統戲曲能有多少的文化認知,但在《牡丹亭》劇中發生重要情節的時候,他們都作出了適當的回應。比如說,杜麗娘起死回生的那一刻,全場觀眾頓時鼓掌。
竅門在哪里?字幕的翻譯。
這些年來,閱讀“知音行天下”欄目的朋友們,都知道我對于“字幕”這個話題的觀點。我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迷上意大利歌劇,是因為舞臺上投影了翻譯字幕。當年的投影字幕讓更多的觀眾有機會愛上歌劇。翻譯字幕的始創者就是剛剛倒閉的紐約市立歌劇院。我第一次窺探中國戲曲的奧妙,是1999年由陳士爭執導、林肯中心搬演、歷時20個小時的《牡丹亭》。事隔多年的今天,那還是我畢生最深刻的戲劇經歷之一。
我在幾年前無意中發現,投影字幕這個發明,其實源自亞洲。紐約市立歌劇院總監貝弗利·西爾斯(Beverly Sills)與加拿大歌劇院總監洛特菲·曼沙利(Lotfi Mansouri)兩人被邀請到臺灣考察。當他們觀賞傳統戲曲的時候,看到了投影字幕。后來,他們雙雙把投影字幕引進自己的歌劇院。上月在孟買演出的《牡丹亭》,證明了字幕不一定要跨越亞洲遠達世界各地,也可以在亞洲區內擔負起溝通文化的重任。
有這樣一個比喻可能更為貼切:遠赴印度取經的歷史人物,幾百年前把重要文獻帶回中國。而今天,一個演藝團隊從中國出發,他們帶到印度的,是中國文學的重要傳承。
有人真的相信紐約市立歌劇院就這樣壽終正寢了嗎?一年前,我在這個專欄里已經說過,市立歌劇院申請破產令的主要目的,是讓歌劇院可以重組架構,并非徹底瓦解。2014年12月5日,市立歌劇院董事局同意把歌劇院剩下來的資產一除了歌劇院所剩無幾的留本基金(endowment)以外——賣給一群投資者。而這群投資者的領頭人,是邁克爾·卡帕索,他正是迪卡珀歌劇團(Di Capo Opera)的創辦人。迪卡珀歌劇團是紐約多個室內歌劇團之一。
根據卡帕索于去年1月份遞交的建議書(我從某個渠道找來了拷貝文本,該文長達69頁!),歌劇院將改名為“紐約市立歌劇院復興”(NYCO Renaissance),從前的市立歌劇院品牌將注入新的定義。重生的歌劇院搬演的首個劇目,將會是由弗朗哥-澤菲雷里(Franco Zeffirelli)執導的《托斯卡》,這個制作也將為歌劇院與羅馬歌劇院的長期合作伙伴關系拉開帷幕。“復興”的頭三個演出季包括三部美國歌劇經典。多年來,這些劇目與紐約市立歌劇院息息相關:卡萊爾·弗洛伊德(Carlyle Floyd)的《蘇珊娜》、伯恩斯坦的《老實人》,又名《貢迪德》、《康迪德》或《天真漢》)、羅伯特·沃德(Robert Ward)的《煉獄》(Crucible)。從前,紐約市立歌劇院發掘新歌劇的VOX項目,找來了志同道合的美國歌劇計劃為合作伙伴,得以繼續。
最令人矚目的一點,在卡帕索的計劃中,歌劇院將重回林肯中心的懷抱。當年林肯中心的紐約州立歌劇院(New York State Theater。現改名為科克劇院)為市立歌劇院增添了不少麻煩一租金昂貴之極、與毗鄰的大都會歌劇院相較往往吃虧、為期一年的維修重組工程迫使歌劇院整個演出季處于休假狀態——林肯中心可算是將市立歌劇院推進墳墓的兇手之一。卡帕索打算進駐林肯中心比較小型的羅斯劇院(Rose Theater,也是林肯中心爵士總部基地),座位要比從前的劇院少了一半、經費也同樣減了一半。
卡帕索的計劃書以及財政預算,看起來合情合理。營運成本可以減低至150萬美元(市立歌劇院最后一年的營運成本是430萬美元)。“復興”首個演出季的預算,只不過是市立歌劇院當年1000萬美元的一半。這些數據不但看起來踏實,卡帕索的計劃書更包括了多明戈大師親自撰寫的一份推薦書。
可是,在2014年12月23日,正當政府各個部門準備關門放年假的那一刻,曾捐款給紐約市立歌劇院的吉恩·考夫曼——他是一位建筑師,也代表另一個競投市立歌劇院商標與贊助者名單的團隊——在紐約市破產法庭中提出上訴,質疑卡帕索的計劃,并要求截止期限從2015年1月9日延遲至1月12日,聆訊日期也推遲至1月20日。
他的理由如下:這些年來,卡帕索與工會的關系惡劣——迪卡珀歌劇團也有因為財政問題被迫取消演出季的前科——考夫曼希望法庭慎重考慮其他方案。特別令人憤慨的是,他接受紐約財經雜志《科倫》訪問時聲稱,“復興”的董事局里包括幾位市立歌劇院前任董事,就是他們當年的錯誤抉擇導致了市立歌劇院被迫倒閉。
這樣說吧,市立歌劇院這臺戲還沒有結束。在我的記憶之中,市立歌劇院的舞臺上從來都沒有過這么具有戲劇性的發展。
我記得,早在2007年初,我聽說蒂姆·波頓(Tim Burton)要把桑德海姆的經典音樂劇《理發師陶德》拍成電影(預計要趕上2014年圣誕節放映),當時被嚇得我啞口無言。一位朋友對我說,普天同慶的圣誕電影檔期,竟會出現殺人狂理發師,將被害者剁成碎肉,烤出肉餅賣給饑餓的群眾!天吶!愿上帝保佑你們!
去年的圣誕電影榜上包括了《魔法黑森林》。這么說吧,斯蒂芬·桑德海姆(Stephen Sondheim)創作的音樂劇變成了扭曲圣誕意義的一種新傳統。還好,最起碼《魔法黑森林》的情節沒有《理發師陶德》那么血腥——真的,很少有音樂劇可以比得上理發師人吃人那么駭人聽聞的——盡管如此,《黑森林》的故事一點兒都不算“老少咸宜”。故事中包括了灰姑娘、長發姑娘(Rapunzel)、漢澤爾(Hansel),格蕾泰爾(Gretel)、還有幾位王子,但是情節的處理卻讓格林童話染上了后弗洛伊德(post-Freudian)的色彩。著名心理學家布魯諾·貝特爾海姆在《童話的魅力》中所發表的理論,像經過絞肉機粉碎后的碎片一般,在這部音樂劇中到處浮現(我覺得這兒用上《理發師陶德》的譬喻,十分貼切)。這部音樂劇與迪斯尼銀幕上的童話動畫,簡直有著天壤之別。
但從宏觀來看,時間配合得堪稱完美,因為中文版的《魔法黑森林》正在籌備中。坦白說,面對這樣一個中國音樂劇項目,我持懷疑態度。全球經典英文劇目,顯赫的作曲家兼填詞家的眾多佳作之中,桑德海姆的音樂劇屬于最難翻譯的劇目——我指的不單是他那令人贊嘆的、特異的文字格律,還有他對當代社會一針見血的評論,以及劇中那些富有立體感、容易犯錯、一點都不完美的人物。要是去掉了西方社會背景(更準確地說,紐約市的氛圍),要觀眾看得懂桑德海姆,除了找來高水平的翻譯以外,更需要添加多項附注。你們知道嗎?桑德海姆的音樂劇等了幾十年,才有機會在法國公演!
我對中國這個音樂劇項目還是抱有一絲希望的。我不祈求中文版本可以成功地反映桑德海姆的原意與概念。其實,我對好萊塢任何一位導演都會投不信任票:他們沒有哪個可以忠于桑德海姆的。羅伯·馬歇爾(Rob Marshall)多年前導演《芝加哥》營造出來的氣氛,其風格最為接近桑德海姆(但我還是覺得兩者是無法直接比較的)。在過去幾周里,我從多位桑德海姆懷疑論者的口中聽聞,馬歇爾處理《魔法黑森林》這部電影十分稱職,令人佩服。真的要用桑德海姆的漢澤爾與格蕾泰爾來替代洪佩爾丁克(Humperdinck)的歌劇《漢澤爾與格蕾泰爾》為大眾歡迎的圣誕佳作,這絕不可能。但是,這部電影現在面對全球觀眾,普羅大眾有機會更深入地去認識故事中令人出乎意料的情節,對于中國的制作也應該有所幫助。最起碼的,中國版本可以更忠于原著。
讓我在這里擱筆,向大家送上節日的祝賀。我正要趕往電影院到黑暗的森林深處去探望外婆和邪惡的大灰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