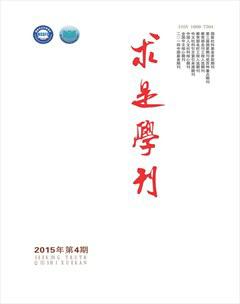創新投入、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
李政+楊思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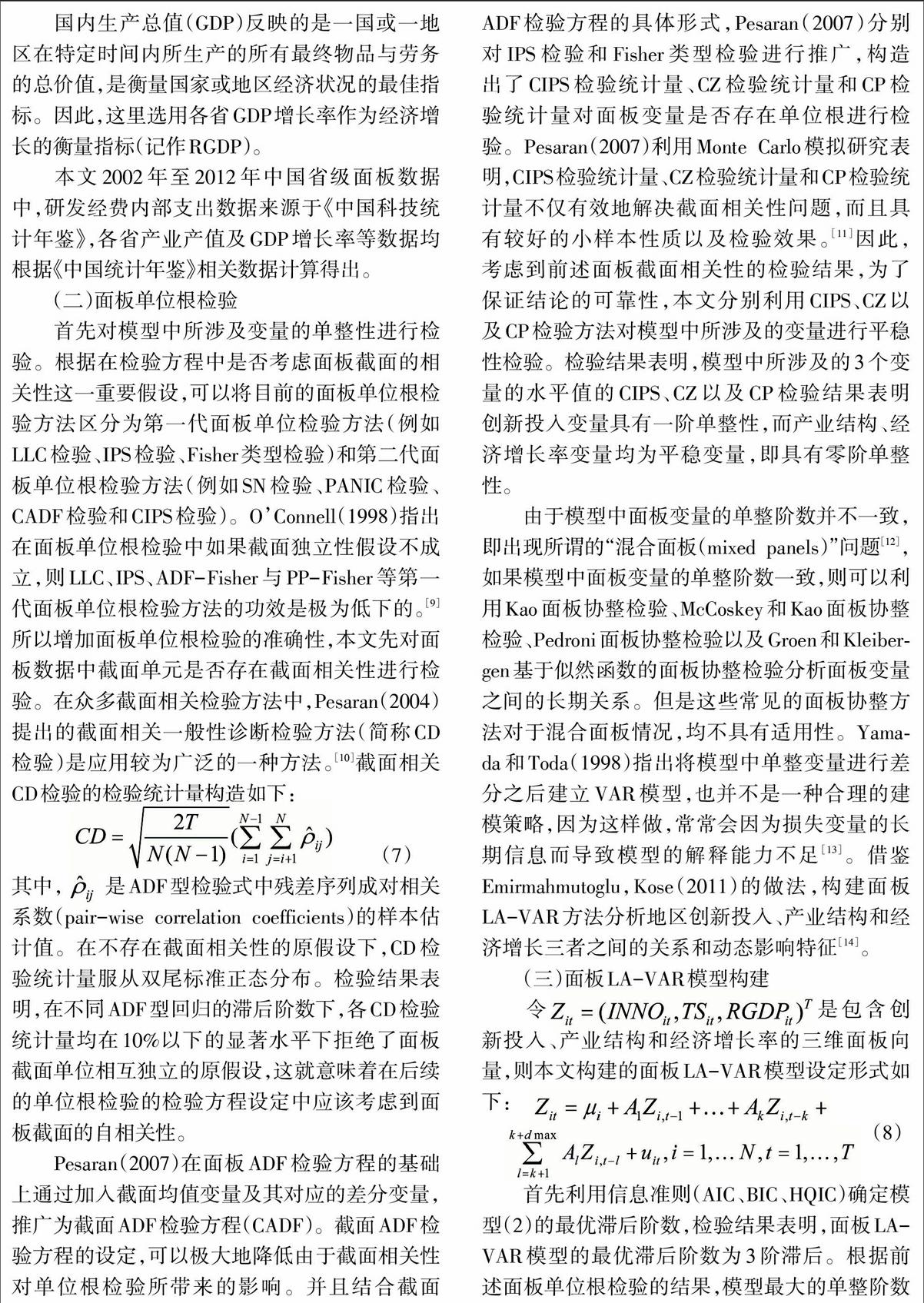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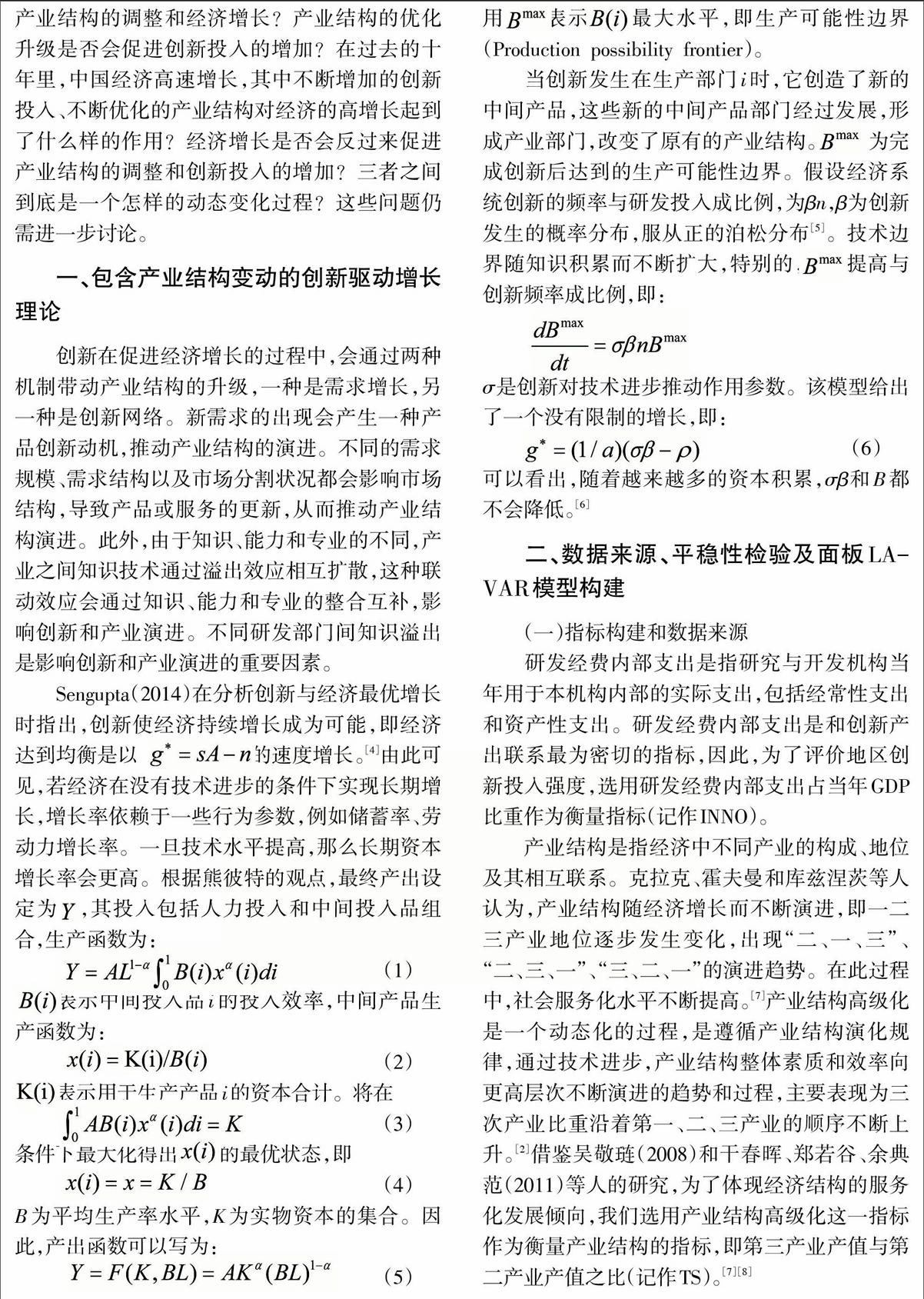
摘 要:創新是經濟增長的長期動力。當前,中國經濟同時面臨增速下行壓力和結構調整要求。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潛能,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基于2002年到2012年省級面板數據,運用面板LA-VAR模型分析中國創新投入、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三者之間的關系表明,中國創新投入對經濟增長具有重要推動作用。但目前創新投入結構不盡合理,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產業結構向高級化水平發展,并導致產業結構凝固。經濟增速提高對產業結構的帶動作用不顯著,也未導致創新投入強度的提高,即經濟增長與創新投入之間沒有形成聯動機制。產業結構向高級化發展能夠有效提高經濟增長速度,但對創新投入強度呈負向影響。處理好三者之間的關系,形成彼此相互促進的聯動機制,必將有助于中國經濟轉型和平穩增長。
關鍵詞:創新投入;產業結構;經濟增長;面板LA-VAR模型
作者簡介:李政,男,經濟學博士,吉林大學中國國有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國有經濟與創新經濟學研究;楊思瑩,男,吉林大學經濟學院研究生,從事國有經濟研究。
基金項目: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項目編號:NCET-12-0242;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我國創新集群培育的機制與對策研究”,項目編號:13CJY053;吉林大學“985工程項目”
中圖分類號:F12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504(2015)04-0061-07
引 言
面對我國經濟下行壓力,繼續不遺余力地保增長、調結構,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是扭轉我國經濟增速下滑、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舉措。近年來,國家不斷加大創新投入,2013年我國研發經費為11906億元,比上年增長15.6%,占GDP比重為2.09%,與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差距進一步縮小。研究顯示,我國研發創新效率仍處于較低水平,但逐年不斷提高[1]。研發是創新過程中的重要環節,研發投入在質和量上逐年提高,是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要任務。各地區通過增加研發投入保障,合理配置研發創新資源,促進地區創新水平的提高,對地區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轉型具有重要意義。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必須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強調要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科技創新不僅可以直接轉化為生產力,而且可以通過擴散效應提高各生產要素使用效率,促進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水平。
與不斷加大的研發投入相比,我國產業結構調整速度卻相對緩慢。1978年第一、二、三產業比重分別為28.2:47.9:23.9,而2013年第一、二、三產業比重為10.1:43.9:46.1。1雖然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第三產業比重大幅上升,但是第二產業占比相對于發達國家依然較大,并且處于國際產業鏈的中低端,資源消耗大、利潤低,并由此造成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等問題。傳統的以資源高消耗、環境高污染為代價的增長方式難以為繼。此外,中國是制造業大國,但一直是“創新小國”“供應鏈小國”“品牌小國”。產業結構水平受科技水平、創新水平限制,調整速度緩慢,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經濟增長。創新能夠不斷更新產業所依賴的特定的知識基礎,提高產業基礎技術水平,帶動產業發展,并推動上下游產業的科技創新,催生新的相關服務性產業。創新資源在不同產業之間合理配置,可以促進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
此外,雖然經過多年發展,我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但是我國人口眾多,人均國民總收入較一些發達國家仍有差距。2011年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為4940美元,大約是韓國的五分之一,英國的七分之一,日本的九分之一,美國的十分之一。2012年,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排在第94位,與韓國(第39位)、英國(第27位)、日本(第17位)和美國(第14位)等發達國家差距較大。從增速來看,相對于其他四國,2011年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增長幅度最高,為15.96%,其次是日本(7.24%)、韓國(4.93%)、美國(2.32%),英國出現了負增長。因此,抓住機遇,繼續保持經濟快速增長,是縮小我國與發達國家收入差距的重要保證。目前我國正處于經濟增速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疊加”階段,經濟增速下行壓力加大,如何找到穩增長和調結構之間的平衡,是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又一重要課題。
產業結構優化的目標是資源配置最優化和宏觀經濟效益最大化,即實現產業結構的高度化和合理化,最終實現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推進產業結構轉型,增強創新驅動發展新動力,加快形成經濟發展新方式,推動經濟社會科學發展、率先發展,就必須處理好創新、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
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最主要的是靠創新推動,創新是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最主要的推動力。技術進步創造出新工藝、新產品,并發展成新的生產部門和行業。這些新的生產部門憑借自身的技術優勢,能夠迅速積聚各種資源,規模不斷擴張,市場勢力迅速膨脹,甚至壟斷市場。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二者之間的關系一直是學術界爭論的話題,以庫茲涅茨為代表的觀點認為經濟增長是一個總量過程,總量增長引起部門結構變化;以羅斯托為代表的觀點認為經濟增長本質上是一個部門的過程,部門結構變動推動總量增長。[2]經濟增長階段論認為,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是一個結構轉換過程,一定的經濟增長階段與一定的產業結構相對應。[3]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并且對經濟發展具有促進作用。隨著科技發展,創新和技術進步必然會影響各生產要素在不同產業的重新配置,引起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資源使用效率得到提高,由此促進了經濟增長。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和經濟增長相互促進,一個高度發達的經濟體需要一個高度化的產業結構與之相適應。因此,產業結構必然成為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產業結構的高度化、合理化影響著經濟增長的速度。
然而,大部分研究都只注重創新投入、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某兩者之間的關系,而沒有從三者整體聯系的角度去分析三者之間的關系。當前中國正處于實施創新驅動發展的初級階段,面臨經濟增速下行、產業結構不合理等問題,如何把握三者之間的聯系,完善產業結構調整政策,合理配置創新資源,穩定經濟增速,解決這些問題具有重要意義。在研發創新效率較低、研發投入不斷加大的條件下,創新是否真正推動了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經濟增長?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是否會促進創新投入的增加?在過去的十年里,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其中不斷增加的創新投入、不斷優化的產業結構對經濟的高增長起到了什么樣的作用?經濟增長是否會反過來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創新投入的增加?三者之間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動態變化過程?這些問題仍需進一步討論。
一、包含產業結構變動的創新驅動增長理論
創新在促進經濟增長的過程中,會通過兩種機制帶動產業結構的升級,一種是需求增長,另一種是創新網絡。新需求的出現會產生一種產品創新動機,推動產業結構的演進。不同的需求規模、需求結構以及市場分割狀況都會影響市場結構,導致產品或服務的更新,從而推動產業結構演進。此外,由于知識、能力和專業的不同,產業之間知識技術通過溢出效應相互擴散,這種聯動效應會通過知識、能力和專業的整合互補,影響創新和產業演進。不同研發部門間知識溢出是影響創新和產業演進的重要因素。
Sengupta(2014)在分析創新與經濟最優增長時指出,創新使經濟持續增長成為可能,即經濟達到均衡是以 的速度增長。[4]由此可見,若經濟在沒有技術進步的條件下實現長期增長,增長率依賴于一些行為參數,例如儲蓄率、勞動力增長率。一旦技術水平提高,那么長期資本增長率會更高。根據熊彼特的觀點,最終產出設定為 ?,其投入包括人力投入和中間投入品組合,生產函數為:
(1)
表示中間投入品i的投入效率,中間產品生產函數為:
(2)
表示用于生產產品i的資本合計。將在
(3)
條件下最大化得出 ? ?的最優狀態,即
(4)
B為平均生產率水平,K為實物資本的集合。因此,產出函數可以寫為:
(5)
用 ? ?表示 ? ?最大水平,即生產可能性邊界(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當創新發生在生產部門i時,它創造了新的中間產品,這些新的中間產品部門經過發展,形成產業部門,改變了原有的產業結構。 為完成創新后達到的生產可能性邊界。假設經濟系統創新的頻率與研發投入成比例,為βn,β為創新發生的概率分布,服從正的泊松分布[5]。技術邊界隨知識積累而不斷擴大,特別的, ? ?提高與創新頻率成比例,即:
σ是創新對技術進步推動作用參數。該模型給出了一個沒有限制的增長,即:
(6)
可以看出,隨著越來越多的資本積累,σβ和B都不會降低。[6]
二、數據來源、平穩性檢驗及面板LA-VAR模型構建
(一)指標構建和數據來源
研發經費內部支出是指研究與開發機構當年用于本機構內部的實際支出,包括經常性支出和資產性支出。研發經費內部支出是和創新產出聯系最為密切的指標,因此,為了評價地區創新投入強度,選用研發經費內部支出占當年GDP比重作為衡量指標(記作INNO)。
產業結構是指經濟中不同產業的構成、地位及其相互聯系。克拉克、霍夫曼和庫茲涅茨等人認為,產業結構隨經濟增長而不斷演進,即一二三產業地位逐步發生變化,出現“二、一、三”、“二、三、一”、“三、二、一”的演進趨勢。在此過程中,社會服務化水平不斷提高。[7]產業結構高級化是一個動態化的過程,是遵循產業結構演化規律,通過技術進步,產業結構整體素質和效率向更高層次不斷演進的趨勢和過程,主要表現為三次產業比重沿著第一、二、三產業的順序不斷上升。[2]借鑒吳敬璉(2008)和干春暉、鄭若谷、余典范(2011)等人的研究,為了體現經濟結構的服務化發展傾向,我們選用產業結構高級化這一指標作為衡量產業結構的指標,即第三產業產值與第二產業產值之比(記作TS)。[7][8]
國內生產總值(GDP)反映的是一國或一地區在特定時間內所生產的所有最終物品與勞務的總價值,是衡量國家或地區經濟狀況的最佳指標。因此,這里選用各省GDP增長率作為經濟增長的衡量指標(記作RGDP)。
本文2002年至2012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中,研發經費內部支出數據來源于《中國科技統計年鑒》,各省產業產值及GDP增長率等數據均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相關數據計算得出。
(二)面板單位根檢驗
首先對模型中所涉及變量的單整性進行檢驗。根據在檢驗方程中是否考慮面板截面的相關性這一重要假設,可以將目前的面板單位根檢驗方法區分為第一代面板單位檢驗方法(例如LLC檢驗、IPS檢驗、Fisher類型檢驗)和第二代面板單位根檢驗方法(例如SN檢驗、PANIC檢驗、CADF檢驗和CIPS檢驗)。OConnell(1998)指出在面板單位根檢驗中如果截面獨立性假設不成立,則LLC、IPS、ADF-Fisher與PP-Fisher等第一代面板單位根檢驗方法的功效是極為低下的。[9]所以增加面板單位根檢驗的準確性,本文先對面板數據中截面單元是否存在截面相關性進行檢驗。在眾多截面相關檢驗方法中,Pesaran(2004)提出的截面相關一般性診斷檢驗方法(簡稱CD檢驗)是應用較為廣泛的一種方法。[10]截面相關CD檢驗的檢驗統計量構造如下:
(7)
其中, 是ADF型檢驗式中殘差序列成對相關系數(pair-wis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的樣本估計值。在不存在截面相關性的原假設下,CD檢驗統計量服從雙尾標準正態分布。檢驗結果表明,在不同ADF型回歸的滯后階數下,各CD檢驗統計量均在10%以下的顯著水平下拒絕了面板截面單位相互獨立的原假設,這就意味著在后續的單位根檢驗的檢驗方程設定中應該考慮到面板截面的自相關性。
Pesaran(2007)在面板ADF檢驗方程的基礎上通過加入截面均值變量及其對應的差分變量,推廣為截面ADF檢驗方程(CADF)。截面ADF檢驗方程的設定,可以極大地降低由于截面相關性對單位根檢驗所帶來的影響。并且結合截面ADF檢驗方程的具體形式,Pesaran(2007)分別對IPS檢驗和Fisher類型檢驗進行推廣,構造出了CIPS檢驗統計量、CZ檢驗統計量和CP檢驗統計量對面板變量是否存在單位根進行檢驗。Pesaran(2007)利用Monte Carlo模擬研究表明,CIPS檢驗統計量、CZ檢驗統計量和CP檢驗統計量不僅有效地解決截面相關性問題,而且具有較好的小樣本性質以及檢驗效果。[11]因此,考慮到前述面板截面相關性的檢驗結果,為了保證結論的可靠性,本文分別利用CIPS、CZ以及CP檢驗方法對模型中所涉及的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檢驗結果表明,模型中所涉及的3個變量的水平值的CIPS、CZ以及CP檢驗結果表明創新投入變量具有一階單整性,而產業結構、經濟增長率變量均為平穩變量,即具有零階單整性。
由于模型中面板變量的單整階數并不一致,即出現所謂的“混合面板(mixed panels)”問題[12],如果模型中面板變量的單整階數一致,則可以利用Kao面板協整檢驗、McCoskey和Kao面板協整檢驗、Pedroni面板協整檢驗以及Groen和Kleibergen基于似然函數的面板協整檢驗分析面板變量之間的長期關系。但是這些常見的面板協整方法對于混合面板情況,均不具有適用性。Yamada和Toda(1998)指出將模型中單整變量進行差分之后建立VAR模型,也并不是一種合理的建模策略,因為這樣做,常常會因為損失變量的長期信息而導致模型的解釋能力不足[13]。借鑒Emirmahmutoglu,Kose(2011)的做法,構建面板LA-VAR方法分析地區創新投入、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三者之間的關系和動態影響特征[14]。
(三)面板LA-VAR模型構建
令 是包含創新投入、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率的三維面板向量,則本文構建的面板LA-VAR模型設定形式如下:
(8)
首先利用信息準則(AIC、BIC、HQIC)確定模型(2)的最優滯后階數,檢驗結果表明,面板LA-VAR模型的最優滯后階數為3階滯后。根據前述面板單位根檢驗的結果,模型最大的單整階數為1,即 。Emirmahmutoglu,Kose(2011)建議對模型(2)進行OLS估計。
由估計結果可以看出,首先,滯后前三期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對創新投入強度在10%的置信水平下負相關,但系數非常小。這說明產業結構向高級化方向發展對創新投入的提高有負作用。滯后一期、滯后二期和滯后三期的GDP增長速度對創新投入強度作用不顯著。其次,創新投入強度各期均在較高的置信水平下對我國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產生負向影響,說明我國創新驅動經濟增長作用第二產業要優于第三產業。導致這種狀況的原因可能有兩種,第一,各省創新投入多集中在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創新投入較低;第二,第三產業創新效率低于第二產業。從創新投入角度來看,如此分配創新資源導致的結果只是產業結構凝固,第二產業比重居高不下。GDP增長速度對產業高級化水平的作用也不顯著,因此可以得出我國經濟增長速度的提高對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的作用不明顯。最后,各期的創新投入強度和產業高級化水平均對GDP增長速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并且創新投入強度系數遠大于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系數,因此判斷,各省創新投入對經濟增長速度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創新投入強度的提高能夠有效促進各省經濟增速的提高。
(四)脈沖響應分析
利用脈沖響應函數對上述構建的面板LA-VAR模型進行結構分析。
從分析結果看,創新投入強度對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和GDP增長速度的脈沖響應,可以看出創新投入強度對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和經濟增長速度沖擊的響應非常小,來自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的波動和經濟增長速度的外生擾動對創新投入強度影響較小。產業結構向高級化水平發展以及經濟增速的提高沒能有效帶動創新投入強度的提高。因此,建立三者之間的聯動機制,使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和經濟增速的提高能夠增強創新投入強度,是我國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高創新水平的重要保證。
從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對創新投入強度的沖擊響應來看,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對創新投入強度當期沖擊響應為正,隨后五期響應均為負。說明創新投入強度的外生擾動會引起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的下降,這說明各地區創新投入強度的提高有效促進了第二產業的發展,創新投入強度對第三產業的拉動作用明顯低于第二產業。
從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對GDP增長速度的沖擊響應來看,對于滯后三期的GDP增速波動響應為負,說明GDP增長速度的外生擾動會降低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從滯后四期的數值來看,GDP增長速度對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存在正的滯后影響,雖然這種影響僅為一年,滯后五期這種影響逐漸下降為零。
從GDP增長速度對創新投入強度的沖擊響應來看,經濟增長速度對創新投入強度的沖擊響應當期為負值,往后兩期均為正值。說明創新投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具有一年左右的滯后期,并且這種影響能夠持續兩年。
從GDP增長速度對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的沖擊反應來看,GDP增長速度對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當期沖擊為負,滯后兩期響應為正向,說明在產業結構向高級化發展會帶來經濟增速的下滑,這也是我國正面臨的產業結構調整陣痛期,但是滯后兩期的影響為正,隨后逐步收斂為0。
(五)面板Granger因果檢驗
本文將基于前述所構建的面板LA-VAR模型,進行面板Granger因果檢驗,從而揭示中國地區創新投入、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之間的動態影響特征。
從面板Granger因果影響檢驗結果看:對于不管是高創新投入地區還是低創新投入地區,創新投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均是顯著的,但是經濟增長對地區創新投入的作用并不顯著。高創新投入地區的創新投入對產業結構的影響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但是低創新投入地區的創新投入對產業結構的影響不顯著。同時不管是高創新投入地區還是低創新投入地區,產業結構對創新投入強度的反饋作用均不顯著。最后,不管是高創新投入地區還是低創新投入地區,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均存在雙向的Granger因果影響。
三、簡要的結論及政策含義
基于2002年到2012年省級面板數據,本文運用面板LA-VAR模型和面板Granger因果檢驗分析了中國創新投入、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三者之間的關系,得出以下基本結論:
第一,無論是高創新投入地區,還是低創新投入地區,創新投入對經濟增長具有較大的拉動作用。因此面對人口眾多、人均資源匱乏、生態環境壓力巨大的具體國情,堅定不移地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不斷提高創新投入強度,注重培養創新人才,形成產學研相結合的創新系統,發揮創新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對提高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但是也必須注意到,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并未帶動創新投入強度的高增長。經濟增速的提高對創新投入強度的拉動作用還很小,因此要不斷加大創新投入,形成創新投入與經濟增長的雙向促進的聯動機制。
第二,創新投入對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呈現顯著的負向影響。產業結構和創新之間本應存在的互相促進關系[15],在中國并不存在。創新投入對第二產業的拉動作用優于第三產業。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對創新投入同樣具有負向影響。創新投入多以第二產業為主,忽視第三產業創新,這種不合理的創新投入結構導致了產業結構調整速度緩慢,產業結構凝固。因此要調整創新資源分配格局,增加第三產業創新資源投入,發揮創新對第三產業的拉動作用,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第三,產業結構高度化水平對經濟增長速度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無論是高創新投入地區,還是低創新投入地區,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的提高能夠有效促進經濟增長速度的提升。估計系數顯示GDP增長速度對產業結構高級化具有不顯著的正向作用,而Granger因果檢驗得出兩種投入地區的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和經濟增長速度互為因果。因此,在促進經濟增長過程中要進一步發揮第三產業的作用,通過創新手段,提高第三產業技術發展水平和生產效率,增加第三產業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投入,發揮第三產業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保證經濟增長速度的同時提高增長質量。
總而言之,中國創新投入、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三者之間并沒有形成一種通暢的聯動機制,這種聯動機制的缺乏影響我國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實施效果。因此,疏通三者之間相互作用脈絡,合理配置各種創新資源,發揮創新對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的帶動作用,同時調整創新投入結構,著力加大第三產業創新投入,形成創新驅動作用下的創新投入合理增長、產業結構向高度化方向發展和經濟增速穩步提升的聯動機制。
參 考 文 獻
[1] 白俊紅、江可申、李婧:《應用隨機前沿模型評測中國區域研發創新效率》,載《管理世界》2009年第10期.
[2] 付凌暉:《我國產業結構高級化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載《統計研究》2010年第8期.
[3] 林善煒:《中國經濟結構調整戰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4] Aghion,Philipe,Peter Howit.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Cambridge MA:MIT Press,1998.
[5] Sengupta,J. Theory of Innovation a New Paradigm of Growth. Springer press,2014.
[6] 江洪:《自主創新與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華中科技大學博士論文,2008.
[7] 吳敬璉:《中國增長模式抉擇》,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8.
[8] 干春暉、鄭若谷、余典范:《中國產業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和波動的影響》,載《經濟研究》2011年第5期.
[9] OConnell,P. G. J. “The Overvaluation of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i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8(44).
[10] Pesaran,M. H. “General Diagnostic Tests for Cross-Section Dependence in Panels”,Working Paper,Trinity College,2004,Cambridge.
[11] Pesaran,M. H. “A Simple Panel Unit Root Test in the Presence of Cross-section Dependence”. in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2007(22).
[12] Zixiong Xie,Shyh-Wei Chen.“Untangling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Budget and Current Account Deficits in OECD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bootstrap panel Granger causality”. i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14(31).
[13] H.Yamada,H.Y.Toda.“Inference in Possible Integrated Vector Autogressive Models: Some Finite Sample Evidence”. in 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8(86).
[14] Emirmahmutoglu,F.,Kose,N.“Testing for Granger in Heterogeneous Mixed Panels”. in Economic Modelling. 2011(28).
[15] Greunz,L.“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nnovation-evidence from European Regions”,in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2004(5).
[責任編輯 國勝鐵]
Innovation Input,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LI Zheng,YANG Si-ying
(Center for the Study on Chinese National Econom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ina)
Abstract: Innovation is the lasting power for economic growth. At present, Chinese economy faces a slowdown of economic growth and requirement for an updating of structure. It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of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to improve quality and proficiency of economic growth, and promote optimal updat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a new normal state.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2 to 2012 and adoption of panel LA-VAR model to analyze the relation among Chinese innovation input,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it shows that innovation input propels economic growth, but at present, the structure of innovation input is not reasonable, for it hinders industrial structure to develop to a higher level and leads to an industrial concretion of the latter. The increase of economic growth does not propel industrial structure very much 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tensity of innovation input, i.e. there is no coordinated mechanism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innovation input. Updat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helps improve speed of economic growth, but influences negatively on intensity of innovation input. It is good to deal well with the relation among the three and form an active coordinated mechanism so as to help Chinese economy to transform and grow steadily.
Key words: innovation input, industrial structure, panel LA-VAR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