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肉搜索的?罪與罰
王曉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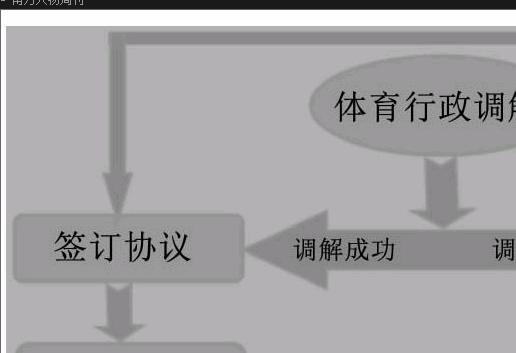

時光倒流十年,大概沒有人會想到,有一天會出現“人肉搜索”這個詞語,更不會想到,給人以最大自由的互聯網,也會成為“多數人的暴政”的工具。人們發現,在互聯網上“沒人知道你是一條狗”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只要你被人盯上,短時間之內,你的所有資料將在網上公布,所有生活細節將一覽無余。
“人肉搜索”是正義驅使嗎?
“我希望能找到失去聯絡9年之久的父親!”24歲的奧運會女子氣手槍金牌得主郭文也許不會料到,她在獲獎后說的這句話,會讓自己“陷入了網中央”。為了幫助這位奧運冠軍尋找父親,網民發動了大規模的“人肉搜索”。父親找到了,但網上出現的大量揭秘式信息,令郭文陷入了巨大尷尬。
據《南方都市報》2014年9月8日報道,因懷疑顧客偷了一件衣服,汕尾陸豐市一服裝店主蔡女士將顧客視頻截圖發上微博尋求人肉搜索,兩天后該顧客不堪壓力,跳河自殺。這個事件不僅釀造了一場“人肉”悲劇,也突破了法律邊界。
事實上,“人肉搜索”從誕生之日起,就游走在法律和道德的中間地帶。“人肉搜索”在中國催生了數起轟動一時的網絡事件:從2006年的“虐貓”門事件到“銅須門”事件,從2007年底自殺的北京女白領姜巖到今年的“遼寧罵人女”……每一次的“人肉搜索”都會詳細公布目標人信息,包括姓名、照片、家庭、住址等等都無所遁形。
“人肉搜索對于這個數字化時代而言,就是一個獨特的中國現象。”英國《泰晤士報》在今年6月的報道中這么總結。
為什么“人肉搜索”會愈演愈烈?文化學者朱大可對此有形象的解釋:“他們以無名氏的方式,藏在黑暗的數碼叢林里,高舉話語暴力的武器,狙擊那些被設定為有罪的道德獵物。”
人們早已發現“人肉搜索”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網友們在通過它宣揚著懲惡揚善的社會正義;但另一方面,用“人肉搜索”搜集并公布當事人的個人信息,對處于言論表達弱勢端的個體進行群體圍攻甚至道德審判,導致當事人在現實生活中遭到侵擾。
“過去的人肉搜索受正義感的驅使,而現在不少網民是在發泄情緒。”貓撲網站管理員說,該網站是國內最早出現“人肉搜索”概念的互動社區。“如今網絡確實越來越發達,任何信息都有被公布的可能。”管理員對此表示擔憂。
“人肉搜索”也是國際難題
在美國,媒體為表達中國的“人肉搜索”,專門創造了一個短語“Chinese style internet man hunt”(中國特色的網上追捕)。這是在濫用言論自由和網絡的力量,以匿名方式聚眾一逞一己之快意。
事實上,“人肉搜索”并不僅僅在中國網絡中出現,在今年的國外網絡中,“人肉搜索”也成為一個顯著的現象。
2014年8月23日的英國《英中時報》披露,在英國紐卡斯爾兩名中國留學生被殺事件迅速告破,很大原因要歸功于英國華人留學生論壇發動的“人肉搜索”行動。
而在美國,一段網絡視頻引起的“人肉搜索”行為甚至引起了美國軍方的注意。在YouTube網站的這段視頻中,一名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笑著把一只約八周大的小狗扔下懸崖,小狗落崖時的凄厲吠聲激怒了無數美國網民。
一些美國網民利用“人肉搜索”,直接公布了虐狗士兵的姓名、身份、年齡、駐地、電話號碼、轎車照片等詳細的個人信息,并掀起了對他的聲討活動。迫于民意壓力,美國軍方展開調查,海軍陸戰隊不得不聲明作惡者有悖“海軍陸戰隊員被期許的高標準”。
在韓國,“人肉搜索”同樣在網絡上掀起了滔天巨浪。今年7月,韓國網絡中圍繞“警察是否過度鎮壓反對進口美國牛肉的示威”的問題議論紛紛,在此情況下,曾被投入到示威現場的韓國警察遭受了接連不斷的“網絡通緝”。
“那幾天,韓國門戶網站Daum的論壇里出現了首爾一位警察的姓名和照片,還有個人主頁。”韓國留學生王鈺說,“很多韓國網民登錄警察的個人主頁發表了很多‘詛咒一樣的謾罵。”不過,韓國網民并沒有就此收手,他們還訪問了該警察的個人主頁上鏈接的親友主頁,一并進行了辱罵和威脅。
刑事立法可行嗎?
“人肉搜索”是科技高度發展和網絡迅速普及的產物,自其誕生之日起,就受到廣泛爭議,在起到對社會監督作用的同時,又如同一把利劍,窺探著公民的私人空間——網絡隱私權。“人肉搜索”孰是孰非,大家各持己見,但可以肯定的是,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環境中,“人肉搜索”已沖破法律的底線,危害到他人的合法權益。近年來,“人肉搜索”侵權案件在頻繁發生的同時,也暴露出了諸多問題。到底是否要進行法律規范,引發了人們的熱議。
有人認為,“人肉搜索”與監督渠道不暢有關。與傳統媒體相比,網絡輿論的公共論壇確實是復雜的,但在嘈雜中,往往傳遞著較為真實的底層聲音。公權力不僅僅要保護大多數人利益,少數人的權益也要得到法律的保障。法治的精髓是用法律規范政府的行為,監督政府不超越職權,不濫用職權。眾多網絡話語平臺的建立,使公民表達意見的門檻與成本降低,通過網絡社區集合廣大網民的力量,追查某些事情或人物的真相與隱私,并把這些細節曝光。人肉搜索從一定意義上推動了監督體系的完善。
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何海波表示,將“人肉搜索”納入刑法目前來說還不成熟,“在《個人信息保護法》立法起草工作尚未啟動的情況下,個人信息的保護范圍難以得到明確界定,僅有刑法的規定還遠遠不夠。”
中國政法大學刑法學教研室主任薛瑞林說,“人肉搜索”刑事立法可行性不高,“民法可以解決的事情,不必上升到刑法的高度上去,刑法不是管家婆,別什么事情都找它。”
中國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研究員王鳳翔則認為,應推進個人數據立法,“歐盟于1995年制定了歐盟數據保護指令,要求各成員國必須在遵守隱私的基本價值和尊重信息在國家間自由流動兩者之間達至平衡。美國則通過行業自律和判例法并配以單行立法來實現對個人數據的保護。”
王鳳翔說,“當司法很難介入時,以網站為主的傳媒業內人士,應該有起碼的底線意識:保護涉案人員的個人信息,避免直接評價誰對誰錯,平撫公眾的無謂憤怒,引導多角度的信息解讀。”
“人肉搜索”立法是社會進步
《中國青年報》在6月30日的一項調查大概可以看出部分民眾的心態,在2491名調查對象中,有79.9%的人認為“人肉搜索”應該受到規范,65.5%的人認為“人肉搜索”可能成為一個新的發泄渠道和報復窗口,而64.6%的人認為這侵犯了個人隱私,而20.1%的人擔心自己會成為搜索目標。
2014年8月25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審議刑法修正案草案時,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作委員會主任朱志剛提出“網上通緝”“人肉搜索”等嚴重侵害了公民基本權益,其危害甚至比出售公民個人信息更為嚴重,有必要追究“人肉搜索”者的刑責,建議在刑法中予以規范。
新司法解釋的一大亮點就是,它首次明確了個人信息受法律保護的范圍,包括:基因信息、病歷資料、健康檢查資料、犯罪記錄、家庭住址、私人活動等個人隱私和其他個人信息。若是未經允許發布他人的上述信息,就是侵權了。
誠然,開放的網絡平臺給了公眾“發言”自由,但也應有“度”的限制。現代社會是一個崇尚理性、多元與寬容的“陌生人社會”,與傳統的“熟人社會”不一樣。由于人們來自于不同的道德共同體,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道德觀與價值觀,故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應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為原則,即便對于他人的道德觀與價值觀并不認同,仍需以寬容的心態和最基本的尊重對待。
現代社會是以法律,而不是相對一元化的道德來調節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未經當事人同意的“尋人啟事”式“人肉搜索”是建立在對他人不尊重的基礎上的,而“通緝令”式的“人肉搜索”卻更是建立在對他人道德觀與價值觀的不寬容基礎上的。如果我們的社會放縱這種建立在非理性情緒基礎上的“網絡暴力”,任其發展,而不是將之納入理性與法制的軌道,將造成巨大的社會危害,嚴重威協到每一位公民日常生活的安寧,每個人都可能成為它的受害者。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人肉搜索”是現代信息技術與中國傳統的一些社會弊病,如缺乏法制意識、權利意識與對他人權利的尊重,缺乏寬容、法制不健全、道德一元化等結合的產物。正因為如此,對“人肉搜索”為代表的侵犯公民“隱私權”之類的行為進行立法,是一種社會進步的表現。
(編輯·韓旭)
hanxu716@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