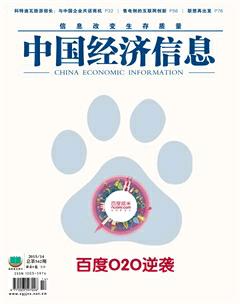存貸比落幕,還權于市場
賀佳雯
6月24日,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李克強總理宣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修正案(草案)》。草案刪除了貸款余額與存款余額比例不得超過75%的規定,將存貸比由法定監管指標轉為流動性監測指標。
銀行業活躍二十年的存貸比就此落幕。它也曾對銀行風險控制發揮積極作用,卻逐漸對銀行的市場化產生限制。存貸比何時開始松動?商業銀行“斷尾”存貸比后,對市場有怎樣的影響?能否符合中央刺激實體經濟的預期?
計劃經濟時代的遺產
存貸比,即銀行貸款余額與存款余額的比例,因而又被稱為“貸存比”。1994年存貸比指標在部分股份制銀行中推行的資產負債管理試點提出。現行中國《商業銀行法》于1995年5月10日由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通過,后根據2003年12月27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的決定》修正。其第三十九條規定,商業銀行貸款“貸款余額與存款余額的比例不得超過百分之七十五”。
一定程度上,存貸比可看做是20世紀90年代計劃經濟時期的遺留產物。
據中國人民銀行原副行長吳曉靈介紹,最初制定75%的存貸比是為了給當時新設立的交通銀行貸款自主權。那時銀行在貸款方面實行計劃指令管理,而給交通銀行75%存貸比的管理,可使其按照這個比例有彈性地實現貸款規模。
“國有專業化銀行商業化改革開始的時候,信貸過快增長,貸差嚴重——貸款多于存款,不得不依靠向中央銀行再貸款來滿足企業旺盛的貸款需求及存貸款資金缺口。”銀率網銀行分析師閆杰向《中國經濟信息》記者分析存貸比應運改革而生的時代背景。
《商業銀行法》實施之初,銀行還不是完全市場化的經營主體,作為商業銀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重要指標的存貸比,能夠有效地管理流動性風險,并控制貸款,對銀行的穩健經營是有幫助的。
隨著銀行市場化發展,計劃經濟時期過于統一化和行政化的管理規則顯然已經有些格格不入。各家銀行情況不一樣,對于資產匹配以及流動性管理的需求也不同,而存貸比為商業銀行設定統一上限,多少有些捆綁商業銀行放貸的步子。
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FSI)副所長趙錫軍接受《中國經濟信息》記者采訪時指出,近十年來,由于資產負債多元化,存貸比監管覆蓋面不夠、風險敏感性不高的弊端日益顯露。
“銀行作為商業化的金融機構,一方面監管機構要求銀行能夠做到自主經營、自擔風險、資金平衡、自負盈虧。但另一方面,又有存貸比的限制,其實二者是相矛盾的。”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向《中國經濟信息》記者解釋,計劃經濟年代,國家認為商業銀行的自主經營能力不足,擔心放開限制,會造成銀行盲目放貸,甚至將市場上拆借來的資金用于放貸。
但目前看來,商業銀行的發展日趨成熟。一方面銀行作為完全市場化的商業主體,自負盈虧本身會讓銀行惜貸。另一方面,隨著存款保險制度的建立,一旦銀行盲目放貸出現問題,還有制度兜底。即使銀行倒閉,也完全可以按照既定的清算流程處理,不會造成市場恐慌。
郭田勇將存貸比造成的最大問題歸結于束縛銀行的自主經營,特別是隨著互聯網金融、金融脫鉤脫媒等外圍環境的不斷沖擊,很多銀行的存款不斷流失,在存貸比的限制下,容易陷入困境。
有些銀行在金融競爭中創新能力增強,通過金融市場進行資金拆借或者發債來融資,但按照存貸比規定,通過這些途徑獲得的資金不能用于發放貸款。這對銀行在轉型背景下進行業務創新,從而形成的信貸投放能力,就沒有予以肯定。
這導致兩個市場出現了背離現象:一個是銀行自身的反差,即存款壓力越來越大,存款成本不降反升。二是銀行之間的反差,即市場利率逐步走低,卻無法有效傳導到存款市場,實體經濟得不到貸款支持。
正如黃金被經濟學大師凱恩斯稱為“野蠻的遺跡”,而存貸比作為計劃經濟時代的遺產,也到了退出歷史舞臺的時刻。
新規與國際接軌
存貸比的弊端根深蒂固,取消存貸比看似一夕之間,實則早有苗頭。
其實從2009年存貸比就已經開始“放水”。是年中國銀監會發布《關于調整部分信貸監管政策促進經濟穩健發展的通知》,允許部分中小銀行適當突破存貸比。
此后,存貸比指標又經歷幾次重大調整。其中,2011年存貸比指標被改為日均數監管;2014年銀監會再次調整了存貸比計算口徑,分子(貸款)扣除六項、分母(存款)增加兩項。分子扣除符合條件的債券,分母增加尚未開始發行的銀行對企業和個人的大額存單。
不少銀行業內人士以“方向正確,力度不足”來評價此舉。據銀監會發布的監管統計數據,調整近一年后,中國銀行業流動性水平相對充裕。
截至2014年12月末,商業銀行流動性比例為46.44%,較年初上升2.42個百分點;人民幣超額備付金率2.65%,較年初上升0.11個百分點。2014年12月末,調整后人民幣口徑存貸款比例(人民幣)為65.09%。
從今年5月發布的一季度數據觀察,銀行業流動性水平繼續保持充裕。2015年一季度末,商業銀行流動性比例為47.46%,較上季末上升1.02個百分點;人民幣超額備付金率2.30%,較上季末下降0.35個百分點;存貸款比例(人民幣)為65.67%,較上季末上升0.58個百分點。
在趙錫軍看來,存貸比的限制對商業銀行早已有些形同虛設。存貸比對銀行的監管是有時點的階段性抽查。
每到月末、季末,銀行為了讓存貸比能達標,便到處高成本拉存款。無論央行宣布存款利率上限上浮至1.1倍、1.3倍還是1.5倍后,一旦脫離輿論壓力,商業銀行很快會彈簧般地反彈置頂。銀行之間搶占資金盛行一時,導致市場資金利率劇烈動蕩,一度鬧出“錢荒”。endprint
也有為存貸比傷透腦筋的,比如進入中國注冊的外資銀行,由于很多國家沒有存貸比這一規定。一些外資銀行本在國外經歷更嚴格的監管,但面對中國本土化的存貸比監管仍有心無力,甚至冒出兩三百的存貸比數據。幸而銀監會拋出五年寬限期,在收縮貸款拓大存款等手段之下,外資銀行法人機構基本在2011年底達標。
對此,也有監管人士透露,中國銀行業遲早都要融入到國際規則中。《外資銀行管理條例》中,對存貸比指標的表述其實是有彈性的,為“外商獨資銀行、中外合資銀行應當遵守《商業銀行法》關于資產負債比例管理的規定”。“這就預見了存貸比指標肯定會被取消的問題,避免未來還要跟著修改。”他推測。
吳曉靈同時作為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在今年兩會期間她贊同修訂《商業銀行法》,對存貸比指標進行調整,主張用巴塞爾協議III的流動性覆蓋比例和凈穩定資金比例替代。
2014年2月,銀監會正式發布《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辦法》,根據國際早已應用的巴塞爾協議III要求,引入了新的流動性風險管理指標,流動性覆蓋率(LCR)。
閆杰解釋,流動性覆蓋比率指標考核,可以確保單個銀行在監管當局設定的流動性嚴重壓力情景下,能夠將變現無障礙且優質的資產保持在一個合理的水平,這些資產可以通過變現來滿足其30天期限的流動性需求。
巴塞爾協議III還提出另一個流動性指標:凈穩定資金比率(NSFR),要求可用穩定資金來源與業務所需穩定資金的比率要求大于100%,其分子包括存款、資本金和發行長期債券等可用穩定資金,分母包括貸款、投資,是關注長期風險的指標。
NSFR與存貸比的原理相似,只是分子分母顛倒。主要考核銀行長期穩定資金來源是否可以支撐其表內外資產業務發展。據閆杰分析,這項考核有助于推動銀行使用穩定的資金來源,支持其資產業務的發展,從而降低資產負債的期限錯配。目前巴塞爾委員會仍在修訂NSFR,有望年內定稿。
“新規巴塞爾協議III已經能覆蓋存貸比的監管面,甚至更為全面,在風險控制上敏感神經更細,也更符合國際化要求。”趙錫軍說。此次完全取消存貸比,時機成熟。
對刺激實體經濟作用有限
存貸比紅線一取消,市場不乏歡呼叫好聲。尤其表現出興奮的是一些股票分析師,認為取消存貸比,銀行貸款額度增加后會提升銀行盈利水平,銀行會釋放出巨量資金也利好股市。
業內人士則顯得比較冷靜。他們認為短期看,銀行信貸投放大幅增加的可能性不會太大,不必擔心造成流動性過剩,更不可能存有“大水漫灌”的顧慮。
目前存款仍是銀行負債的主要來源,貸款也是銀行的主要資產業務,存貸比仍會作為重要的流動性監測指標,對銀行的信貸投放構成一定程度約束。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員蘇培科透露,今年1月他在參加國務院法制辦向學者專家征詢關于存貸比指標從商業銀行法去存的意見會議上,曾表達自己的意見是:“用法律硬約束企業的經營管理標準似乎欠合理,可適時增加其彈性和及時調整指標參數,但在銀行監管和銀行經營管理軟約束方面決不能放棄對該指標的監測和參考。”此觀點獲得在場大部分學者專家的支持。
眾所周知,從當前經濟形勢來看,中國經濟下行壓力較大,需要更為寬松的融資環境。
還權于市場,提高市場資源配置和商業銀行自我經營管理能力,是銀行業內關于取消存貸比的影響普遍給予肯定態度的。但正是因為市場化的進一步增強,銀行能否聽命于中央,將更多資金投入到實體經濟當中?
“其實與是否取消存貸比,壓根沒關系。”趙錫軍解釋,從商業銀行盈利角度來看,信貸投放還受到資本充足水平、風險偏好、行業投向指引、信貸需求狀況等因素的影響。在目前經濟下行、企業有效信貸需求不足、銀行資產質量壓力較大的情況下,銀行自然會綜合考慮、統籌兼顧,穩健經營,因而此舉并不會導致貸款投放大幅增加。
申銀萬國證券也分析稱,目前銀行惜貸更主要是受中國經濟疲弱、銀行壞賬壓力大增、有效融資需求不足等因素的影響,并非是受存貸比的制約。
今年以來,央行持續釋放流動性,但銀行的信貸規模并沒有盲目擴張。
據銀率網向《中國經濟信息》提供的數據來看,5月末人民幣貸款余額87.52萬億元,同比增長14.0%,當月對實體經濟發放的人民幣貸款增加8510億元,同比少增281億元。
銀行業金融機構對實體經濟的信貸投放依然謹慎,并沒有因為寬松的貨幣政策而顯著擴大投放規模,郭田勇推測這主要是因為經過上輪改革后的發展,銀行業的經營漸趨成熟。
給銀行存貸比松綁,是為了不讓商業銀行的發展受政策所累,改革時點到了,取消法定約束水到渠成。但其實這一指標并不是貸款對實體經濟支持不足的主要因素。“實體經濟減少中長期貸款依賴的主要原因是企業家對未來經濟預期悲觀和貸款資金成本太高有關,核心還得降低社會融資成本。”蘇培科強調。
至于此舉是否利好中小企業貸款,趙錫軍表示相信存貸比從監管指標變為監測指標,長期發展將會形成貨幣政策的有效傳導機制,會有效地降低資金成本,包括存款的資金成本、貸款的融資成本。但根據企業、項目自身的不同情況,商業銀行自有評估,融資難度也會有不同回應。
取消存貸比能否代替降準,反哺實體經濟,業內普遍持觀望態度。對中小銀行而言,能有更多資金放貸于中小企業,基于中小企業更大的貸款利率浮動空間,中小銀行的盈利能力在未來或有所提高。招商銀行評論稱預計后續中小銀行貸款投放能上一個臺階,進一步刺激信貸投放。但此舉能否替代降準,仍難以確定。
申銀萬國證券認為流動性釋放仍需降準。取消存貸比對解決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幫助有限,仍需央行有步驟的下調存款準備金率,釋放流動性,以支持實體經濟發展。
從宏觀角度分析,閆杰認為取消存貸比對國有大行正在孕育的改革以及地方債置換,其意義更大。新一輪的銀行改革需要的是更大的資金運作空間,新一輪的國企改革需要消化或展期大量債務,存貸比取消在一定程度上會滿足這種需求。
長遠來看,存貸比監管取消是我國整體金融體系改革的一部分,有利于優化和完善金融監管,促進社會融資結構多元化。對商業銀行而言,此舉還將促進銀行負債結構進一步多元化,引導銀行優化資產負債配置,推動銀行改變業務結構和轉變經營模式。趙錫軍認為,取消存貸比后,中國銀行業總體流動性仍將保持相對充裕和健康的水平。
編輯 張興軍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