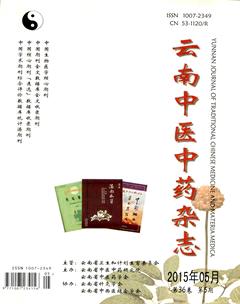彝族醫藥歷史源流探討
羅艷秋 鄭進 徐士奎等
摘要:本文通過對占有史志資料的理解,對彝醫藥的歷史源流進行初步梳理,按照歷史沿革,分為六個時期,即百濮醫藥時期、爨蠻醫藥時期、鄉土醫藥時期、滇醫滇藥時期、中草醫藥時期和彝族醫藥時期。
關鍵詞:彝族醫藥;歷史;源流
中圖分類號:R29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7-2349(2015)05-0014-05
無論是查閱彝、漢史志文獻,或者是考查碑文墓志,字里行間諸如“忘形宇宙之中,寄傲羲皇之上”的彝人情結,不時感動著我們,深感彝族文化淵源之久長,內涵之博大。為了追溯鳳毛麟角的彝醫史實資料,以利全面認知彝醫,正確估價彝醫在彝民族發展的歷史進程中所擔負過的任務和所起到過的作用。本文通過對現存史志資料的理解,對彝醫藥歷史源流進行初步梳理,按照歷史沿革,大致分為六個時期。
1百濮醫藥時期
陳毓芳在《五華文化史話·云南醫藥文化溯源》一文中說:“云南醫藥最早的記載,還是反映在公元前11世紀起西周時代史實的《逸周書》,《逸周書》中已有云南濮人向周王朝進獻丹的記載。”[1]且所獻物必是“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必易得而不貴”[2],意思是說百濮所獻的叫做“丹”的藥物是百濮人居住地域所產之物,而非其他地方得來的藥物。丹,是提煉過的藥物,是藥物劑型——丸、散、膏、丹、湯之一。[3]以上史實說明了兩個問題:一是百濮人會提煉丹,二是丹的用材產自本地。
百濮,亦稱“濮人”、“卜人”,最早見于《尚書·牧誓》,為商周時的八個少數民族之一,分布在“江漢之南”或楚國之南。[4]即所說的江漢之“濮”,散居楚西南及夜郎、牂牁一帶。[5]總的來說,百濮是從江漢平原到云貴高原都有分布的一個古老族群。[6]川、滇、黔、桂彝族各支系的自稱是有共同特征的,大部分自稱中都有“濮”及與之口音相近的“潑”、“撥”等,如諾蘇濮、濮拉潑,《西南彝志》中有“武濮所”的記載。彝族與古“濮人”有淵源關系,彝族自稱中的“濮”、“潑”、“撥”是古“濮人”之“濮”在彝族文化中的延續,史志中亦有“哀牢夷”即永昌“濮人”的記載。[7]云南古代民族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頻繁的分化和不斷的融合,以近代的彝語支民族來說,如果追溯他們的歷史,則很少有一成不變的單一民族,彝族是由古代的“羌”、“濮”、“哀牢夷”融合而成。[8]從以上史料著眼,我們并不難理解“濮人”是當代彝族的祖稱這一事實。彝藥在百濮時期就已鵲起,也是可信的,沒有一定的使用經驗是不會有“丹”的出現的。
2爨蠻醫藥時期
爨夷或爨蠻,是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不同的階層,對哀牢王國到南詔這段漫長歷史時期的他稱。由于歷史的原因,到目前雖然尚未發現哀牢王國到南詔政權的這個時期的彝文醫藥典籍,但是通過為數不多的漢文書籍《蠻書》、《南詔野史》、《云南志略》、《大理行記》等可以找到爨蠻時期彝族醫藥的片斷史料。這些漢文書籍記載了爨蠻時期彝區特產的藥材,如《蠻書》中記載了唯一用彝語記錄的藥物“護歌諾木”,“護歌”是彝語“腰腿”,“諾”是彝語“疼”。[9]王正坤在他編著的《彝醫攬要》一書中把它的基原定為Schisandrapro pinqua(Wall.)Baill.var.sinensis Oliv,現今彝醫用它治療“跌打損傷,風濕麻木,筋骨疼痛”。[10]此外,還有藤彌、孟灘竹、琥珀、犀、大蟲、麝香、沙牛等動植物藥的記錄。
這些彝區特產的藥物通過蜀身毒道、茶馬古道等通道同內地開始了廣泛的交流和貿易。宋代周去非所撰的《嶺南代答·邕州橫山寨博易場》中講到:“蠻馬之來,他貨亦至,蠻之所賫,麝香、胡羊、長鳴雞、披氈、云南刀及諸藥物”,反映了彝區產藥物大量輸出的情況。中外揚名的大理三月街起始于南詔時期,極大地促進了彝藥的交流。據傳,南詔時期因瘟疫流行,南詔王命子民深山老林中采集各種藥材用以防疫,于是四面八方采集之藥材匯集于大理點蒼山下,時值農歷三月十五,故稱“三月街”,又稱“藥(月)街”。[11]彝史、漢史均有記載的孟節治療諸葛亮三百將士的喉痛處方中的野壩蒿就是三月街售賣的主要藥物之一,直至今日,它是治熱癥(包括瘧疾)和提取治療瘧疾藥物的重要原材料。
爨蠻時期名醫輩出,有史可查的有孟節、楊廣和、杜清源、楊法律、楊正保等。公元225年(蜀漢建興三年),諸葛亮率軍平定云南,因瘴疫所侵,戰斗力大大降低。孟節使用韭葉蕓香草施治獲全愈,在《滇南本草》中有“昔武侯入滇,得此草以治煙瘴”的記載。杜清源為醫學世家,“杜清源祖父杜朝選,世居點蒼山花甸哨。祖輩以牧獵為生,兼通岐黃。至其父杜允忠,允忠常覓藥于葉榆,與段府名醫楊廣和善交,常為廣和尋找諸藥而懂藥千余種,并通藥性。”[12]此外,還有段府名醫楊廣和,南詔醫官楊法律和楊正保的事跡和病案在《大理古佚書鈔》上也有記載。
爨蠻時期醫藥發達,名醫成群的原因可以從兩個方面探索:一是公元749年和754年,唐王朝分別命何履光、鮮于仲通率大軍,“征天下兵十余萬”,抵達南詔,均全軍覆沒,仲通僅以身免。[13]李密陣亡,被俘的士兵,全落籍南詔,其中有不少人原是工匠,習醫者自不在少數,成為南詔醫藥發展的主要力量。一是“宋元時期,上自國主及貴族,下至普通百姓,常常通過官方及各種民間渠道來學習內地的文化,大理國主派遣使臣高泰運到宋朝廷求書,“求經籍得六十九家,藥書六十二部”。[14]這些書籍對于彝醫后來的醫藥發展特別是醫藥理論的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鄉土醫藥時期
明、清時期,朝廷對云南的統治更是苛刻,為了滅絕云南少數民族文化,采取了很多殘酷手段,“傅、藍、沐三將軍臨之以武,胥元之遺黎而蕩滌之,不以為光復舊物,而認為手破天荒,在官之典籍,在野之簡編,全付之一炬。”[15]迫使民族文化消失,醫藥也幾乎瀕臨滅絕。但慶幸的是,明末清初“精通歷算,哲學及醫術的知識分子”根據記憶斷斷續續抄錄的一些文獻,如記載彝醫藥知識的《哎哺啥呃》、《宇宙人文論》、《雙柏彝醫書》、《啟谷署》等一批彝族醫藥典籍,在彝族軸心地區的新平、元江和貴州仁懷、大方等地發掘出。
明朝軍隊攻下云南后,大量移民到云南。在云南腹地實行大規模的移民屯田,先后遷來云南的漢族人口總數遠遠超過當時云南境內人口最多的少數民族。[16]大大壓縮甚或限制了云南土生土長的屬于同一醫藥理論體系的彝族醫、白族醫、納西族醫。[17]為了區別于“中醫”,將世代秉承本民族文化,以家傳或師承為主,在本民族醫藥理論指導下遣方用藥的各民族醫生,叫做“鄉土醫”。事實上,來到云南的中醫久而久之,也不得不使用當地的藥材,解決當地民眾的疾苦。因此,很難區別誰是鄉土醫,誰是“中醫”。
被譽為“神農后裔”的蘭茂在《滇南本草》序文中說:“余將已學種種草本,著之于書”。說明書中所列品種都是他伸手能及的草本。在這段短文里,值得注意的是:“已學種種草本”中的“學”,向誰學呢,肯定地說是向“鄉土醫”學。由此可以推斷《滇南本草》就是鄉土醫用藥經驗的記錄,起因是鄉土醫不識漢字或識字少,而蘭茂是文化人,把鄉土醫使用的藥物,用文字記錄下來,自然是號稱“滇南鄉賢”的事了,于是就催生了《滇南本草》。這種系儒醫于一身的鄉土醫在云南很普遍。使用中藥為主的中醫和使用草藥為主的鄉土醫相互借鑒共同治療病人,加速了中醫和草醫同化步伐,統稱鄉土醫,這就是《滇南本草》中收載有大量彝區地產藥材的原因。
此外,清雍正年間被召進京城為皇家醫病,去世后被云南楚雄彝族人、漢族人尊為女神,建廟供奉的準塔娃。[18]清朝雍正六年創制撥云眼藥錠和撥云復光散的通海人沈育柏,清朝同治四年創制黑藥、紫薇膏的江川人侯萬春、格勒婆,清朝光緒二十一年創制萬應丹(無敵丹)的江川人王萬祿,清朝光緒三十四年把開設在玉溪的“成春堂”遷到昆明,出售玉溪地產藥材的峨山人彭寂寬等。[19]無一不是鄉土醫藥的代表人物。
4滇醫滇藥時期
1914年曲煥章按照其師父袁恩齡、姚洪鈞傳授的處方結合滇南鄉土醫生的配方研制出百寶丹。1916年呈送云南省政府警察廳衛生所檢驗合格,允許公開銷售。[20]1923年曲氏獲贈云南督軍唐繼堯書寫“藥冠南滇”的匾額。1926年,云南地方政權將其定為滇藥,當年在東陸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成立滇醫部,教授滇醫滇藥,委任曲煥章為滇醫部主任。江川人侯萬春、王萬祿后人也不斷完善“云南黑藥”的配方長期經營滇藥,如萬應丹、紫薇膏等。從此,滇醫滇藥在全國享有盛譽,馳名中外。建國后的1956年,國家批準建廠生產的云南白藥,前身就是曲煥章按照彝醫配方創制的百寶丹。如今,云南白藥已成為彝藥代表品種,廣泛用于內、外、婦各科疾病。
在這個時期,祖傳或師承的鄉土醫大都以滇醫滇藥的名號,在各自所在地開堂行醫,堂號名目繁多。如昆明的“福元堂”、“大安堂”;經營大宗云南地產藥材的“臨泰號”、“德豐號”。有些鄉土醫以師承方式培養滇醫人才,充實滇醫力量。如“元江縣洼垤區羅垤村李仕甲,精于內、外、婦、兒諸科。民國二十九年,招收了本村李長生和白村的李開文、白佑三等人為徒,傳授滇(彝)醫技術,一代一代的延續。1963年全縣吸收6名滇(彝)醫為全民所有制人員,在縣內各醫療點位行醫。1969年又吸收了滇(彝)醫出身的醫生為各大隊合作站醫生,他們主要以彝族醫療技術和藥物服務于各族群眾,深受群眾愛戴。”[21]可以證實當年大力提倡的滇醫滇藥其實就是彝醫彝藥,使彝醫彝藥為群眾健康服務,是符合民情民意的。李孝友在《昆明風物志》中寫道:“大板橋白土村少數民族醫生周文斌,精外科,專治跌打損傷,處方不類常醫,專用祖傳草藥,無不湊效如神。”大板橋一帶,居住著子君人、傒卜人,也叫‘撒馬幫,這些都是彝族的支系。[22]正是因為云南各民族中形成了各族一支自己的醫技超群、經驗豐富的民族醫療衛生力量,給各族群眾提供了看病吃藥的方便條件。這個時期,云南除了江川的曲氏、候氏、李氏,通海的沈氏,還有巍山的朱氏,元江、新平的李氏,宣威的何氏都是滇醫滇藥世家,在當地有很高的名望,可以說是有口皆碑。
5中草醫藥時期
云南省中醫中藥研究所民族醫藥研究室的施文良在《云南民族醫藥遺產的繼承和發展》一文中寫道:“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全省性的大規模‘中草藥群眾運動,推動和促進了民族醫藥的調查、發掘、整理工作的開展,全省共整理編印了十二個(十五冊)全省或地區性的版本,收載藥物2300余種,方劑數千個,這些藥物絕大多數均產于民族地區,也是當地民族長期所言傳習用的,為服從‘運動主題,這些品種大都冠以漢名或植物名,沿襲中藥性味、功能等格式撰寫,只有部分品種載列了使用民族的藥名及用藥經驗,雖然如此,也為我省民族醫藥的發掘、整理工作,奠定了極為寶貴而又豐富的基礎。”[23]從這段話我們可以看出,中草藥群眾運動是特殊歷史時期民族醫藥挖掘整理研究和發展的另一種手段。確切地說,中草藥中的草藥指的就是民族藥。彝族醫藥經過這個時期也得到了很大提升,許多珍貴的珍善本彝文醫藥典籍得以發掘和整理,許多彝醫沿用的藥物品種及其臨床經驗得以系統地整理和應用。
除了《云南中草藥選》、《昆明民間常用草藥》、《玉溪中草藥》等書籍記載了大量彝族習用藥材之外,還有《彝藥志》、《哀牢山彝族醫藥》、四川的《彝族醫藥》等記載彝藥的專書相繼問世,顯然,這個時期的中草藥運動為彝族醫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一大批出生于民族醫藥世家的在職醫藥衛生人員也得以大顯身手,多數參與了“中草藥”的調查、采挖和資料編寫。如白族的王正坤,彝族的黃傳貴、方文才、李學恩、阿子阿越、李國森、王榮輝等。這個時期對包括彝族醫藥在內的民族醫藥的發展,可以說是飛躍式。主要的收獲有三點:一是培養壯大了隊伍;二是摸清了藥物家底;三是加速了民族醫藥在國內國外的交流。
6彝族醫藥時期
根據衛生部1977年衛藥字第444號文件,全國的藥檢系統開展了民族藥的普查工作,并著手編寫《中國民族藥志》一書。1977年版《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收載了民族藥藥材32種。同年,《云南省藥品標準》收載了民族藥75種。1992年,云南省玉溪地區藥品檢驗所牽頭完成的《彝族醫藥文獻發掘研究》科研課題獲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科學技術進步獎,彝族醫藥和藏、維、蒙、傣、朝醫藥一樣被歸入國家職能部門的文書檔案。199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下發了(1993)第64號文件《關于制定民族藥部頒標準的通知》,該文件中說:“民族藥是我國傳統醫藥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使民族藥管理規范化、標準化和科學化,以便進一步提高傳統藥物的質量,保證人民用藥安全有效,振興和發展民族醫藥,我部決定制定民族藥部頒標準。”文件還明確規定云南省衛生廳負責彝藥標準的制定,復核和初審工作。從那時起,云南省衛生廳集中力量先后制訂了137個彝藥標準,這些品種先后投入生產。2002年2月以后,先后研制的如降脂通脈膠囊、腸胃舒膠囊、恒古骨傷愈等150多種彝藥升為國家標準。從此,彝藥納入國家職能部門管理,而“民族醫藥”一詞也隨之出現在中共中央、國務院文件中,彝族醫藥為解除人類疾疫病痛提供了技術支撐。
從百濮、兩爨、南詔、大理、后大理的史志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到彝醫藥始終沒有偏離彝族文化、彝族信仰、彝族習俗以及彝族居住的地形地貌、天候氣候等這些根本的社會元素和自然元素,離開了這些元素,彝醫藥也就沒有根基了,也就不能稱其為彝醫藥了,這是彝族文化孕育的結果,沒有彝族文化,就不會有彝族醫藥。因此,我們認知彝族醫藥的時候,一定要遵從彝族文化。
致謝:本研究得到了獲得民族醫藥科技進步獎傳承貢獻一等獎項目《彝族傳統醫藥知識體系的挖掘整理與傳承研究》、部級獎項目《彝族醫藥文獻發掘研究》第一完成人;西南地區優秀圖書獎書目《彝醫攬要》作者王正坤先生的指導,特此致謝。參考文獻:
[1]桂云劍.五華文化史話[M].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08:428.
[2]黃懷信.逸周書校補注譯[M].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6:333.
[3]王堯清.中國膏藥學[M].西安:陜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81:1.
[4]陳永齡.民族辭典[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7:1245.
[5]張福.彝族古代文化史[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9:76.
[6]馬曜.云南簡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27.
[7]李相興.彝族與古濮人關系論析[J].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20(3):69.
[8]張福.彝族古代文化史[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9:87-88.
[9]王正坤.彝醫攬要[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4:199.
[10]王正坤.彝醫攬要[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4:199.
[11]大理白族自治州醫藥管理局編.大理州醫藥志[M].1992:211.
[12]大理州文聯.大理古佚書鈔[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332-333.
[13]云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集刊[C].1986:235.
[14]馬曜.云南簡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85.
[15]師范.滇系·典故系天.南詔與白族文化[M].北京:華夏出版社,1992:79.
[16]馬曜.云南簡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19.
[17]陶云逵,方國瑜.納西族歷史參考資料[M].1934:8.
[18]云南社會科學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主編.彝族文化,1998,(4):22.
[19]王正坤.彝族驗方[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7:7.
[20]鄭世文.萬應百寶丹及其他“白藥”.江川文史資料[M].1989:22.
[21]玉溪地區衛生志編纂委員會.玉溪地區衛生志[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1995:527.
[22]李孝友.昆明風物志[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75.
[23]施文良.云南民族醫藥遺產的繼承和發展[J].云南中醫雜志,1989:10(1).36-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