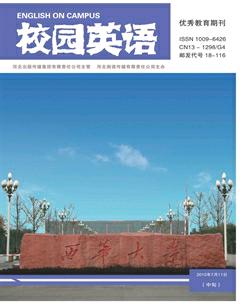美學視角下的古典詩詞英譯研究
孫陽 王古月
【摘要】詩歌作為民族文化的精華,其翻譯也至關重要。本文從美學的視角探討了詩歌的英譯,主要介紹了中國傳統議論中幾個重要的美學命題以及詩歌美的具體體現。將理論與翻譯實例結合,欣賞詩詞英譯的魅力,同時為今后的詩歌翻譯提供一定的思考。
【關鍵詞】美學 理論 表現
艾青說過:“一首詩的勝利,不僅是它所表現的思想的勝利,同時也是它的美學的勝利”,顯然,古詩詞的魅力首先是美的勝利。在準確表達古典詩詞的原意時,我們更要重視古典詩詞的美的傳達。
從總的發展歷史看,中西方譯論從一開始就與美學結下了不解之緣。西方譯論與中國譯論各自處在不同的歷史條件和社會條件下,為翻譯的發展提供了理論淵源。如果說美學在西方譯論史上起到過一定的推動作用,那么在中國,中國傳統譯論都與哲學-美學緊密相連。中國傳統譯論除了借鑒“文與質”等主旨性議題,形成了傳統譯論的主旨性或中心命題以外,還引介了中國傳統美學的審美價值論或審美形態作為翻譯標準。在中國傳統議論中,有以下幾個重要的美學命題。第一是“信達雅”的美學內涵,“信達雅”是嚴復提出來的美學標準。他在1898年出版的《天演論·譯例言》中說:“譯事三難,信達雅。”自此,“信達雅”譯事三難說風靡譯壇,在中國傳統譯學中影響至為深遠。“信”的命題源于老子,在老子的美學思想中,“信”是與“美”相互獨立,互不相容的嚴復則繼承了老子關于“信”的審美價值觀,才將“信”作為首要條件。嚴復指出“取明深義”,“將全文神理融會于心”。后來他又提出一個“誠”字,與“信”相呼應,合為“誠信”,非常符合儒家的“倫理美”原則。為了達致對原文的“誠信,事信”,嚴復又提出了“達”的主張作為一種手段,也就是他所說的“為達,即所以為信也”。在思維表達中,“達”確實與說理有很密切的關系,就是《呂氏春秋》中所說的“理塞則氣不達”。這里的“達”也就是通順。可見嚴復在譯論中引介“信達”,都是承前人之至理,秉乎中國文藝美學思想傳統之旨意使然,即所謂“推陳出新。三難之說其實也就是翻譯思想,它的特征在于雅,在嚴復的翻譯美學觀中,“信達雅”是三環聯袂的統一體,他首先提出了“信”,要做到“信”,就必須“達”。要做到達呢,他提出的途徑是“雅”。嚴復所謂雅,用孔子的話來說就是“文采”,“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中國譯學傳統譯論中的第二個重要命題就是馬建忠首推的“神”與“形”,“神似”與“形似”。他認為,得原文之神情,又能擺脫原文句式的束縛,而達致“心悟神解”,才談得上“善譯”,可見在馬建忠的心中,翻譯離不開“神”的運作。但是將“神”與“形”,“神似”與“形似”化為一對相依相濟的矛盾,引入譯學而用于自己的翻譯實踐,標舉闡發的第一人是傅雷。他提出“重神似而不重形似”論,移花接木自中國古典文藝美學,借他山之石,倡譯學新論,影響深焉。從他本人的譯注水平看,大體無愧“形似”兼“神似”之旨,得力處可謂“以神馭形”。必須說明的是,中國古代美學觀“重神似而不重形似”是一種相對的說法。“神似重于形似”的真諦就是在藝術表現上不追求淺表層的,單純的形似,而是以神馭形,神形兼備為理想。以達致摹寫外物與主觀審美相契合的精神特質,也就是劉勰所說的“情采”:神動于中而生情,情發乎外而多采”。
第三種是錢鐘書提出的“化境”,也就是所謂的“以境論藝”。蘇東坡主張“境與意會”,王世貞提出“神與境和”,可見“境”是寄遇藝術情思的一種超越凡俗的依托。錢鐘書以“化境”論是翻譯秉承了中國傳統藝術論之論旨,以“化入”為主旨的精美而不留痕跡的一種“易語而釋”的高超境界。從總體上來說美學對中國譯論的影響之深遠是世所罕見的,也是世界上任何國家和民族文化都無法比擬的。
站在美學的角度上進行分析中國古典詩歌的翻譯。主要是將譯人語的各種優勢進行創造性的翻譯,這樣一來,譯詩就能夠實現“意美、音美和形美” 的統一。要創作出經典的詩歌翻譯,譯者必須在充分闡釋和重建詩歌內涵的同時努力保持其形式獨特所在。從美學的視角來看古典詩詞的英譯,有利于我們對中國傳統文化有更為更深刻的了解,對古典詩歌永恒的美,永恒的魅力有更加獨到的領悟。
參考文獻:
[1]許淵沖.文學與翻譯[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2]顧正陽.古典詩詞曲英譯美學研究[M].上海大學出版社,2006.
[3]叢滋杭.古典詩歌英譯理論研究[M].國防工業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