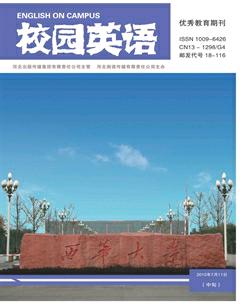美籍華裔的身份困境
方舒
【摘要】趙健秀通過以泰姆為代表的新一代華裔從對自我身份的迷惘、文化沖突的壓力、價值觀念的失落到重新定位自我、尋找自身價值、尋求文化溝通的再覺醒的過程,表達了新一代的美籍華裔只有把自己的男性氣質和祖輩傳承結合起來,才能在美國這個大熔爐里找到皈依感和慰藉性的自我身份的這一主題。
【關鍵詞】《雞舍中國佬》 身份尋求 身份困境 美籍華裔
自從移居到美國,關于自我身份的尋求一直是美籍華裔不可避免的重要問題。對于每一名美國華裔,在中國文化、美國文化、華美文化這三者間作出選擇,是注定無法規避的問題。在美國亞裔文學中,對民族以及文化身份的探討與追尋一直是永恒的主題。美籍著名作家趙健秀在其戲劇《雞舍中國佬》中對于身份尋求的困境進行了深刻的展現與討論。
對第一批美國移民來說,中國傳統文化是他們價值觀念的根基,深深地植根于他們的血肉中,但美國社會嚴酷的生存競爭迫使他們放棄母國文化而試途融入主流社會。華裔女作家譚恩美曾說過:“如果一個人想成為美國人,他不得不放棄中國文化。而一旦這樣做,他便失去了平衡。”尋求文化認同的艱辛和失敗,使這一代移民深切體會到“里外不是人”的尷尬。然而,在美國出生的華裔子女,在身份困境的問題上更為困惑。他們生活在與父母截然不同的生活環境里,接受的是美國文化,在思想上更傾向于接受美國文化與價值觀。但是,無論華裔青年已經被美國化到何種程度,以白人為代表的主流社會依然把他們看作是少數民族,是中國人,關鍵時刻總會對他們采取歧視和排斥的態度。這使得新一代華裔極易產生一種迷茫和身份危機:“我究竟是誰?”
在趙健秀的《雞舍中國佬》中,當香港夢女問主人公泰姆“你在那里出生”時,他說“我來自雞舍”。他成長的中國城,在他眼里就是“雞舍”。“貧瘠、骯臟、墮落之處,那里父親們母親們因為癆病奄奄待斃,孩子們因為厭倦無聊而倍感傷痛、乏味和壓抑。中國人被描寫為爬蟲、蜘蛛、青蛙……干燥土地上喘息著的滑溜溜的魚。社區本身就像殯儀館,一個破敝的展覽館,或是一場慘兮兮的白人扮演黑人的滑稽歌唱表演。”在這個“雞舍”里,充斥著各式各樣的“雜燴”。這些“雜燴”是混亂多元的各民族文化,它們影響著、困惑著泰姆這些華裔青年。他們的出生是被迫的,他們被拋入這個實際上他們根本不愿意降生的少數族裔社區。在中國式家長教育和美式學校教育的雙重影響下,他們越發困惑,表現出強烈的身份危機感。他們以不同的方式企圖擺脫肉體與精神的雙重危機。然而,這些在美國出生的新一代華人子女,因為生活在與父母截然不同的文化環境里,耳濡目染,受著美國文化的熏陶,平時讀的是英文書籍,而非儒家的經典,所以言行舉止、思想理念等都不可避免地更加“美國化”。然而,這種“美國化”其中還蘊含著更深層次的含義。
在劇中,泰姆說話的腔調一會模仿白人,一會模仿黑人,唯獨沒有模仿華人口音,是因為他意識到自己是“文化上的孤兒”,他很困惑迷茫,他沒有自己的語言,他認為華人口音、華人文化低于白人黑人的口音和文化,語言的喪失意味著身份的喪失,語言的自輕意味著文化的自輕。美國華裔試圖通過模仿真正的美國人來掩蓋自己的華裔身份,這種“美國化”實則是忘根的體現。
然而,為什么泰姆會對中國本民族文化產生如此排斥的心理呢?在美國主流意識形態中,泰姆被教育到,中國人溫順而消極,沒有男子漢氣概,而這一點在他的父親身上尤為體現。他的父親是一家養老院的洗碗工,因為怕白人老太太偷窺,他每次洗澡都要穿著內褲。在泰姆看來,這是一個無法承擔教育兒子、引導兒子的有名無實的父親,一個對于敏感而有叛逆精神的年輕一代而言已經缺失或者死亡了的形象。他在本民族的父輩身上沒能找到他所向往的陽剛之氣,所以只好到他的偶像——獨行俠那去尋找他所向往的陽剛之氣。但是當他發現它所崇拜的偶像是一個充滿歧視的白人種族主義者,而并不是美國華裔時,他保留中國人特性的最后一絲信念完全崩塌。美國主流文化對華裔形象的固有偏見、華裔對自身文化的自輕以及對老一代移民價值觀念的不認可和懷疑,導致了年輕的華裔們不停地想擺脫中國文化打在他們身上的烙印,以更好地融入美國主流社會。
泰姆完全放棄了保留自身的中國人特性,想從他的新偶像——杰克的父親身上尋找力量和希望。杰克是黑人拳擊冠軍,這位斗士親口講述了他的英雄父親的故事,那是一位脊背上留有鞭痕以及惡狗咬過的傷疤、堅強而從不屈服的父親。這是理想父親的形象,是年輕而尚嫌幼稚、尚會動搖的叛逆者們獲得鼓舞和慰藉的精神動力之源。他擁有泰姆所幻想的一切特質——強壯、剛健、充滿男子氣概。泰姆堅信,他應該成為這樣的人。然而,當他跑到匹茲堡專程找到杰克的父親——查理后,卻發現理想父親的神話純系編造,是徹底的謊言。查理并不是杰克的父親,只是他從前的教練。關于杰克的比賽戰績和傳奇故事,一大部分都是杰克自己虛構的,而且在比賽中杰克經常是通過陰謀詭計取得勝利。這一切對泰姆來說是個沉重的打擊。從杰克的父親,從黑人文化,從不同文化中找尋力量的希望也破滅了。趙健秀將黑人拳王父親的神話徹底解構,暴露出其某種“反英雄”意識,但也表現出更深層的渴望英雄的焦灼。移民及其后代的父子矛盾,是以父輩的無能與子一代的迷惘而暫告結束的。而這象征性的希望破滅的場景,預示出作家對于前途的深沉困惑:叛逆者自身承受著身份危機的折磨,卻又找不到可以欽佩或敬仰的領袖人物,這一切使得叛逆者的叛逆行為只是一個以背相向的姿態,前途或者出路令人擔憂。
與此同時,泰姆有一個驚人的發現。在他眼中無能、沒有陽剛氣的父親在查理心中卻喜愛拳擊,而且很有尊嚴,查理甚至還很敬重他。這一切,都與泰姆之前對父親的印象與理解完全相反。泰姆對自己之前對父親的偏見產生動搖,在某種程度上,他被杰克的謊言和查理的一番話喚醒,開始意識到老一輩華裔堅毅男性化的一面。他開始承認中國人特性中積極的一面,并一定程度上愿意接受中國文化。在文化尋求的漫漫長路中,年輕的美國華裔們終于看到了本民族文化中閃光的部分。
在最后一幕,泰姆在好友家遇到了前來尋找李的湯姆。湯姆是李的前夫,是一個美國華裔作家。他曾寫過一本料理手冊,但在劇中卻被當作一本來自主宰文化檔案庫的食譜。湯姆和泰姆不同,他太想融入美國社會,太癡迷于被美國社會接受,甚至不惜一切代價。他完全洗去了自己的中國特性,接受了主流價值觀,被美國同化。這實際上已成為背叛種族的典型代表。泰姆對他忘根忘本的行為很是鄙視,卻沒有意識到自己,其實也犯了相同的錯誤。他也在不斷地逃避自己的本族文化,想在其他民族文化中尋找依托,想讓自己的身份擺托中國文化的特性。他將自己尋求身份的希望分別寄托在獨行俠和查理身上,可這一切都讓他大失所望。他終于意識到作為美籍華裔,他不能忘記歷史,忘記過去,忘記自己的根。如果抹殺過去,他們將會變成一群沒有歷史、沒有傳統、沒有身份、沒有根的“浮萍人”,在競爭日趨激烈的多元文化社會中是不可能真正解釋和確定自我的,就會失去自我存在和發展的根基。
該劇體現了作者對美國華裔的文化、屬性和男人氣概的思索,他反對白人種族主義者給華裔規定的屬性,并總結了一些經驗教訓。第一,華裔不能模仿白人或黑人文化;第二,華裔不能被迫接受單純的“美國人”或者“中國人”模式;第三,華裔不能被當作“模范少數族裔”來對待。趙健秀認為,捍衛和堅持純潔的亞裔和華裔美國屬性是關鍵,他反對同胞在美國多元的熔爐中失去了亞裔和華裔的屬性。
中華民族有著燦爛悠久的歷史,上蒼賦予華裔兒女的歷史與文化是無法也不需要抹殺的。對于生活在美國主流文化中的華裔來說,了解中華民族的歷史與文化會使他們有一種歸屬感,使他們覺得自己有了根,有了“底氣”,進而可以在美國社會中保持與主流不同的民族個性,才能挺起腰桿做個華人。新一代的美籍華裔必須把自己的男性氣質和祖輩傳承結合起來,才能在美國這個大熔爐里找到皈依感和慰藉性的自我身份,不再迷惘。
參考文獻:
[1]Wang,Jianhui.Gender & Racial Politics in the Works of Chinese American Women Writers.Qingdao: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Publisher,2011.
[2]Guan,Hefeng.Seeking Identity Between Worlds:A Study of Chinese American Womens Literature.Henan:Henan university Publisher,2007.
[3]程愛民.美國華裔文學研究[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