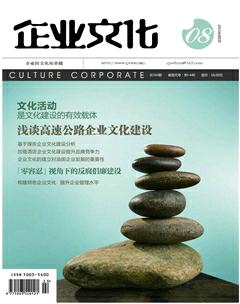淺論國企改革的障礙
摘 要:國有企業改革了這么多年一直沒有重大的突破,我們有必要去分析、探討為何沒有突破的深層次原因以及找到一條出路。在筆者看來,改革所有問題的癥結都在于國有企業與政府的聯系上,與之而來所延伸出的“三重關系”。對于如何處理三重關系才是改革所需要解決的。
關鍵詞:國有企業;三重關系;政府;產權;輿論
生產資料所有制是一個社會經濟制度的基礎,是決定一個社會基本性質和發展方向的根本因素。改革開放三十余年,中國人民圍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有制結構進行了不懈探索,確立了公有制為主,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其中,公有制的實現形式是多種多樣的,而目前,混合所有制是實現公有制最主要的一種形式,而這種形式成敗關鍵在于國有企業的改革,所以,搞好、搞活國有企業事關我國經濟發展、政治穩定、國泰民安。
一、在競爭與合作中前進的國企改革
在國家所有制經濟中,國家作為全民的代表對國有企業的生產資料擁有最終所有權。在所有所有制的范圍內,全體社會成員在生產資料的關系上是平等的。根據這一原則上所成立的國有企業從地位與作用上看,在社會主義國家,國有經濟控制著國民經濟的命脈,對經濟的發展起主導作用,國有經濟的作用不是像資本主義制度那樣,主要從事私有企業不愿意經營的部門,補充私人企業和市場機制的不足,而是為了實現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協調發展,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
國有企業改革是整個改革的重要環節,國有企業改革能否成功,關系國民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全局,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時代發展要求市民社會變革的過程中必須從實際出發。國企改革的初衷不是為了否定國企,[1]而是要讓國企在國民經濟、生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的前提下不斷的變革、調整,而且,國企的缺陷是在與其他性質企業合作、競爭中逐漸暴露出來的。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使我們不斷深化對國有企業的認識,并對國有企業的改革建言獻策。
對內改革、對外開放三十余年過去,楊其靜先生對國企改革的三個階段劃分我個人是比較贊同的:改革之初,試圖解決統收統支的舊體制下企業缺乏積極性的弊端,從而有了放權讓利、撥改貸、利改稅和承包制;20世紀90年代中期,國企在國名經濟中的功能被重新認識,從而有了“抓大放小”的民營化中小型企業的改革;從20世紀90年代末至今,中小型國企的民營化基本結束,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主要內容的大中型國企改革成為關注的焦點。也正是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理論界形成的一個共識,即國企的真正功能在于彌補市場缺陷。[2]
如何達到這一長遠而又務實的目的,現實中存在有三重“大山”,也正是這三重“大山”內部與相互之間的關系已嚴重阻礙了國有企業的改革。
二、改革中的三重關系的制約
由于國有企業在產權歸屬,經營管理,運行環境等方面的特殊性,受多重目標驅使,國企改革開始前,就已重擔壓頂,帶有“原罪”。有關于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的障礙,筆者總結出了一下三重關系。
(一)父子關系衍生產品
國企是目前階段實現公有制的最主要形式,無論是從國有企業設立的初衷,還是近幾年黨中央、國務院出臺的相關文件來看,我們能清楚地認識到,國有企業的成立與發展是為了實現政府的目的。這樣的宏觀布置無論是從歷史還是從現實上來看,達到了兩種效果。從好的方面來看,中國從沒有發生嚴重的經濟危機,因為國民經濟的命脈掌握在政府手里,政府揮動著指揮棒,通過財政與稅收調節經濟發展,同時,國有企業也鞍前馬后,不遺余力地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發展。與此同時,也正是這一關系下,國有企業的投資人是代表全體人民的政府,政府自然有權力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讓國有企業承擔著各種復雜的社會任務,反過來,當國有企業遇到困難時,也轉而訴諸于政府的公權力來解決現實中存在的問題,這是第一組相互關系。
還有一些屬于歷史遺留問題,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國有企業的行政級別,這雖然是計劃經濟的產物,但同時也是國有企業改革的阻礙。對于這樣一種局面,究竟是利大于弊呢,還是弊大于利?筆者嘗試討論一下。行政級別使政府與國有企業之間架起了一道橋梁,有些國企管理者集企業管理者與行政官員兩重身份于一身,在兩者之間自由轉換,名利雙收,形成了一個特殊的利益集團。當改革的榔頭敲打國家機器時,既得利益者愿意成為一顆被敲掉的廢舊釘帽嗎?改革自然而然有阻力。從另外方面來看,企業規模擴大、資本增加,管理者居功自偉,以效益論英雄的局面下,這當然也成了晉升為國家機器管理者的一條通道。反過來,企業虧了,但國有企業管理者與政府管理者在某種程度上又有業務上的往來,甚至是同一部門的老領導,老同事,在中國這個“人情社會“的籠罩下,管理國企的部門會對自己的老同事,老部下問責嗎?這群龐大的企業管理者自然而然的是“負贏不負虧”。究其原因,對企業,盈虧是由企業的老板來負這個責任,然而,國有企業的老板則是整個國民,整個國民來負責造成的局面是可能誰都不負責,誰都負不了責。從會計學的角度來說,收益權是所有權的重要內容,也是所有權的最終表現形式,[1]要國企管理者來負責企業的盈虧,那么國有企業還是不是屬于全體國民呢?這得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同時也對接下來的兩重關系有重要影響。
(二)現代型企業的建立與企業間的關系
現在,我們來討論第二重關系,現代型企業最基本特征就是產權清晰,說白了就是國有企業到底屬于誰,這同時也是在第一層關系礙影響下的延伸。產權是所有權的法律表現形式,也是價值實現和利益分配的先決條件。國企改革的目標即實現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這個“四自”意味著政、資的絕對分開,而國企的出資人是代表全體國民的國家,是國家代表全民行使所有權,如果“四自”了,完全獨立于政府,那國企還是國家的企業嗎?這財產還是國民的財產嗎?這是一種變向的對人民財產的剝奪。
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國有企業的地位不需要在贅述,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形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的“大哥大”思想。“大哥大”表現的一種方式就是想怎么辦,就怎么辦。所以在管理上,大手大腳的鋪張浪費;在經營上,出現了權錢交易;在市場上,就此一家,愛買不買。與此同時,所有制決定分配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來分配利益的這塊大蛋糕,市場參與者可謂是下足了功夫。市場經濟具有競爭性、開放性的特點,但由于國有企業憑借著在計劃經濟時代所確立的領先定位,具有經營規模大,技術實力強,員工素質相對較高,發展比較早的特點,對一些行業形成了或自然或行政性的壟斷,致使提高了想進入該行業的民營企業進入的成本和技術門檻,不利于開展競爭。如何能盤活市場,對政府、對企業,對百姓都是一道難題。對于一些應該被放開的行業,又會出現一些難題,其中凸顯的一條就是如何防止平等地保護公有財產和私有財產不被侵犯,對于國有企業的資產流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腐敗,導致嚴重的低估國有資產,從而賤賣,甚至管理者以權謀私,把人民的財產放入自己的腰包;再者,民營資本進入一個行業,稍有不慎,又會回到前文所敘述的“父子關系衍生產品”所提到了,利用公權力,侵吞了私人的財產。
(三)輿論與國企改革
在前文的描述中,第一、二層關系對國企改革影響重大,現在,我們探究一下人民對國有企業改革的影響。國企的本質從職能上看,是實現政府的目標,與民企的逐利不同,但是,國企的改革與發展又是整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中最為復雜的一環,每走一步棋,幾乎都會被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表現在改革使國企規模擴大,市場占有率提高,經濟效益提升,就會被扣上“與民爭利”,試圖壟斷市場的帽子;改革求穩,逐步推進,幅度不大,也會被指責為改革效率太低,行動遲緩,尾大不掉。其實,這一情況在高度市場化的今天,輿論的壓力實屬稀松平常的事情:今天的國有企業,如前文所述,由于規模巨大,吸收的勞動力量多,除非大的政策變動,效率低了還有政府的財政補貼,是不可能使其破產的;而與國有企業相對的民營企業,在價值規律的影響下,沒有效率,就一定沒法生存。
這一點還是因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在固有的觀念上很難把國有企業與民資企業在競爭者畫上等號。換句話說,有一種看不見的“所有制歧視”不僅阻礙了國有企業的發展,更加阻礙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根深蒂固地認為國有企業代表了社會主義,代表了執政之基,代表了政治正確,雖然不斷的在提高民營經濟的地位,從“共同發展”到兩個毫不動搖,但實際上,在人們的心目中,尊卑長幼實則是分得很清楚的。這就造成了公平的市場競爭難以形成,民間資本的正當權益很難得到保障,國有企業壟斷的行業,民營資本不敢進入,不僅僅是沒有話語權,或者話語權小,更是擔心被鯨吞,從此一無所有;民營資本進入一些行業,可能背后充斥著權錢交易,侵占了國有資產,短時是會獲得暴利,但長遠的看來,背負上了“原罪”,這終有一天會得到“審判”。
總之,國企改革一切的一切都或多或少地遭受聲討,都會使改革者在改革過程中影響其決斷,甚至是通過輿論從而綁架
政府。
三、總結
國企改革的成效在某種程度上依然擺脫不了姓“資”還是姓“社”的路線之爭,而國企真正的責任是在于不能使改革偏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向,其是宏觀調控的重要環節,應該有正確的方向。但目前的情況賽,國企改革受到了上述三從關系的阻礙,正停滯不前。所以,“政企分開”才是國有企業改革的重中之重與點睛之筆,而前提是要在關乎國民經濟命脈的行業以及支柱產業不放手,其他行業完全按照遵循市場經濟原則的條件下,大膽的放開,使其充分地競爭,這才是國企改革的出路。
參考文獻:
[1]楊衛東. 國企改革與“再國有化”反思[J]. 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01:23-37.
[2]楊其靜. 國企改革:在摸索與爭論中前進[J]. 世界經濟文匯,2008,01:55-63.
[3]宋磊. 在理念與能力之間:關于國企改革方向的第三種思路[J]. 經濟學家,2014,08:43-51.
[4]仇保興. 國有企業的問題及其改革思路[J]. 企業改革與管理,1999,12:4-7+11.
[5]和軍,劉洋. 積極推動民營企業與國有壟斷企業融合發展的混合所有制經濟[J]. 遼寧經濟,2014,10:42-45.
[6]蔡恩澤. 去行政化:國企改革新期待[J]. 中外企業文化,2014,01:12-13.
[7]桁林. 三論國企改革的正確方向——評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國企改革的點睛之筆[J]. 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01:64-71.
[8]王軍. 所有制歧視是“國民共進”的最大障礙[J]. 當代社科視野,2014,04:38.
[9]鞏琳萌,李愛玲,金蕾蕾. 新一輪國企改革:箭在弦上[J]. 前線,2014,09:80-83.
[10]黃速建. 中國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經濟管理,2014(7):1-10.
作者簡介:吳林驥(1991–),男,重慶開縣人,四川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方向:中國近現代史基本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