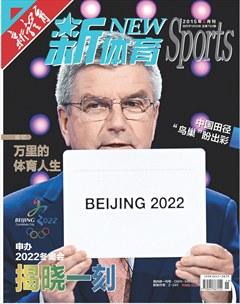環法 不僅是比賽
蕭深
一年一度的環法自行車賽7月26日完成了第102屆賽事。英國名將弗洛姆以領先第二名1分12秒的總成績,再次奪得車手總冠軍。
環法自行車賽挑戰自然、挑戰時間、挑戰極限。人們提到他的大名,談到的不僅是一場賽事,更是一種精神和體育文化的圖騰。在各項自行車比賽中,環法的意義和價值顯然超出了圈內賽事的范疇。很多人對自行車運動的了解可能知之不多,卻知道環法。
環法還具備一種特質,如果不到現場,不走過那些道路,不爬上那些山峰,不看到那些車迷,就不能真正理解環法以及它背后的東西。一座只有兩三萬人的小城,幾乎全城出動來觀看一個賽段的發車儀式。這樣的場面無法用任何語言表達,這是一種感情和文化。
很多不了解環法的人都會有這樣的疑問:大批車迷不遠萬里來到賽場,提前好幾個小時到達賽道邊,開著房車、帶著帳篷,難道就是為了看車手在自己眼前通過的幾分鐘畫面?這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又是個很容易回答的問題。只要來到環法的賽場,特別是爬坡路段的旁邊,看看那些無論烈日還是暴雨都瘋狂吶喊的車迷,就會明白了。
公路自行車比賽,觀眾和選手的距離是如此接近。車迷不是賽道邊的風景,他們就是比賽的一部分。沒了他們,再精彩的比賽都會失色。有的人從爺爺輩開始,已經有三代現場看環法的歷史。有的人每年在固定時候來到固定地點觀戰。沒人知道每個賽段會發生什么,但大家都知道一定可以見到一群和自己一樣狂熱的車迷。

全程報道環法的記者要走環法走過的道路,爬環法爬過的山峰,體驗屬于環法的情懷,不僅有環法爬坡的艱難,還有轉場的艱辛。經過近一個月的長途跋涉,由荷蘭、比利時進入法國,然后繞逆時針來到巴黎的時候,那輛拉著整個團隊的車已經跑了超過8000公里,幾乎每天都要面對轉場,作息時間經常被打亂,特別是在比利牛斯和阿爾卑斯山區,路上的折磨更加厲害。
但這種付出是不能替代的經歷,還是一種力量的展示。每天賽后的混合采訪區,那些來自歐美知名媒體的老記者們會和我們聊起去年計成參加環法展示中國車手的實力,聊起他們報道過的在中國舉行的比賽。
環法這樣一項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賽事在中國缺少關注,原因不在于環法本身缺乏魅力,而是推廣力度的不足。實際上,環法和公路自行車運動的潛力遠遠沒有得到應有的開掘。
這種開掘應該從比賽層面入手,了解這項運動的本質是欣賞這項賽事的重要前提。公路自行車是一個引起誤解比較多的項目,有人把它看成競速項目,覺得不夠刺激;有人把它看成耐力項目,經常用馬拉松的思維去分析。最大的誤解則是認為公路自行車是個人項目。實際上,公路自行車是一個真正的團隊項目,包含豐富的戰術內容。

像環法這樣的公路自行車賽具有很特殊的魅力,只不過不像球類項目那么好提煉,它更像是一種情懷。也許不是每個觀眾都能了解和體驗山地賽段斗智斗力的角逐,但很多人可以感受到環法和自行車運動是人類對于自我和自然的征服。
辦賽也是重要環節。中國人談環法,常常用“百年環法”的說法,辦自行車比賽也喜歡拿環法當標桿,追求規模效應。但“百年環法”所代表的不僅是時間長度,更是歷史積淀。中國的環賽設置了為數不少的城市繞圈賽段,電視轉播也以繞圈為主。這種平路賽段的背后是一種平面化的思維,簡單的比賽模式加上簡單的辦賽思路,“打造百年”只是空談而已。環法是立體化的賽事,不僅賽段組合立體,推廣策略同樣立體。商業化乃至炒作,環法從來不缺少噱頭。但環法更不缺乏深耕小細節和小地方的精神,百年以來打造了無數屬于這項賽事的城市和一個個享譽車壇的著名爬坡。
今年是一戰爆發101年,二戰結束70周年,和去年一樣,環法又一次通過比賽來緬懷歷史。康布雷、阿拉斯、亞眠、阿布維爾,環法把這些曾經的戰場作為比賽的起終點。這是環法的魅力之一,在有意無意間帶過一些看似不起眼卻十分重要的地方,用獨特的方式把它們組合在一起。這些細節上的東西恰恰是中國辦賽事所缺乏的,而且并不是靠時間的簡單累積所能達到,需要思路上的重大調整。
騎行乃至戶外文化的推廣同樣關鍵。比如今年環法的始發地荷蘭是環法歷史上在法國之外發車最多的地方,深厚的自行車文化底蘊居功至偉。遍布大街小巷的各式自行車,老少皆兵的全民騎行大軍,精致的紅色專用自行車道,自行車的重要性滲透到荷蘭人生活中的每個細節。當騎行成為改變生活的一種方式,乃至生活方式本身的時候,自行車運動成為主流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因為環法和自行車運動不僅僅是一場比賽,看似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