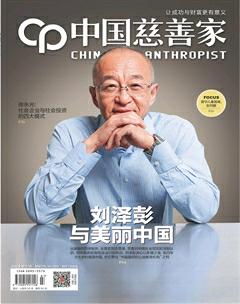路林:基金會投資管家
章偉升

操盤過500多億元的中城投資,從2009年起就已經受托管理萬科公益基金會、萬通公益基金會、南都公益基金會等多家基金會的資金,年收益超過同期銀行存款利率近兩倍
北京香格里拉酒店,上海中城聯盟投資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總裁路林一邊翻看PPT,一邊無奈地告訴《中國慈善家》,“這是我四年前做的,現在還能用。” 此時,中城投資正忙碌籌備新三板上市,但他仍讓助理抽空補充、修改一份分析中國公益基金會的狀況、管理制度、投資訴求和特點,并且落款時間是2011年的PPT。 助理一番研究后回復:無需更新。言下之意, PPT中提及的基金會狀況、制度等方面至今沒有變化。“這四年我們國家的政治、經濟、企業變化多大?而社會組織這四年沒有變化、沒有進步、沒有提升,可能觀念在改變,但從管理部門來講是一件很可悲的事。”路林想了想,神色揶揄地補充說,唯一可以更新數據的,是他拿來作為參考案例的美國福特基金會。 坐擁上百億美元資產的福特基金會,投資組合主要在公開市場、私募市場和固定收益。為了滿足持續的公益支出和其他機會,該基金會一直保持高流動性的投資,公司債、不良資產證券、私募股權、全球股票對沖、房地產等都是其收益來源。 “他們有兩大部門,投資部分負責掙錢,公益部門負責花錢,結合統籌管理和分散管理,雙層經營,盈利部門和非盈利部門分治。”路林告訴記者,福特基金會把70%的總收入用于投資,年收益甚至可以達到12%,“他們的購買能力和投入能力都很好,這樣公益事業才能良性循環。歐美靠投資收益解決公益支出,我們國家卻是靠規定。” 已經在中國施行十年的《基金會管理條例》明文表示:公募基金會每年用于公益事業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總收入的70%;非公募基金會則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額的8%。強制性的行政指令讓路林哭笑不得,“這看似保護捐贈人的利益,實際上限制了公益行業發展,政府部門還在拍腦袋和不作為,閉門造車。” 操盤過500多億元的中城投資,從2009年起就已經受托管理萬科、萬通、南都等多家基金會的資金,年收益超過同期銀行存款利率近兩倍,但政策法規仍是難以逾越的壁壘,中國投資收入為零的基金會超過半數,“社保基金能做投資,為什么其他基金會不能做?” 2011年,《基金會管理條例》修訂草案送審,其中新增一條規定:基金會為保值、增值進行的投資總額不得高于上一年末總資產的10%。路林抱怨這個數值太過保守,“這點投入帶來的收益微不足道,那還投資干什么?” 在他眼里,基金會應該至少把一半總收入用于長短期投資,“郭美美事件搞得官員和公益人心里都挺脆弱,挺可憐的,沒有人文和宗教精神支撐內心,純粹靠利益驅動、小官吏思維,無論做什么事,推動力都有限。” 盡管對大環境失望,但路林仍在嘗試做些改變。 2015年5月,中城投資推出“SEE·中城公益投資產品”,公眾可按1萬、2萬、3萬等三種額度認購,一年后,本金和基礎利息返還投資者,投資產生的超額部分則作為SEE生態獎得主的獎金。最終,產品認購總額達72萬元,在此基礎上,中城投資又追加72萬元配投資金,并無償為這筆資金提供穩健的理財服務。 “這只是牛刀小試。”路林說,中城投資在考慮根據基金會的投資規模、標的和風險因素,按相應比例配投,產生的收益再次捐贈。提高資產保值、增值能力,以充足的資本維持基金會高效運轉,讓公益行業成為人才高地,進而成為事業高地,是路林推動配投、配捐的目的。“不能光憑覺悟、道德干活,人家不拿或少拿錢,不意味著他們不應該有,做公益應該是升華而非剝奪的過程,這是底線。” 但是,路林反對捐贈人過度干涉基金會的運作和治理,“捐贈是把財富讓渡給社會,如果還把基金會或者公益組織當成他們家自留地就麻煩了。” 他鼓勵秘書長們以獨立意志、專業能力行使職權,按基金會的能力而非捐贈人的意愿進行管理,“要把自己當成CEO一樣去運營機構,一些秘書長把自己當成伺候大佬的辦事人員看,這個定位不對。” 目前,中國的基金會普遍由理事會和秘書處組成二級管理結構,路林認為這不合理,他主張基金會借鑒企業的治理經驗。“理事會如果把自己等同企業的董事會而過度管理就有問題,大樹底下不長草。他們應該分出一部分理事,成立執行理事會,一把手要專崗專任,跟企業一樣,分為執行董事和非執行董事。” 與多數企業家相似,路林關注慈善公益也是“倉廩實而知禮節”。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催生出一批“92派”企業家。當時供職中宣部的路林也不再安于機關生活,“太程式化、確定性太強,我可以把自己一生都看清楚。”他選擇了下海經商,經歷小型貿易公司、互聯網創投機構和金融上市公司后,輾轉來到中城投資擔任總裁。“這些年,我們越做越大,企業高速增長帶來個人視野的擴張,從商業企業延伸到社會企業、公益領域。” 未來,路林的主要目標還是在商業領域,他要把中城投資的事業做得更強,衍生更多業務,甚至進軍新的領域。退休后,他計劃到一家社會企業做CEO。 從自益到益他的轉變路徑同樣適用于中城投資,路林說,企業達到一定規模后需要推己及人,兼顧股東、員工、客戶和社會等各方利益才會有更好的結果。與阿拉善SEE聯合主辦第六屆“SEE生態獎”并推出公益投資產品,便是平衡經濟利益和社會效益的嘗試之一,“SEE這群企業家做得比較漂亮,創新、責任和效率都不錯。而我們也是保護一種人文遺產,人文生態重建了,才有更大的力量推動生態重建。” 為了寫頒獎典禮的發言稿,路林想了兩周,最后決定講重建綠色人文。“中國古代各個學派對于人與人、人與自然有很多思考,‘五四以后我們對傳統文化的認識根本就回不去。過去說‘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其樂無窮,斗的第一位是人,這破壞最大。”他的邏輯是,人與人都不和諧,人與自然就不可能和諧。 跟所有出生于1960年代的同齡人一樣,路林也經歷過“文革”,激烈地批林批孔。那個時期,他大量閱讀傳統典籍,原是為了挑其漏洞用于批判,卻無意中積累下濃厚的興趣和知識。“文革”結束,路林考入大學繼續主修古典文獻。批判和推倒一切的狂熱過去之后,他逐漸轉向反思和敬畏,認為人類不能對抗自然、市場、人民和上帝。“企業家群體現在比較焦慮、浮躁。SEE治沙肯定有很多正面意義,但像推廣節水小米說不準結果如何,農民有利益導向,都爭著去種可能會使水源更緊張。”他否定人定勝天,對什么是“正確”顯得審慎。 青年時期,路林深受儒家文化影響,改革開放后相對寬松的社會環境又讓他得以接觸西方的理性和宗教精神,“我看到它們可以帶來很好的結果,比如科學、工業、現代化,都是理性精神的體現。進入繁雜的后工業化時代,人類可以在不分東方、西方的宗教精神中找到心靈歸宿。” 路林說,每個民族都會思考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上帝這三大關系。在他的研究中,西方的宗教看似分散實則相通,從猶太教到基督教、天主教、新教、東正教,再到伊斯蘭教,一脈相承,“伊斯蘭教的先知當中有耶穌,易卜拉欣就是亞伯拉罕。”他不具體信仰某個宗教,但自稱是個有宗教精神的人,堅信有上帝的存在,“一定有真實的上帝、造物主。” 路林還以傳統文化倡導的一些理念,與傳教士精神作對比,試圖闡明西方宗教與中國傳統文化也有諸多共性。儒家典籍《大學》中,正心、誠意、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連貫的軌跡,“這之前還有為己、克己、成己。從自然人到社會人是成己的過程,克己才能成己,這個路徑跟西方宗教有點像,就是要看到人性惡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