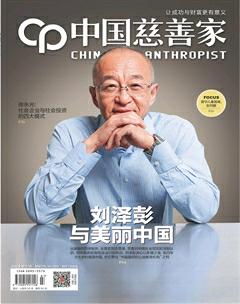張紅巖:棄商從益“癥候群”
白筱

從商業轉身公益,6年中,張紅巖顯現了一系列典型或非典型轉型癥候
張紅巖從商業轉身公益已有6年。
2009年,他創立深德公益,為公益機構提供咨詢服務;2011年,他與5位合伙人聯合發起 “育基金”,開展公益創投;2012年,“新湖-育”合作達成,他引入商業資本;去年,他繼續深入,與清華大學Xlab創新創業教育平臺合作,著手打造社創硅谷。
轉身6年中,他顯現了一系列典型或非典型轉型癥候。
虛無感—2008年即將結束,張紅巖的虛無感達到臨界點。
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商學院進修MBA畢業時是2004年,張紅巖有兩個跨國公司的就職機會可供選擇,一家是波士頓咨詢公司(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BCG),另一家是生產刀具的美國肯納金屬公司(Kennametal Inc.)
張紅巖喜歡做咨詢服務,他能在“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中找到樂趣,但他放棄了BCG的邀請。在美國兩年,他花光了十幾萬美元積蓄,而肯納給了他無法拒絕的豐厚待遇。“報銷了我所有學費,給我非常好的一個位置,甚至負責為我搬家。”
張紅巖本科就讀于清華大學,學習材料科學,但他還沒能用自己的專業知識服務過一家公司。他說服自己,干脆在美國安家落戶,“準備開始養老”。
在肯納“養老”的4年,張紅巖稱之為煎熬。“最煎熬的不是工作辛苦,而是不確定性全部消失,一眼看到自己未來,沒有未知了。”他發現高估了自己循規蹈矩的能力,索性辭職,回頭朝“混沌”走去。
“回到中國之后,給BCG發了封信,問offer還存在嗎?對方說還在。”
張紅巖在BCG得到了不錯的職位和薪水。他喜歡這里“以人為本”的企業文化,工作內容也暫時滿足了他的好奇心。2008年年末,張紅巖已是年薪150萬元的項目經理。
他對金錢沒有太高的欲望,很滿足,他甚至以為可以這樣過一輩子,但虛無感再次襲來。
“每天醒來,我都覺得渾渾噩噩,懶得為一個商業項目爬起來,覺得自己在混日子。我覺得任何人從商業轉身做公益之前都是這種情況。”張紅巖說。
成就感—為羌繡項目提供戰略規劃,張紅巖體會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2008年12月,張紅巖收到BCG合伙人皮特給項目經理們發的一封郵件。郵件中稱,BCG將為壹基金做一次戰略規劃,薪酬由BCG與壹基金各支付三分之一,項目經理自行報名帶隊。郵件發出不到10秒,張紅巖便回信報名。
2009年,整整一年時間,他跟羌繡項目一同摸爬滾打。他發現,對于草根NGO來說,需要解決的問題可以小到庫存管理,為奔馳、阿迪達斯等500強企業做發展路徑圖的常規打法并不適用。他需要無視業務范疇,參與具體操作,提供手把手指導。
期間,因投入成本過高及票據等問題未能得到解決,蒙牛決定退出羌繡項目,并取消300萬元的一筆訂單。張紅巖得知后,馬上給蒙牛的幾個相關負責人打電話,“從晚上8點打到夜里12點”。
他情緒激動地向對方闡述這筆訂單背后那些繡娘的辛勤付出,告訴對方他親眼見過并感同身受的曲折與艱難。他甚至質問對方,“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一件什么事?你知道取消訂單對這個機構意味著什么?你知道后果么?”
最后一通電話長達半個小時,張紅巖滔滔不絕,對方一言未發。末了,對方回應:“好了,張先生我知道了,這個事我們不取消,一定要把它做下去。”
“很開心,無比開心,比我當年拿下一些咨詢項目,或者做成一些大生意都要開心。”
自信—在商業機構供職太久,能為公益組織做戰略規劃,張紅巖隱隱覺得自己可以在“跨界”背后找到無限欣喜。
他逐漸發現多數公益組織都需要專業支持。與此同時,他接觸到了社會企業概念。
“羌繡只是壹基金資助的項目,但社會企業這個詞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關注點,它又是Social,又是Enterprise,我覺得非常適合我這樣的人。我對公益一直很有熱情。”張紅巖說。
他決定離開BCG。
2009年1月,旨在為公益組織提供咨詢、評估服務的深德公益在上海太倉路58號成立。張紅巖將公司稱為“Venture Avenue”。“Venture就是小企業,Avenue就是大道。在整個公益領域效率偏低的情況下,小的公益機構不一定要真正變成一個商業企業,但能以商業領導人的方式領導機構,哪里有需求,我就去做。”
走向“極端”—剛剛轉身公益,滿懷熱情的張紅巖執著地走向“極端”。
“當時有點左,剛開始創業嘛,就想做一些與公益相關的事,真是把錢當成第二位。”
有BCG的同事想介紹張紅巖到星巴克、阿迪達斯做自由顧問,薪水豐厚,三個月100萬,張紅巖拒絕了。
2011年11月,法國愛達訊基金會邀請深德公益為其在四川甘孜州丹巴縣東馬村的一個學前兒童教育項目做評估,需要團隊進行三周的調研。張紅巖以為法國的基金會應該“很有錢”,問項目預算,對方回答他“一萬四”。
“差旅費不在里邊吧?”張紅巖問。
“包括差旅費。”對方答。
這樣的選擇讓深德公益艱難地運作了兩年多,最少的一次項目預算僅8000元。“員工工資經常接不上,”張紅巖逐漸醒悟,“如果你照顧不好團隊,甚至不能養活自己,這真的不是公益,不可持續。那我們就轉型。”
Deja-vu現象—此后,深德公益繼續支持草根機構,也逐步與一些國際機構開展合作,如福特基金會、卡特中心以及英國大使館文化教育處,同時,拓展業務范疇,開始對接奔馳、通用電器等跨國企業。這一調整讓公司收入大幅提高,人才質與量均得到提升和壯大,形成正循環。
公司轉型后,張紅巖需要經常變化自己的著裝—上午正裝考究,中午摘掉領帶,下午換上牛仔褲,奔忙于不同屬性的機構之間,與不同領域的人見面,以致出現了Deja-vu現象—即視感,認為眼前某一場景似曾相識。endprint
2014年11月某天,張紅巖的汽車三次駛過北京二環。上午,他去一家五星級酒店,為德國某奢侈汽車品牌客戶進行頭腦風暴。中午,他到北京干面胡同,為一家基金會梳理“去行政化”戰略。下午,他駛向北京遠郊月租600元的寫字樓,考察一家專門服務PKU罕見病兒童的社會企業。
張紅巖記得,一年前,也有過相同的一天。那一天,他先后見的是奔馳大佬、公益大佬徐永光和熱心公益的楊瀾。
孤獨凄苦—2012年小年夜,南京小雨,透骨地冷。張紅巖從未見過如此空蕩蕩的車站,他孤獨地等待駛往杭州的列車。
2010年始,深德公益決定發起公益創投基金,支持社會企業。他們四處洽談合作,無一達成,對方質疑他們的動機與能力。“首先你不是巨富,沒到這個份兒上,做公益人家不理解;其次,原來做咨詢,那你憑什么孵化公益伙伴?”
張紅巖認同商業機構的謹慎,但他不能忍受“你們憑什么做公益?”這樣的態度。2011年7月,張紅巖與深德公益的幾位董事湊了250萬元,聯合發起育基金。后經徐永光助力推動,新湖集團、愛德基金會育基金共同成立“新湖·育公益創投基金”,這是中國首家正式注冊成立的人民幣公益創投基金。
2012年小年,張紅巖先從北京到南京,等了一整天,與新湖·育的一個關鍵客戶會面半小時,解決合作中遇到的麻煩。接著,他要前往杭州,等著他的是新湖集團方面“指著鼻子”的一通抱怨和數落。
當時,能引入商業資本進行公益創投絕非易事,張紅巖選擇“該忍還是要忍”,但種種承受讓他倍感孤獨。
“前前后后各種打交道和談判,受到各種各樣的置疑,無數多的置疑。非常凄苦。”
對抗自我—與草根組織打交道,張紅巖陷入了長期的困擾,他需要經常對自己說NO。
新湖·育參照合伙制企業的模式設立,原始基金1000萬元,新湖將資金捐給愛德基金會,由愛德和育公益創投分別出資750萬元和250萬元,共同成立新湖·育。張紅巖說,“整個的架構設計上,滿足了捐款人、出資人做公益的需求,同時,給管理和運作者創造了更大的靈活性。”
給養模式創新后,選擇投資何種項目,是張紅巖要面對的另一大問題。“最容易打動我的是哪些?創始人有著無比多的公益熱情,再就是對扶助自閉癥兒童等弱勢群體的這類項目,但你深入了解會發現,很多項目更像是一個傳統的公益模式,不可持續。”
張紅巖必須同時考慮項目的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他要與自己的個人好惡對抗,需要經常拒絕感動過自己的公益項目和公益人。
尋找同類—2014年11月,隨“中國社會投資家考察團”訪問英國,張紅巖激動地找到了同類。
貝斯納爾格林風投基金(Bethnal Green Venture,BGV)是英國一家創業和孵化機構,專門幫那些“異想天開”的粗糙創意孵化成蝶。該機構不僅為創意團隊提供辦公場所,還提供資金以及相關培訓,當創意團隊孵化成社會企業并成功獲得商業融資,BGV將占有其6%的股份。
該機構是非盈利擔保機構,但它控股一家營利公司,營利公司的絕大部分利潤將留給包括BGV在內的股東,確保收益用于公益,實現永久綠色循環。
截至2014年7月,BGV先后支持的42個團隊中,孵化出了20余個小型社會企業。
“我當時非常激動,一下子就感覺找到同類了,馬上拍板,說這個事情必須在中國落地,就叫‘社創硅谷。”
回到中國,張紅巖緊鑼密鼓地為“社創硅谷”尋覓合適的落腳點,從上海到杭州,再到天津,目標久久未能出現,這讓他一度感到頹喪。
“第一要找到好項目,找到社會企業這個概念基礎好一點的地方;第二,我們需要場地和資源,要找到很好的合作方;第三,要找到孵化平臺所需的資金和相關投資。”張紅巖東奔西跑,找了整整6個月時間。
無比激動—2015年5月,身在天津的張紅巖收到兩條短信,兩個不同的朋友向他推薦了清華大學的Xlab學生創業平臺,他馬上啟程回京。
5月18號這一天,北京的空氣特別好,天很藍,云很白。出了地鐵還有兩公里路程,張紅巖故意沒有叫出租車。他邊走邊聽音樂,恰巧是他的清華校友李健的那首《為你而來》。
對于社會企業這一概念,北京無疑是土壤肥沃的城市之一,清華大學Xlab已創立兩年,優勢得天獨厚。作為清華校友,張紅巖覺得,跟斯坦福、哈佛比,清華正需要一個社會創新板塊。
“一到這個地方,一下被震撼了,整個創業氛圍非常好。短短兩個小時,基本上就把這個合作意向敲定了。無比激動。”
倍感自豪—創立深德公益至今,沒什么能比“自強”更讓張紅巖感到驕傲的了。
“你看國內的咨詢也好,評估也好,很少有像深德這樣,沒拿一分錢捐款,都是靠自己的專業服務收費,養活十幾個人。”
張紅巖所說的十幾個人,都有頂尖的教育背景,團隊成員一半以上來自清華、復旦等名校,很多是海歸。“他們現在的收入水平,和市場價格基本一致,年薪從12萬到100萬都有。”
深德工作積累了230多個咨詢、評估項目,初期絕大多數項目只有一兩萬元的收入,六年后的今天,百萬級以上的客戶已越來越多。
“能讓團隊體面地工作,同時有一個實現夢想的平臺,我覺得挺自豪的。”張紅巖說。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