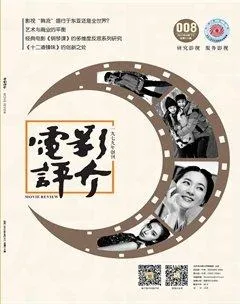重述歷史語境下的“中國形象”研究——論《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釵》等影片對國家形象的女性化解讀
李營營
歷史本然地發生著,對歷史的記錄和反映便構成一種重述。重述的方式不同、重述者的立場不同,所拼貼出的歷史及展現的國家形象也就因人而異、各不相同。縱觀中國近現代史,日本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心靈創傷是我們始終無法繞過的一道坎兒,70年過去了,我們依然無法忘卻那段歷史,當然也從未停止這種重述。
一、“中國形象”轉喻下的“母親”意象
縱觀中國現當代文藝實踐,筆者發現,盡管重述的方式、立場甚至場合各不相同,但是,“中國”這一形象幾乎無一例外地被做了女性化處理。易言之,“中國”作為一種符號“能指”,在大家的理解中,常常與“女性”這一意義范疇聯系在一起,而且是與最偉大的女性——母親,聯系在一起。這從很多地方都可得到印證。中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幾乎在他所有小說中,都能讀到“中國”與“母親”二者間意指的同一性。
如果說這還只是種巧合和個案,那么,近年來中國電影,尤其講述中國抗戰歷史的那類電影,也普遍對中國形象做女性化處理,往往以女性的被蹂躪來意指國家曾經所遭受的屈辱和掠奪,這就不能不說具有一定代表性和說服力了。在這些影片中,“中國”無形中被轉喻為“母親”,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國家苦難,在電影中往往通過女性的被蹂躪甚至被奸淫表現出來。電影《南京!南京!》如此,《金陵十三釵》也是如此,就連非抗戰題材,表現中國歷史上大饑荒的影片《1942》,從中我們也能隱約讀出祖國母親和其膝下子民所歷經的種種苦難。
二、將“中國”作女性化解讀的原因
創作者之所以在書寫歷史時傾向于對中國做女性化解讀,一方面與各國人民習慣于將祖國比作母親有一定關系,英語世界用單詞“motherland”指稱祖國就十分形象地說明了這一問題。但是,這種現象普遍存在于眾多國內抗戰題材類影片中,就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關注。鑒于此,本文擬通過《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釵》和《南京1937》三部影片,結合各影片產生的時代背景和整體文化環境,具體探究到底哪些因素促使創作者在敘述歷史時對中國形象做出這種處理和解讀。
首先從三部影片的故事梗概入手,看影片分別是從什么視角來處理南京大屠殺這段歷史的。
電影《南京1937》(1996)、《南京!南京!》(2009)和《金陵十三釵》(2011)都將抗戰時期日本在南京所進行的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作為影片敘事的總背景。影片《南京1937》(也有人直接譯作《南京大屠殺》)中,故事由一個中國男人(成賢)和日本女人(理惠子)組合起來的大家庭在大屠殺中的遭遇所構成,理惠子目睹了本國士兵對中國無辜生命的踐踏,最終并沒有因為自己的日本人身份而得以幸免,她同樣死在了日本人手下,一個懷著身孕的日本女人被自己國家的士兵活活殺死,其表現力勝過千千萬萬中國婦女死在日本士兵手下,有力地彰顯了日本人的殘忍。電影《南京!南京!》則通過親歷戰場的中日兩名士兵的所見所聞來講述戰爭,日本士兵在燒殺了數以百計千計的無辜百姓之后,忍受不了良心的譴責,最后不得不走向自殺。一個親歷者的感受是最直觀、真切的,因而也最能表現中國曾經所遭受的蹂躪和屈辱,日本士兵的自殺表征了這場戰爭的非正義性。到《金陵十三釵》,沒有像前兩部影片一樣借力于日本人的視角,而是以金陵地區十三位游走于花街柳巷的青樓女子為主人公,講述她們憑借自己微薄之力,替未成年女孩躲過一劫的故事。三部影片雖然編織了不同的故事,最終都旨在彰顯南京大屠殺中日本人的殘忍、無人性及對中國人造成的難以撫平的創傷,畢竟,事實勝于雄辯,而且奸淫婦女之事已經觸碰到中國人的道德底線,這是傳統文化所不能容忍的。
從觀眾的接受心理來講,受中國傳統文化浸潤,我們往往傾向于將弱者與女性天然地聯系起來,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中日對戰中,中國屬于受侵略一方,經濟、社會發展都遠遠落后于日本,所以,作為力量相對弱小的受動方,評判主體會自覺不自覺地同情弱者而將價值天平倒向中國一方,相應地日本則被置于受譴責一端。這樣,中國自然而然地就與女性聯系在一起,影片展現的國家形象也就趨于女性化了。需要說明的是,將中國做女性化解讀并不是貶低、嘲諷中國,自古以來,華夏民族向世界展現的都是積極進取、自強不息的陽剛之美,這里只是就事論事,只是針對最近幾部以南京大屠殺為背景的影片做具體分析。
第三,三部影片都沒有將中國士兵的艱難抵抗作為故事敘述的中心,而是借力于女性的被侮辱與被損害事件來展開情節,這是電影這種藝術門類在表現方式上與其他藝術樣式相比的獨特性之所在,也是電影爭取票房的慣用手法之一。電影作為一種聲、光、影三位一體的藝術門類,立體、直觀的形象尤其人物形象是其表現的重心,可以說,沒有人物就沒有電影(自然景物、紀錄片等除外)。而女性是更易于為觀眾所接受的,加之要展示女性受奸淫這樣的題材,人所共有的偷窺欲會自覺不自覺地期待電影鏡頭中類似場景的展現,盡管展示的是胞弟胞妹的屈辱,但人性天生的窺視欲望還是會暫時避開理性,想要一飽私欲,所以,電影的這種處理正好迎合了觀眾的這種心理,從而贏得了一部分受眾。
但是,三部影片在展現國家災難時對觀眾接受度的挑戰還是存有一定差別的。《南京1937》將對大屠殺的揭示放在一個由中國男人(成賢)和日本女人(理惠子)組成的家庭的遭遇中來展開,按照歷史史實中國婦女被奸淫,但男女主人公并沒有以被奸淫者身份出現,因而造成的視覺沖擊力、心理感受力都明顯要弱于直接奸淫場面的展現。而且,中國男人這一角色的性別定位也一定程度上稍稍安慰了觀眾的心。在電影《南京!南京!》中,用災難制造者的崩潰來表現蹂躪的殘忍和不堪,此時,沉默的大多數成了潛在意義上的受動人群,在這里,創作者用集體性的被殘殺、奸淫來表征中國的性別色彩,讓觀眾提起中國就想到數以千百計的受強奸婦女,這種仇恨也就上升為民族性的。到影片《金陵十三釵》,價值評判角度更加傾斜向中國了,作品選擇了一群尚未成年的小女孩的被奸淫來表現中國在南京大屠殺中的弱勢地位,能對未成年孩子下手,與禽獸相差幾何?中國人的憤怒立馬被點燃了,民族情緒瞬間被激起。總而言之,從《南京1937》到《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釵》,對歷史的重述方式越來越巧妙,對歷史史實的把握越來越戳中觀眾的最佳感受點,從而很容易便能激起觀眾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
盡管如此,電影所運用的打動觀眾的技巧還是各不相同的,如果說《南京1937》通過一個家庭的遭遇來展現屠殺的殘忍,親情的力量多少可以抵消、消解大屠殺給觀眾所帶來的感受上的沖擊力。《南京!南京!》著力于將施暴者的感受傳達給觀眾,在共同人性的基礎上去感受和體認這份情緒,《金陵十三釵》則將視角重新拉回到中國民眾內部,以一個觸碰中國人底線的故事情節聯系于整個屠殺大背景。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說,《金陵十三釵》比《南京1937》和《南京!南京!》更加接近于觀眾感覺爆發的臨界點,收到的效果當然更佳。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上映于2011年的《金陵十三釵》比上映于1996年的《南京1937》和2009年的《南京!南京!》在電影表現技巧上、在電影票房的追求上都更積極和正面了。自我國全面實行市場經濟以來,電影對票房的收益越來越重視,也就說電影的經濟訴求越來越提高了,因此,《金陵十三釵》更會運用一定的敘事策略致力于票房收益。這里的策略便是運用女性,尤其是未成年女孩遭奸淫這種挑戰中國人道德底線的方式增強故事吸引力,相應地,中國的歷史傷痛被濃縮、定格在未成年少女的遭遇上,中國與女性就取得了某種層面的同一。
需要補充的是,影片《金陵十三釵》中楚楚動人、風情萬種的十三位青樓女子每次亮相都是清一色的旗袍,搔首弄姿中盡展東方女性神韻,當然,更多了一份嫵媚和俗氣。對于這種遮不住的濃郁的女色展現本身就是現代商業影片追求經濟利益的一種手段。太多色情的東西在成功吸引觀眾眼球的同時,也相對弱化了歷史創傷的書寫和展現。著名影評人周鐵東曾說:“《金陵十三釵》整個故事用一句大白話便可以一言以蔽之:一個美國混混攜一群風塵女子以自身肉體為代價拯救一幫蘿莉少女的故事。”[1]暫且不論對于影片中以人格價值相對較低的風塵女子的肉體交易換取人格價值相對較高的少女這種價值選擇尺度本身的合理性與否,但是視覺呈現上的矛盾也許才是這部影片沒有達到預期票房的關鍵所在。影片中,數位風塵女子以身體救國這一情節是電影吸引眼球的核心部分和高潮部分,觀眾的性幻想被徹底地吊起來,但是在實際的情節安排中卻以潛在文本的形式直接跳過,按照故事邏輯必然會發生的結果只存在于人們的臆想中,令很多人感到失望,而且,這部分情節的省略對于歷史事實的呈現顯然少了最關鍵、最直接和最具說服力的部分,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缺憾。當然,對于大尺度的展現本身就需要一定的節制和約束,但南京大屠殺這種題材本身就決定了,缺少必要部分的性感鏡頭和浸淫場面是無法有效地勾起觀者的仇恨情緒,因而也就無法真實還原那段歷史,有論者將之歸因于創作者對于此事立場的游離,認為是導演過分考慮觀眾尤其是他國受眾的情緒而選擇隱藏自己對此事件過分鮮明的愛憎情緒。
結語
對于同一題材不同影片的處理方式,筆者以為,一方面與創作者本人的創作體驗、經驗及故事處理方式有關,不同的導演從同一題材中所抓取的或者說截取的橫斷面可以千差萬別、各不相同,只有這樣,才造就了電影藝術的百花齊放。另一方面,作為主創人員,個人的想法與作品最終呈現出來的面貌有時差之千里,這種情況在電影市場化之后更常見,因為影片最終面貌的呈現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還是拿電影《金陵十三釵》為例。《金陵十三釵》上映于2011年,對歷史事實的肉欲化處理注定這是一部追求高票房的商業片。本世紀初,伴隨我國現代化實踐的快速展開,經濟、社會取得突飛猛進的發展,使得快速躋身現代化行列的我們在經濟增長的同時,也提早出現了一些現代化充分發展時期才會出現的問題,如文化的大眾化,通俗文化逐漸取代精英文化成為文化發展的主流。大眾的文化趨于通俗化,以追求商業利益為旨歸的當代電影就會自覺不自覺地在創作中迎合大眾審美趣味,有時,為了高票房,情節的惡俗、場面的宏大、色彩的靚麗等都成為電影創作時主要的著力點。至于對歷史的重述是否符合歷史事實,反思是否深刻則變得似乎不那么重要了。作為第五代導演的張藝謀深諳這些技巧以提升票房收入,具體到《金陵十三釵》,便是把大屠殺僅僅當成了一塊背景板,“在這個背景板上涂抹的卻是極盡奢華、徒有其表、刻意逢迎好萊塢卻又只得其形未得其神的劇情片元素”。[2]
除了對國內觀眾審美趣味的迎合,對海外市場的占有也是電影人堅持不懈的一大主攻方向。建國以來,尤其是新時期以來,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頻繁,電影的國際化成為電影人創作時難以忽略的一塊新領地。自《黃土地》《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等影片走向國際并獲得極好聲譽以后,國產影片創作越來越趨力于國際評獎機制,努力創作迎合國際獎項評選標準的影片,《英雄》《十面埋伏》等影片便是一種嘗試,也取得了國際社會的認可,可謂國內商業大片走向國際的成功案例。《金陵十三釵》中,刻意弱化本該重點呈現的女性被蹂躪情節,而代之以一種較為柔和、中立的敘述立場,這是否是導演在刻意迎合國外獎項評委的口味也未可知。
當今電影創作摒棄了傳統電影所堅持的邏輯和觀念,滿足觀者審美趣味、迎合國際市場日益成為國產影片不斷追求的新目標。除了經濟訴求,有的電影還需要政治話語的支撐,總之,“介入性”[3]電影是當代電影創作的主潮。所以,如何在取得票房收入的同時兼顧文化的傳播與交流,或許是電影人在今后的創作中需要重點思考的問題。
[1][2]周鐵東.好萊塢與中國電影的全球戰略——從《金陵十三釵》的海外失利看加強中美合拍的必要性[J].電影藝術,2012(5):6.
[3]段運冬.“介入性”與新世紀以來中國主流電影的嬗變[J].文藝研究,2011(1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