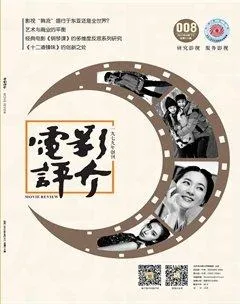凝視男性:觀看的“陷阱”:女性主義經典電影《鋼琴課》的多維度反思系列研究之一
李 晶
《鋼琴課》是新西蘭著名女導演簡·坎皮恩(Jane·Campion)最富盛名的一部電影作品,影片女性畫外音的敘述方式、原型結構的顯露、劇中劇的寓言對照、豐富的隱喻符號、精神分析心理模式的實踐、兩性戰爭與窺視理論的使用以及對各種女性主義理論流派的重溫,讓《鋼琴課》與簡·坎皮恩本人獲得了極大的贊譽與追捧。近20年來,在國內外學術界引發了持續不減的研究熱情,將之推向女性主義電影的巔峰。然而,可能正因為影片的光環效應,國內外學界大多采用認同的研究態度,使一些問題一直處于遮蔽狀態。本研究試圖避開這一闡釋路徑,重新分析《鋼琴課》的電影文本,揭示其復雜凝視背后的性別政治。
“凝視”(gaze)——攜帶權力運作或者欲望糾結的觀看方法。它通常是視覺中心主義的產物,觀者被權力賦予“看”的特權,通過“看”確立自己的主體位置,被觀看者淪為“看”的對象同時,體會到觀者眼光帶來的權力壓力,通過內化觀者的價值判斷進行自我物化。當今對凝視的批判已經成為文化批評主義者用來反抗視覺中心主義、父權中心主義、種族主義等的有力武器。[1]
“凝視”(gaze)可作為20世紀視覺文化興起的關鍵詞之一,其哲學淵源可以一直追溯到本體論哲學的源頭柏拉圖,在其“理念”世界中,感官的視覺能力需要真理的可見光來指引,以擺脫感官束縛與對“摹本”(即現實)的錯誤認知,達到一種“心靈的視力”[2],在法語中,“知道”(savoir)的詞根就是“看”(voir);而英語里的“I see”,往往意指“我懂了”,超越了其原本的字面含義;theory(理論)一詞的希臘詞原型theoria的含義正是“專注的看”[3],這種視覺能力直指洞悉事物本質和真理的第三只眼——理性的知覺能力。
20世紀以來,笛卡爾式身/心二分絕對理性的觀看主體遭到了諸多哲學流派的解構與拷問。薩特首先指出:從被觀看到自我監視——“他者”的目光讓自我建構變得異常艱難;拉康的“鏡我”理論認為:嬰兒萌發自我意識正是依靠鏡中自我的影像來確認的,也正因為這個鏡中的“他者”才讓主體建構變成一場自我放逐與分裂的游戲。福柯則徹底抽掉了視覺模式的主體,國內不少學者受其理論的啟發:“人根本就不是觀看的主體……首先是被觀看的對象、客體,我們其實都是目光的獵物。”[4]
20世紀女權電影理論深受上述視覺文化理論的影響,克里斯汀·麥茨(Christian·Metz)、勞拉·穆爾維(Laura·Mulvey)等富有探索精神的女性主義評論家,揭示了好萊塢主流電影的男性中心主義(Phallocentrism)與窺視癖(Pcopophilia)的密切關系。[5]勞拉·穆爾維發現:主流電影的實際目的是為滿足男性的視覺快感而精心設計的,銀幕上的潛規則是女性作為景觀,男性作為觀看者而存在的,女性形象經過色情編碼后,成為了男性的欲望對象。穆爾維認為:只有揭示并摧毀這種性別霸權的視覺快感,才有可能孕育出新的觀看模式,這一發現直接開啟了女性主義電影理論的發展。而簡·坎皮恩的電影深受勞拉·穆爾維的影響,她在作品中有意識地使用了這些視覺符號,同時又顛覆了符號的所指。
一、 《鋼琴課》視覺權力模式的研究成果與反思
勞拉·穆爾維將弗洛依德的窺視癖理論轉移到了電影院,她認為影院提供了釋放“窺視欲望”的絕佳場所,它黑暗的環境給觀眾造成秘密觀影的幻覺(Illusion),觀眾將被壓抑的欲望投射到演員身上以獲得視覺快感的滿足。但銀幕上男女角色的分工是不同的,男主角作為觀眾“自戀”的鏡像投射是其認同的另一個自我,而女性則作為色情對象(客體)滿足(男性)觀者(包括銀幕上的男性角色)的視覺快感,兩者呈主動/被動,主體/客體的狀態。[6]是象征秩序(Symbolic)的再現。女性不僅在電影中被剝奪了話語權和主體性,女性觀眾也因為重溫了象征秩序固定了在社會中的地位。國內外學界普遍認為,在《鋼琴課》中此視覺權力模式受到了挑戰,甚至可能發生了“翻轉”。
“艾達彈起了一支熱情奔放、動人心魄的樂曲,她朝貝恩斯扭過臉, 可他平常坐的椅子上空無一人,艾達站起身, 小心翼翼地在房間內走動, 四下張望,她走到床邊, 向帳子里窺視, 但卻突然驚叫一聲, 急忙閃開。帳子拉開, 貝恩斯赤身站在她眼前。”[7]
這確實是電影史上具有紀念意義的一刻,女性身體不再作為視覺快感的表征出現在銀幕里,與此相反,男性被赤裸地端出呈現給銀幕上下的女性。史黛拉·布魯茲(Stella·Bruzzi)以穆爾維理論為基礎指出:《鋼琴課》消解了女人的被觀看性(to-belooked-at-ness)①“被觀看性”(to-be-looked-at-ness)來源于勞拉.穆爾維《視覺快感與敘事電影》一文。。“《鋼琴課》把這種標準關系完全顛倒了過來,注視者變成了女性,被注視的對象則變成了男性的身體”。[8]她的觀點不但在國外獲得了一致認可,國內學者也基本認同,都把這種觀看模式當成對父權制的成功反抗。
關于簡·坎皮恩電影的女性本位問題,無論是激進的女性主義者還是溫和的女性主義者都在一點上達成共識,即在簡·坎皮恩的作品里,一向被作為注視對象的女性成為注視者,而男人則成為欲望愷覷的對象,成為“性象征”(sex symbol)。[9]
——祝虹《簡·坎皮恩導演風格評析》
女性凝視的影片具有顛覆傳統男權文化的作用。《鋼琴課》的女性視點重新解讀歷史文化,確立女性的自尊與主體地位。女人講述自己的故事;女人看男人脫;不會說話的女主人公處于獨立發聲的位置,說話的權力自己掌握。[10]
—張世君《電影凝視中的性別意識》
觀看電影的快感己經被性別符號化,從一個女性主義者的觀點來看,這是應該進行反擊的現象……《鋼琴課》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強調了女性觀看的力量。女性不再是被觀看的對象,而是觀看行為的主體。[11]
——楊玉卓碩士論文《簡·坎皮恩影片中的女性形象再現》
作為一部女性主義電影,珍·康萍徹底顛覆了傳統“男性歡愉主義”的觀片模式,將女性的“被觀視性”倒轉為“觀視者”的角色。[12]
——(臺灣)宋國誠《深海中的琴聲——珍·康萍②Jane·Campion音譯,同“簡·坎皮恩”。的后現代女性電影》
國內外研究者一致認可《鋼琴課》中形成的“女性-觀看-主體,男性-被看-客體”的新模式,女性翻身做了觀看的“主人”,男性成了被觀看的“對象”,討論的焦點都集中在“誰”觀看上。然而其背后的價值指向,今天仍無人質疑:女性變成了觀看主體,男性充當客體,其思維方式或許與父權電影并無二致。
不少一貫反對激進女性主義的學者也在無意中踩進了這個“陷阱”,如《簡·坎皮恩導演風格評析》一文評價影片將男性變成“欲望客體”之后,接著說道:“她試圖建立的,只是在新時代當中男女關系之間的一種新的平衡……同時是對極端女性主義的一種反動,這種既激進又傳統的立場使得簡的電影成為尋找時代新秩序、新和諧的代言人。”[13]男性已然是“欲望客體”與“性象征”,又如何能擁有平等的主體與女性共享新秩序呢?誠如一位青年學者所言:
“大多研究者在論及視覺文化時,通常都預設了觀看者的主體位置,主要聚焦于‘看什么’‘怎么看’。即使在他們的批判涉及觀看者(觀看主體)時,這種批判也只是拿現實的觀看者與他們所預設的理想的觀看主體進行比較的結果……激進的女權批評家也突破不了這一局限,當她們抱怨女性只是被看的景觀和對男權觀看主體施以猛烈批判時,其終極目標是加入到觀看者(觀看主體)的隊伍中去。”[14]
對影片視覺權力模式的普遍好評恰恰展示了女權電影批評的局限性,且不論我們是否需要預設觀看主體,采取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無疑是值得反思的,此模式的實踐仍未避免“壓迫”與“反壓迫”,預設一個“女性”觀看主體,對于長期處于“被看”地位的女性確實擁有難以抗拒的誘惑力,可其思維又在不知不覺重演“父權中心”,讓女性走向了新的性別霸權。
二、 凝視的多重結構:作為“批判”與“匱乏”符號的男性
接下來兩節將以艾達的丈夫斯圖爾特(Stewart)所在的鏡頭空間作為分析目標,首先他是男主角之一,且在這部女性電影中代表著“傳統男性”,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再者,他在影片中的邊緣位置與實際研究中被忽視的狀態相當一致,至今沒有一篇論文以他為研究的起點,甚至在影片宣傳期間也少有該演員的身影,透過他能更全面地分析影片深層的性別政治。
電影理論家諾埃爾·伯奇曾說過:“能指者的工作,不論多么復雜細膩,只要它‘保持低姿態’,只要它不在那‘銀幕外的世界’和‘一般觀眾’之間拉上一道語義學噪音的帷幕,那么它必然是如此‘焦點發虛’,以致確實是看不見的。”[15]攝像機的鏡頭畫面總是引導著觀眾的認同,號稱“客觀’的銀幕畫面實際上并不是一種自然產品,它借著畫面的剪切、節奏的快慢、拍攝的角度、選擇拍“什么”給觀眾看……由此營造出一種“不在場”的觀看,對觀眾認同心理進行操縱與干涉,周蕾將其稱為“本身無法被看見的凝視”。[16]
在影片開始的場景中,艾達與女兒弗洛達來到斯圖爾特的家中:
“她們相依相偎坐在一起, 用手語交談。斯圖爾特出現在門口。他看了看妻子便走進屋來。弗洛拉向這個尚可接納的父親轉過臉來。斯圖爾特發覺自己破壞了她們親密無間的氣氛,不小心把艾達的書包碰到地上。斯圖爾特:‘我要離開幾天,我的土地不在一處, 得跑好幾個地方。這段時間,你們可以在這兒好好安頓安頓,等我回來, 我們就一切從頭開始。’斯圖爾特詢問式地望著艾達。艾達動了動睫毛, 表示認可。斯圖爾特如釋重負, 長吁一口氣, 就勢離開了。”[17]
電影里斯圖爾特如此局促不安的場景出現了好幾次,且總出現在想要討好妻子而被拒絕的時刻。從表面上看起來,作為一家之主的斯圖爾特似乎符合“傳統男性”的一切特征:
吝嗇庸俗:忽視精神價值,為省運費,拒絕搬走艾達心愛的鋼琴;貝恩主動退還鋼琴時,他用紐扣抵押毛利人的搬運費,遭到毛利人的鄙視。
專制:將女性視為私有財產,不僅擅自賣掉艾達的鋼琴,還強迫妻子為貝恩教琴。
暴力:窺看艾達偷情后試圖強暴妻子;發現了艾達給貝恩的表白信物,在狂怒中砍下了她的手指。
同時他還是19世紀西方殖民者的化身:用廉價毛毯和火槍交換貧苦毛利人的土地,充滿了對土地的渴望。
在此意義上,斯圖爾特被視為“象征秩序”的表征,接受鏡頭無情的批判。與此同時,電影中存在的第二種視覺敘述語言卻把斯圖爾特看作完全“被動”的角色,是值得同情的人物。為了便于分析此視覺語言復雜的結構特征,我們暫從敘事學理論借用“復調”一詞,為鏡頭“凝視”呈現出的復雜“情感結構”命名:復調視覺語言。它一共包含了四層復雜的結構,第一層為顯而易見的“批判”。而接下來的分析將展現另外三層情感結構。
影片第19分45秒:當斯圖爾特和藹微笑著詢問妻子是否需要一個晚安吻,艾達冷漠、疏遠的眼神讓他尷尬地退回自己房間的時候,他作為“惡”丈夫①影片有劇中劇的情節,上演虐殺妻子的“藍胡子”的故事,劇中藍胡子砍掉新婚妻子的頭,與斯圖爾特砍掉艾達手指相呼應,斯圖爾特作為藍胡子的隱喻而存在。的批判角色即被另一種敘述語言超越——充滿“同情”的視覺語言揭示出斯圖爾特得不到愛情與關心的落寞處境,暗示他一直處于“匱乏”(lack)的狀態中,此“匱乏”在他的家庭關系中體現為從屬與邊緣化的地位。
斯圖爾特作為一個“邊緣”人物,其軟弱的紳士風度與艾達的剛強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從故事一開始他就被排斥在妻子與女兒弗洛達的關系之外,之后則徘徊在妻子與貝恩的關系之外。他婚后未獲得與妻子同房的許可,情感需求得不到回應,甚至差點上演了強暴妻子的鬧劇;他被艾達當成觀看、撫摸的欲望對象,卻連碰觸妻子的身體資格都沒有……性壓抑的結果導致了他著迷般窺視艾達偷情的荒謬,而“斷指”情節更將這種匱乏演繹成“閹割”的隱喻。
弗洛伊德認為:女性流著血(月經)的創傷形象被象征秩序看成閹割掉陽具的“次等人”(不完整的男性),這種匱乏感迫使女性通過戀物的補償行為來逃避焦慮,恰如意義的“不在場”才需要符號的出現,替代符號不可避免的片面性,更說明焦慮的如影隨形。發現艾達送給貝恩的愛情信物后,斯圖爾特在嫉恨交加中砍掉了艾達的一根手指,以重建傳統家庭關系中丈夫的權威,這根被砍掉的“手指”正是男性權威的替代品,已然昭示他精神陽痿而“被閹割”(the castrated)的核心喻意。
影片最后,斯圖爾特主動成全了艾達與貝恩,此行為雖高尚,卻更印證了他在電影中純粹“被動”的性質,他完全承擔著影片敘事賦予他“被閹割者”的形象,沒有絲毫抵抗之力。
由此發現,除了顯性層面作為“批判”的凝視語言之外,復調視覺語言的第二層凝視卻將這個傳統男性描述成父權邏輯下的受害者、一個可憐蟲。該“目光”建立在把男性角色柔弱化、邊緣化、客體化的基礎上,以達到對父權制更深層次的批判。為進一步指出影片觀看模式的復雜之處,我們將繼續分析斯圖爾特如何從一個“被閹割者”慢慢滑入“傳統父權電影”中原本屬于女性的“受虐”與“物戀”的位置。
三、 病理醫學式目視與逃避“閹割焦慮”的再現策略
勞拉·穆爾維指出:好萊塢主流電影將女性視為風格化的“景觀”以滿足視覺快感,但這里存在一個問題亟待解決:如何掩蓋女性自身攜帶的“閹割符號”?因為一旦她的出現喚醒了觀眾的閹割焦慮,勢必讓視覺快感的獲得變成泡影。在閹割理論的框架中,男性代表閹割者的身份,而小男孩由戀母階段到承認父親的權威,是迫于害怕父親報復自己對母親有性的感覺而落得被閹割的下場,那么我們很容易推斷出:匱乏焦慮非但不會因為主角是男性而消失,反而更加劇了——此刻它不再是焦慮的“投射”,而直接顯示了恐怖本身,畢竟在“象征秩序”中,男性才是閹割的“執行者”。
在《鋼琴課》的文本中,“閹割”這個符號在兩個層面上出現過:一是影片對斯圖爾特的精神閹割。二則是女性電影的“凝視”本身正為逃避這原始的父權閹割,而調整了“男性形象”在影片中的再現方式。
“復調視覺語言”能維持住對男主角斯圖爾特的同情態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將他看做感染了父權制病毒的病人。他得不到愛情和關懷皆因他處在“象征秩序”中,“男權邏輯”蒙蔽了他的判斷力,切斷了他理解女性的渠道。他悖論地兼具了“閹割者”和“被閹割者”的矛盾身份,鏡頭中他神經分裂癥般的行為皆是“患病”所致,其分裂的身份導致他在家庭生活中的失敗,而非影片刻意的懲罰。斯圖爾特最終在妻子堅定無聲的凝視中聽懂了她的心聲,這一過程正如福柯的觀看寓言①福柯認為:盡管最初的醫學類似巫術,卻仍在將疾病空間化的同時建立起了覆蓋全社會的衛生監視系統,確立了醫學絕對觀看的合法性。所示:在女性主義“病理醫學”式的目視下獲得治愈的過程,宣告他已脫離“病患”獲得重生。[18]
而此凝視的第三四層情感結構又將斯圖爾特變成了施虐(sadism)與戀物的對象。導演坎皮恩說過:“這部電影想表現男人脆弱的一面,在性方面也一樣。他們需要被愛,需要有被保護的感覺。”[19]影片飽含父親般慈愛、醫生般精準的目光,嚴密注視斯圖爾特這個迷途知返的孩子。套用斯皮瓦克的話:他是西方精英女權主義從父權制下拯救出來的病小孩——拯救者搖身變成了女性。②此處套用斯皮瓦克語:“白人正從褐色男人那里搭救褐色女人”。[20]
由于影片承擔著把“傳統男性”從父權泥潭中拯救出來的重任,所以每當斯圖爾特溫柔地面對妻子,猶猶豫豫想要接近她的時刻,總是激起鏡頭對其產生保護欲。但作為“匱乏”符號的斯圖爾特又喚醒了影片潛在的閹割焦慮,于是這女性凝視的“施虐”欲望又被激活了……
勞拉·穆爾維指出父權電影有兩種女性再現方法以消除由女性匱乏(female lack)③“女性匱乏”一詞來源于弗洛伊德。引起的焦慮。方法一,讓女性成為帶罪之身或使其病態化,以便對其進行合法審訊或療愈,男性充當審判者和拯救者。方法二,假裝忽視“閹割”的存在,將女性當成完美的“戀物對象”,以極端美化掩蓋“閹割”恐懼。
有趣的是我們在這部女性電影中也找到了同樣的再現手法,只不過“斯圖爾特”替換了“女性”的位置,他所在的鏡頭空間實際上已全部“客體化”了。如影片開頭毫無道理的棄琴①影片為制造沖突必須丟棄鋼琴,從而斬斷丈夫與艾達之間發生愛情的可能性,為新關系的開始奠定基礎,、為土地賣琴、逼迫教琴、斷指等一系列情節指認他犯了罪,影片甚至報復似地讓他看到妻子偷情的畫面,甚至讓其在欲望驅使下偷窺了整個過程以羞辱自身,即是“確定罪犯,通過懲罰或者寬恕,對有罪的人施加控制并使之屈從。”[21]斯圖爾特始終不知自己為何討好不了妻子,影片最后他的醒悟讓批判、同情、虐待狂式的復調視覺語言在女性主義冰冷的目視下,同時奏響一首瘋狂的“女獨裁者”之歌,然而僅僅施虐是不夠的……
這是影片的某一場景:被囚禁在家的艾達思念情人貝恩,于是把丈夫當成替代品,主動撫摸他的身體,不明就里的斯圖爾特頗為驚喜,但很快發現事情不太對勁:他不能碰艾達。斯圖爾特不解地問:“為什么我不能撫摸你?我很想那樣做,你到底喜歡我嗎,艾達?”艾達嚴肅而專注地看著丈夫, 沒有做出任何回答。[22]這一場景有點可笑,斯圖爾特的“被動”此刻達到了頂峰,趴在床上的他甚至連觀看艾達的機會都沒有,完全成了她釋放生理欲望的工具。
斯圖爾特的扮演者美國演員山姆·尼爾(Sam·Neill)長相英俊,用導演的話來形容“長著一副‘媽媽的漂亮寶貝’的模樣”,與一般電影中這類壞人的形象不太一樣,坎皮恩覺得這有助于觀眾“意識到他的真性情,把他當成一個人來看”。[23]漂亮的外貌如何有助于觀眾對他的認同?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應考慮“戀物式”的視覺再現手法如何在他身上運用。
片中斯圖爾特光滑的背部特寫,清晰的肌肉線條充滿了男性身體之美,正如女權電影理論中所批評的那樣,父權電影中“陳陳相因的大腿特寫或臉部特寫在敘事中結合了另一種色情主義,分解的身體的局部破壞了文藝復興的空間,破壞了敘事所要求的縱深幻覺,它給予銀幕以平面、剪紙或者肖像畫的性質,而不是逼真性。”[24]而斯圖亞特的身體以同樣的方式隨著艾達手部的滑移逐漸展現給觀眾,其背部、臀部、胸部、腹部的局部特寫消解了由男性整體形象引發的“閹割”焦慮,而這種欲望的滿足是屬于艾達的,觀眾只要認同了艾達,便能在“鏡我”投射的幻覺里間接占有斯圖爾特,如此一來“英俊外表”實際上成了女性觀眾獲得“戀物癖”般視覺快感的必要條件。
到此,我們完成了對影片“復調視覺語言”的開掘工作,揭示了《鋼琴課》具有四層復雜的“結構性”凝視,女性主義“病理醫學式”目視貫穿了影片的始終,在其批判、同情、“虐待狂”式和“戀物癖”共存的復雜情感結構中,斯圖爾特既是情節發展的基礎又是女主角完成自我建構的工具、既是影片性別政治訴求的批判對象又是無力抵抗敘事操控的小人物、既是暴力專制的父權制化身又是女主角欲望的客體、既是需要拯救的無辜病人又是施虐的對象、既是父權制“失敗”的作品又是完美的“物戀”對象……不論多么矛盾皆出于影片建構“自我”時的敘事需要,斯圖爾特作為影片的一枚棋子,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穆爾維指出男權邏輯本身就是虛幻的“人造”產物②穆爾維認為:男性視覺快感滿足機制本身是“菲勒斯”中心下的鏡頭語言所創造,它是虛幻的,是男性一手炮制出來的,應該也必須要打破這種建立在性別歧視上的滿足,以創造出更自由、非霸權的視覺快感。,而影片又悖論地依賴這一虛幻產品創造出新的女性觀者。這一系列復雜的視覺策略使影片具有了多重的觀看任務——批判與同情、揭示虛幻和創造虛幻、客體化與病癥化同在,女性凝視在不知不覺中滑入了“觀看”的陷阱。
四、 告別勞拉·穆爾維的視覺權力模式
通過分析,我們發現影片中主動/被動、觀看/景觀的二元對立依然存在。穆爾維式的視覺快感具有絕對性,因此理論上講《鋼琴課》為女性觀眾量身定制的視覺快感也反過來否認了男性觀眾實現認同的可能性。可當我們把視線拉回到1993年的法國戛納電影節上,卻發現實際情況并非如此。
據法國當地媒體報道:在正式的首映式上,放映廳人滿為患,數百人手持入場券卻被主辦方攔在門外,為了安撫這些憤怒的影迷,主辦方只好臨時安排他們到另一間放映室,手忙腳亂地湊來一部影片給他們觀看,以免發生斗毆。[25]令人窒息的追捧幾乎嚇到簡·坎皮恩本人,她沒料到影片會如此受歡迎。于是,疑惑隨之而來:那么多自愿買票觀看本片的男性觀眾獲得的觀影樂趣該如何解釋?
周蕾提出要注意阿爾都塞闡述“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再生產”的方式,因為意識形態的文明機制會“召喚”(Interpellation)個體回應“主體身份認同”的幻覺,使個人想象自己自愿進入體系中,以此促進資本主義生產條件的再制。此“再制”通過兩種方式完成:一是召喚個體建立主體,二(同時)讓個體屈從于意識形態的物質實踐。為了能進入“文化身份認同”體系中,個體將不計任何代價縫合認同裂縫,即使知道其后果是——“消極安插進既存的論述位置,神奇的充滿力量卻也同時神奇地缺乏力量;面臨失落的威脅以及不真實的重新擁有感,臣服于象征秩序中絕對他者那有著閹割力量的凝視。”[26]
此文化接受過程包含了積極回應和表演的性質,是一種想象性回應身份召喚的感知運作機制,因此,電影的“意識形態召喚”將縫合那些所謂“不可能的觀眾”的認同裂縫,成功實現“認同”并達成觀影目的,這大概可以解釋《阿拉伯的勞倫斯》《末代皇帝》這類“東方主義”濃厚的西方電影對族裔觀眾的吸引力。
周蕾進一步指出:“不可能的觀者”(如觀看父權電影的女性觀眾、觀看殖民宗主國形象宣傳片的被殖民國觀眾、或觀看女權電影男性觀眾等)的認同幻覺并非絕對被動,它會以一種懷舊的戀物方式,進行完美自我的“鏡像”追憶,但同時也會提醒自我在體系中的“閹割”位置,這將有助于自我發現和孕育反抗霸權的意識。她在分析《末代皇帝》一片對族裔觀者的跨文化身份召喚中曾指出:不可能的觀者對“想象共同體”的依賴促使他主動認同此被閹割過的文明體系,其實正有賴于他將過往的文明輝煌當做戀物對象,以彌補此文明已被閹割的事實。
“不可能觀者”成功縫合了認同,加上《鋼琴課》在男性身上也能成功使用此視覺權力模式,都說明穆爾維定義的“男性觀看”——“女性景觀”的模式并不成立,所謂的“不可能觀者”并非真的被束縛在“認同分裂”的位置上,然而在《鋼琴課》上映了近20年的時間中,其對穆爾維模式的運用仍不斷被研究者津津樂道,顯然對此缺乏必要的警惕。
在“凝視”的歷史書寫中,從笛卡爾的“絕對觀看主體”到“他者”登上權力舞臺,“他者”就作為建構、分裂、干擾、吞并觀看主體的異質力量越發顯出其威力。福柯讓“主體”在被看中死亡,而德勒茲隨即以“生成的他者”宣告他者與自我的同一。由此來觀照女性主義視覺理論的發展,可以很明顯地看到:以勞拉·穆爾維為代表的二元對立、主客二分式的女權視覺理論,仍停留在古典階段(本體論哲學)的理論框架中。因此,不論是考慮到今后女性電影理論的健康發展或是穆爾維理論本身的局限,現在都到了超越和告別勞拉·穆爾維的時候。
[1][3]陳蓉.凝視[M]//趙一凡.西方文論關鍵詞.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349.
[2]柏拉圖.理想國[M].張竹明,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9:242-250.
[4][14]朱立元,索良柱.“我們都是目光的獵物”——福柯與視覺文化批判[J].江蘇社會科學,2009(4):20.
[5][9][13]祝虹.簡?坎皮恩導演風格評析[J].當代電影,2003(2):62.
[6][21][24]勞拉?穆爾維.視覺快感與敘事電影[M]//吳瓊.凝視的快感.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1,11,16.
[7][17][22]簡?坎皮恩.《鋼琴課》電影劇本:加列娜?克拉斯諾娃記錄[J].蔡小松,譯.世界電影,1996(6):113,102,121.
[8]丹娜?蘭波.簡?坎皮恩電影中的女性問題[J].當代電影,2003(2):65.
[10]張世君.電影凝視中的性別意識[J].當代電影,2004(3):106.
[11]楊玉卓.簡?坎皮恩電影中的女性形象再現[D].長春:東北師范大學,2008:12.
[12](臺灣)宋國誠.深海中的琴聲——珍.康萍的后現代女性電影[EB/OL].(2006-06-22)[2012-4-2]http://pots.tw/node/693.
[15](美)諾埃爾?伯奇.電影實踐理論[M].周傳基,譯.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2:G.
[16][26]周蕾.婦女與中國現代性[M].蔡青松,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26,40,35.
[18]米歇爾?福柯.臨床醫學的誕生[M].劉北成,譯.北京:三聯書店,2011:25.
[19][23]簡?坎皮恩.我是俗人不是美學家——簡坎皮恩談訪錄[J].霍文利,譯.當代電影,2003(2):55,54.
[20](美)佳亞特里?斯皮瓦克.從解構到全球化批判——斯皮瓦克讀本[M].陳永國,賴立里,郭英劍,主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116.
[25]Ansen?David.Charles? Fleming.Passion for Piano[J].Newsweek,1993-05-3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