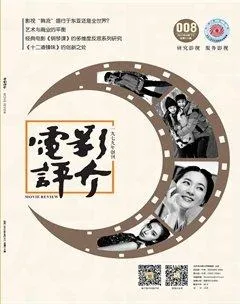歷史車輪的碾壓:新世紀文學與電影的角色互換
盧翩翩
電影與文學相攜已走過了一個世紀的旅程,雖然與文學幾千年的歷史相比,電影僅算得上是“新生兒”,其百余年的歷史還不及文學年歲的零頭,但它卻以摧枯拉朽之勢改變了文學的社會地位,甚至成為新時期文學不得不倚靠的“拐杖”。20世紀80年代以前,文學的地位要遠高于電影,處于“神壇”地位,高高在上,遙不可及。但短短20年時間,文學與電影的地位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今的電影成為大眾的“寵兒”,而文學則有些無人問津。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之后,電影以絕對優勢成為文藝界的“領袖”,而文學則成為屈尊于其下的“子民”。
一、 被電影“綁架”的文學——“神壇”地位的架空
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電影的文學改編之風就已盛行。許多優秀的文學作品如《天云山傳奇》《芙蓉鎮》《老井》等均由導演進行二度創作搬上銀幕。中國的第四代導演謝晉、吳貽弓、吳天明抱著“向文學致敬”的心態將文字影像化,并且將其永遠留在了視覺化的底版之上。但是這一時期導演對文學的改編是有限的、極為克制的,這些銀幕作品基本上是對原著的翻版,無論是精神價值還是場景細節,甚至是語言都對原作進行毫無改動地挪用。“文學電影化”的現象僅僅是文學作品本身的“觸電”,作家們仍然處于封閉的空間中進行自我創作。
進入新世紀以后,隨著電影行業的愈加蓬勃。許多作家已經無法再沉下心來專心創作,而是出現了集體“觸電”現象。首先表現在文學作家的轉行。受電影高利潤的經濟收入影響,作家漸漸開始淌電影這趟“渾水”,而能夠堅持初衷“獨善其身”搞純粹文學創作的人越來越少。一批作家出身的“大軍”浩浩蕩蕩地集體進入電影圈,被冠名之“編劇”。新世紀比較有名的“觸電”的作家有劉震云、嚴歌苓、方方等,其中劉震云的作品《手機》《我叫劉躍進》以及《一九四二》等都被搬上銀幕。嚴歌苓的作品也多次被改編成電影,她的《天浴》《金陵十三釵》以及《陸犯焉識》等作品其本人都擔任編劇參與電影創作。
另外,新世紀電影與文學的關系的重點其實還在于“觸電”作家思想及創作方式的改變,即文學作品的“電影化”。作家參與電影編劇的經歷慢慢滲透并影響到文學的創作過程。編劇受電影視覺化的影像,在之后的創作中開始不由自主地趨向電影化文本的寫作方式,有意或無意地運用到電影的敘事技巧。作品中的文本敘事和心理描寫減少,而有利于視覺呈現的動作、沖突或感官感受描寫的篇幅增加,小說本來所獨有并引以為傲的語言、結構統統退居次要位置。
二、 暢銷小說與網絡小說改編的甚囂塵上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電影改編作品,大部分是對經典文學的改編,充裕的人文精神與思想價值是導演改編的主要標準,如陳凱歌根據史鐵生的《命若琴弦》改編的《邊走邊唱》,霍建起根據彭見明的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那人那山那狗》等,都對人性與人生進行了極為深刻的探討,這些電影除了給人留下一望無際的沙漠、潮濕昏暗的江南小鎮等視覺的印象外,更重要的是傳達了人情的溫暖和對宿命的追問。但隨著新世紀電影愈加商業化與市場化,如今,導演對文學的改編標準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由原來的精英化與經典化向通俗化轉變。
如今有作家已經開啟了由作家到導演身份的轉換,近幾年最新崛起的兩位新銳小說作家郭敬明和韓寒便是代表。兩位作家的暢銷小說培養了大批閱讀群體,自2013年起,郭敬明陸續將自己的小說作品《小時代》以系列形式搬上銀幕。韓寒也于2014年將自己的作品整合拍攝成《后會無期》開啟導演處女秀。這種資源整合與文學作品的視覺化一方面使小說創造的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也成就了作家本人。另外,電影改編陷入了唯觀眾喜好而定的怪圈,尤其是對網絡小說的改編。繼第一部網絡小說改編的電影《第一次的親密接觸》上映之后,網絡小說改編之風便甚囂塵上,2011年《失戀三十三天》和2013年趙薇根據網絡小說改編的《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的票房成功另眾多觀眾與影視工作者瞠目結舌,網絡小說產生的巨大效益再不容忽視。一方面小說較高的點擊率與閱讀人群培養了電影的一部分固定受眾,另一方面,被改編之后的電影與之前的網絡小說的比較掀起的討論高潮又為電影宣傳做了很好的鋪墊,可謂達到“虛張聲勢”“一石二鳥”的效果。另外一些網絡小說改編的影片例如陳凱歌的《搜索》,徐靜蕾的《杜拉拉升職記》等成功使網絡小說的電影化之路更為平坦。
當然,這種通俗文學的電影改編也面臨著許多問題。網絡小說的出現造就了一批寫手,更使小說成為一種多人聯合創作的“速成品”。但此種創作的弊端也顯而易見,由多人創作的作品不比單個作家一氣呵成的作品來得天衣無縫。小說難免融入不同個人的寫作思想,小說各部分之間容易產生裂隙與斷層。
三、 影像觀的顛覆——性元素的赤裸化
當今社會電影作為視覺文化以絕對優勢壓倒以小說為代表的紙媒文化已成為既定事實。美國當代文化批評理論家丹尼爾·貝爾說:“目前居‘統治’地位的是視覺觀念。聲音和景象,尤其是后者,組織了美學,統率了觀眾……”[1]然而,電影并不是一種單純的存在,電影與夢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著名美學家蘇珊·朗格認為,“電影與夢境有某種關系,實際上就是說,電影與夢境具有相同的方式”“這種美學特征,與我們所觀察的事物之間的這種關系構成了夢的幾個特點,電影采取的愉悅這種方式,并依靠它創造了一種虛幻的現在”。[2]在這種巨大的夢境背景之下,女性成為了幻想對象的呈現。尤其進入新世紀之后,“女性電影”或以女性為主要表現對象的電影成為許多導演的首選。
不可否認,上個世紀的八九十年代也有一些關于女性的電影出現,但當時的電影并非純影像化的呈現身體的裸露,而是通過這種方式挖掘人性中更為深刻的價值觀念,甚至上升到對人的存在的意義解讀。例如陳沖在1998年根據嚴歌苓的同名短篇小說改編的電影《天浴》中有幾次出現知青女孩文秀的裸體,但這種肉體的呈現并不會給人帶來視覺上的愉悅或產生非分聯想,反而給觀眾帶來精神的陣痛。而新世紀由小說改編的電影卻曲解原著作者的意圖,將小說中的女性變成電影中唯一的主體,淡化其所在的社會背景,甚至淡化精神價值的呈現。
2012年王全安導演的電影《白鹿原》一上映便批評聲不斷,原因是導演將“一部渭河平原50年變遷的雄奇史詩”改編成“一個女人和幾個男人”之間的情欲故事。張藝謀的《滿城盡帶黃金甲》中從宮女到皇后的“胸器”成為撩撥觀眾情欲的“殺手锏”。《金陵十三釵》更是將肉欲、身體置于道德抉擇中的重要一環,妓女用身體換取女學生們的清白,這種赤裸的女性身體價值的呈現不能不說是導演迎合商業、迎合觀眾之后所作出的妥協。
如今的電影改編已經進入“相似式”的創作階段,原作僅僅作為改編的素材,電影成型之后與原作的差距較大,甚至是另一部作品。[3]電影創作已經不再唯文學馬首是瞻,而是更有“主見”地開辟自己的道路。文學只是作為一種誘因或者噱頭,影片難以真正呈現文學作品所體現的核心內涵和精神價值。例如張藝謀的新作《歸來》在上映之前,一直宣稱是嚴歌苓長篇小說《陸犯焉識》的改編,但電影刻意消解了原著中的文革背景,將整個故事改編為陸焉識和馮婉瑜的愛情史。電影改編越來越將原著作為取材的來源,借用文學作品的故事外殼為電影披上華麗的外衣,與之前所強調的“忠實”與原著的理念截然相反。改編的方式越來越由“忠于原著”或“忠于導演本人”向“忠于觀眾”發生偏移,文學到電影的改編加入了一些藝術之外的元素。這種改變到底是緣于導演創作觀念的變化還是觀眾的審美標準的變化不得而知。被影視奴役的文學如何在新時期突破魔咒,堅守文化的主體性與獨立性,從被改編的命運中抽離自身,將成為新世紀文學亟待解決的問題。
[1](美)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M].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社,1989:156.
[2]張成珊.談“電影的文學性”[J].電影新作,1983:1.
[3]趙慧娟.新世紀文學與電影的互動影像[J].天津師范大學學報,200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