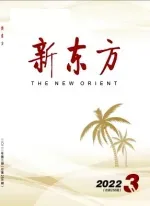試論當代民族文化自信與傳統優秀文化的內在關系
無論是否按照“軸心文明”的觀點看,古典的華夏文明都是一種自足的文明型態。在現代世界的諸文化型態里,今日的中華文明仍然還是一種獨特的文明形態。亨廷頓將現代的中國仍然看作是儒家文明型態,這一看法只能說是一種方便的說法,為他的“文明沖突”論提供一個方便于人們記憶的儒家符號而已,很難具有實質性的意義。但他至少承認現代的中華文明是一種不同于歐美、阿拉伯、日本諸文明型態的文明。僅此一點,還可以看出亨廷頓的新文明類型說有某些合理因素,以及他個人學術眼光的敏銳之處。
一、中國傳統文化的三大特點
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個人言人殊的大問題,僅從主流的哲學形上思維來看,特別是與猶太—基督教一神論文化傳統的比較來看,它具有明顯的三大特征:
其一,與猶太—基督教的一神論文化傳統相比,中國傳統文化主要特征就是:在一元真實的“氣機”世界里尋找解決人與自然的矛盾,在人的世界里尋找解決人類的問題,而不借助虛幻的宗教神學力量來解決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問題。這一點在《易傳》、先秦道家、秦漢以后的儒家思想中表現得最為明顯。盡管《易傳》哲學也開創了“神道設教”的宗教傳統,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宗教”并不是一神教意義下的宗教,而是一種“人文宗教”(唐君毅語)。這種“人文宗教”實質上是一種特殊的多神論,即在“敬天”的旗幟下,各自以自己的祖先為神祗。
其二,秦漢以后,不斷吸納、綜合諸子百家思想,尤其是道家思想的廣義新儒家,雖然也有“敬天法祖”的宗教神學思想內容,但構成儒家之為儒家的根本精神特質,就在于不相信一神的上帝。儒家只敬重自己的祖先,尤其是與自己生命有直接關系的祖先。由祭祀祖先的文化所提煉出的“慎終追遠”意識,從根本上說不是宗教意識,而是一種“歷史意識”。傳統的中國人把人在時間歷程中的存在以祭祖活動的方式上升為一種“歷史意識”。這種“歷史意識”在現實的生活中以兩種具體的方式展開,一是重視祖先;二是重視下一代。普通人重視祖先的歷史意識是以對祖墳、宗族祠堂的重視的典型方式表現出來;在倫理觀方面就是以重孝的觀念表現出來。而普通人重視下一代的歷史意識,就是以對家庭、家族男性成員的高度重視方式表現出來,并以“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倫理觀念為這種歷史意識進行理論的辯護。這可以說是傳統中國人的普遍“歷史意識”。
相對于這種活生生、普遍的“歷史意識”而言,中國歷代王朝重視修史的政治傳統與史學傳統,反而是這種普遍“歷史意識”的一種異化形式——即傳統中國人普遍的“歷史意識”以意識形態化的形式表現出來。然而即使這種官修史學也仍然以歪曲的、異化的形式展現了中國傳統文化重視人類歷史的連續性,以及從歷史經驗中吸取現實的經驗、教訓的思維方式。在現代社會出現之前,幾乎還沒有一個民族有中華民族如此重視人類的政治生活史、社會生活史的傳統,有如此比較完整的“二十五史”,同時還有很多其他的逸史、帝王起居錄等。當然,這些史書中記載的事件的真實性,有些需要考訂。而這種“歷史意識”中蘊含的輕視女性的負面思想內容也不容忽視。
其三,相對于基督宗教“千禧年”所虛構出來的,由上帝主宰的“末日審判”的未來意識而言,中國傳統文化由“歷史意識”所孕育出的具有深刻人文關懷的“慎終追遠”意識,以及“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思想觀念,恰恰是在一元的真實存有的世界里,以具體的人類生命繁衍為出發點而恰當地表達出了對未來的真切關注,以及對于生命超越性的重視。中國的道家、中國化的佛教所具有“法嗣”意識,以及他們的尊重自然、提倡素食的思想觀念,既表達了對未來的重視,也具有深遠的環境意識與可持續發展的意識。而現代西方的環境哲學、環境倫理學才在一定的程度上表達了這種自覺。但由現代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所發展出的現代西方文化命中注定了要走一條先破壞全世界的環境,然后才去拯救環境的道路。就現代的工商業文明類型所發展出的進步、進化的人類歷史觀而言,傳統中國人對未來的認識并沒有這種單線進化、發展的觀念,而只有變化、日新的觀念,不過可以與現代文明的進步、進化觀念相融。
二、當代中國文化自信力的三個來源
基于上述對中國傳統文化形上思維三大根本特點的認識,筆者認為,當代中國文化的文化自信力,首先應當建立在對自己民族文化傳統有一個真切認識的基礎上,在廣闊的比較文化視野里確認自己民族文化傳統的真正優秀部分。我們的文化自信應當建立在自己所擁有的“歷史意識”與未來意識之上,而不是什么“宗教情懷”、以及“末日審判”的無妄恐懼和預言。而傳統文化的“氣一元論”思想,以及由此形上思維而發展出來的中醫學的知識系統與治療技術系統,更是值得認真發掘。我們應該理直氣和地宣稱:中醫是一種不同于現代西方醫學的知識—技術系統,更不是現代西方醫學所謂的“補充醫學”或“替代醫學”。在中醫系統里的中草藥是一種對自然的污染最小化、對人體的副作用最小化的藥物,值得大力推廣。至于當代中草藥自身受到污染而引起藥效與對人體的負作用問題,是另外的問題,與中草藥本身的少污染與少副作用特征不相關。
其次,當代中國文化的自信力,也應當奠定在近、現代中國發展出的現代文化傳統的基礎之上。一部近、現代中華民族史,既是熱愛中華文化的有志之士抗擊外侮,維護民族獨立、民族文化自尊的可歌可泣的歷史;也是現代中華民族果敢地揚棄自己傳統中不適應現代文明、大膽吸收現代西方文明的革故鼎新的壯烈的歷史。在這一過程中,經過艱難曲折的文化選擇,最終正確地選擇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體系,以社會主義形式實現自己民族文化的現代化轉化。而中國共產黨人在現代文化的建設過程中,既清理了傳統文化中不適應現代性的陳渣,也吸收了傳統文化中仍有生命力的精華。因此當代中國的文化自信,還有來自近現代以來一切追求進步,維護民族文化傳統的進步思想傳統,和以中國共產黨人為主體所建構出的現代民族文化的自覺意識與獨立意識。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就已經代表共產黨人為現代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提供了一個綱領性的說法,那就是要建立一個民族的、大眾的、科學的新民主義文化。民族的,就是要在世界諸民族的文化之中確立現代中華民族文化的獨特性。大眾的,就是要發展出適合最廣大的普通民眾精神提升要求的現代性的新文化,這一思想后來被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馮契提煉為極富哲學意味的一個概念,即“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科學的,就是要充分學習西方人擅長的知識理性、科學理性、邏輯理性等精神,用切實有效的方式改造自然、改造社會,增進人民的福祉,進而增進人類的福祉。總而言之,我們的文化自信力也要建立在近、現代文化新傳統的基礎之上。
最后,弘揚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自信,在理論上要努力避免晚明以來“西學中源”說的老調,認真反省當代中國文化、學術研究的獨立性問題。對于后面一個問題,尤其要給予高度的重視。舉例說來,德國思想家馬克斯·韋伯,他研究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關系,我們就有人跟著研究儒家倫理、佛教思想對北宋以來中國經濟的影響。西方學術界強調基督宗教之于倫理的根基意義,中國的儒學研究者就大談儒家的宗教性。當代西方學術界涌動著后現代思潮,我們的學術界也大談“后現代問題”。總而言之,歐美學術界,次則日本學術界熱衷談論的問題,馬上在中國就成為最前沿的學術問題,而中國社會自身的問題研究反而顯得不重要了,中國的學術界似乎就成了泛西方學術思想販賣的市場。這是一種非常值得警惕的“文化奴化”與“學術奴化”現象。當代中國學術,尤其哲學人文社會科學要以解決中國現實問題為自己的根本任務,要以講好中國近百年發展歷史的故事和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中國社會進步與翻天覆地的故事為己任。這當然也要從學術與理論上反省我們在現代過程中的種種失誤,但更主要的是要講清楚中國社會進步的根本原因。
當前,習近平總書記將中國傳統文化看作是現代中華文化的“基因”,高度地肯定了中國傳統文化在當代發揚光大的必要性與可能性。但在弘揚傳統文化的過程中,不應該忽視中國的近、現代文化傳統。
三、重省西方現代文明,探索人類文明的新方向
弘揚傳統優秀文化,確立當前的民族文化自信,還應當深刻地批判近、現代西方殖民文化的血腥與強盜性質的一面,不要簡單、天真地認為,西方近現代文化僅給中國送來了科學、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等“上帝的禮物”。1840年的鴉片戰爭,接著后來的八國聯軍共同侵略中國、掠奪中國的財富,一方面導致了腐朽的清政權的迅速倒臺,但同時也將中華民族推向了真正的水深火熱的苦難深淵。這很難說是西方文化的文明表現,恰恰相反,這正是西方文化在近現代歷史過程中所表現出的野蠻性。商業資本的唯利是圖,借助發展起來的先進的殺人武器,打碎像瓷器一樣精美的中華文明。這與其說是文明的傳播,還不如說是強盜的搶劫。如果說,中世紀基督教的十字軍東征因為武器的落后而沒有成功,那么,從阿拉伯人那里學習了各種數學知識,從中國人這里學習了火炮、指南針等技術后,基督教文化養育下的歐洲人發展了更加先進的殺人武器,從而征服了文化上比他們精致的中國人。
近代以來的中國人主要向西方學習實用知識,首先是保護自己不被西方人搶劫、殺戮;其次是學習各種開發自然的技術知識,以改良自己的物質生活狀態。在今天,第一項任務接近完成,但還不是很有保證。第二項任務還在學習、追趕的過程之中。至于如何做人,過人的生活,如何管理社會,我們不必全向基督教的文明學習。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在這方面也有歐美人所沒有的長處。不理解這一點,就無法建立現代民族的“文化自信”。
更進一步地講,近、現代西方率先發展出科學、自由、民主、平等等價值與文化理念,也不只是在歐洲的基督教文化中才能產生,是他們的文化專利。其實,稍微熟悉中國晚明社會歷史的人都知道,中國傳統社會內部也發展出了自己的早期現代性,也有自己的“早期啟蒙”思想。這一點,有一大批中國學者,如胡適、梁啟超、侯外廬、馮契、蕭萐父等人用大量的史料與思想史資料證明并論證了。蕭萐父先生更是精辟地論述道,相對于歐洲近代化過程中反對“宗教異化”,建立現代文化的歷史任務而言,中國近現代文化的主要歷史任務恰恰是要反對“倫理異化”。就今天的中國社會而言,反對“倫理異化”要從兩個方面展開自己的現實任務,一是大力破除來自于前蘇聯的極左、僵化、教條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對于現實的束縛;二是要防止簡單地照搬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的思想觀念,特別是一系列頗為誘人的價值觀念與中國傳統的思想觀念和道德觀念,認真研究經典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著作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代的社會現實與當前的國際社會現狀,以社會主義現代性的生產、生活方式與新文化理想,實現中華民族的現代性轉化與民族復興的任務,進而引領當今世界的現代性文化。
必須承認,歐洲的近現代科技文明發展速度快于當時的中國,更具體地說,他們在鼓勵人們開發自然資源的能力上優于中國文化,因而在近、現代文明的形成過程中發展出了諸多優勢。但從人類的整體生存、發展,尤其是幸福生活的諸方面看,現代西方文明未必就能給全人類帶來真正的福祉。不能盲目地歌頌現代西方文明,而是要深刻地意識到,現代西方文明在給人類帶來了諸多便利的同時,也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危機。而在反思現代西方文明給人類帶來的嚴重危機的時候,不僅中國傳統文化可以提供不同于歐美文化、阿拉伯文化的獨特內容,而且當代中國以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形式實現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轉化的實踐模式,對于當今世界上后發現代化的國家無疑可以提供新的實現現代轉型的新經驗。對于這兩點,應該有足夠的文化自信。
當然,弘揚傳統文化,確立民族文化自信,確立民族學術研究的自主性、獨立性,絕對不是要拒絕學習外來文化,拒絕翻譯、介紹外來學術思想,恰恰是要認真吸收外來學術,特別是泛西方意義上的學術精神,認真研究中國自己的問題,努力發掘中國文化中優秀的思想傳統,對當代世界問題、人類問題的解決提出中國人的解決方案與思想建議。在處理民族文化傳統與外來文化的關系問題時,可以參酌費孝通的晚年說法,略加調整表述如下: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相通,和諧相處,相互提升。這樣,在弘揚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確立當前民族文化自信的同時,就不會把現代中華民族重新導向一個封閉的、自大狂的可怕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