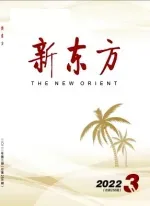“民間視角”下海南冼夫人文化的變遷及其文化意蘊
引言:海南冼夫人文化研究的“民間視角”
長久以來,被周恩來總理稱為“中國巾幗英雄第一人”的冼夫人一直以維護國家統一的歷史形象為人所稱道。這種形象的形成既得益于書寫正史的史官對于冼夫人的塑造,也與諸多文人學者的研究相關。由于后者又往往依據前者的記載而展開自己的論述,因此,代表著歷朝歷代中原政權統治理念的正史在諸多文人學者的助力下塑造了一個“國家視角”下的冼夫人。這位冼夫人對于結束中國數百年分裂動亂的局面所作出的歷史貢獻自然毋庸置疑,問題是,對于她的歷史書寫是否只有“國家視角”一種解讀?是否存在與“國家視角”相對的“民間視角”下的冼夫人?
對于“民間視角”的思考并不是無的放矢。美國著名中國史研究專家保羅·柯文(Paul Cohen)教授認為自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的中國史研究之所以逐漸突出了區域研究的重要性,就是為了應對區域性與地方性的巨大差異,從而改變“平淡無味地反映各組成部分間的最小公分母”式的舊史學研究范式[1]。這一觀點與近年來中國史學界不斷反思地方史演變為國家史副本的觀點不謀而合[2]。有學者更是直接指出:“中國地方史的敘述,長期被置于一個抽象的中國為中心的框架內……是導致許多具有本土性的知識點點滴滴地流失,或至少被忽略或曲解的原因……”[3]越來越多的社會歷史研究者嘗試從區域社會的角度重新思考歷史研究,而不再是積極尋找地方社會歷史中的素材來為宏大的敘事架構提供佐證。在這場強調地方社會歷史研究應當突出地方性的學術思潮中,海南歷史文化研究也面對同樣的問題。冼夫人文化研究過分關注“國家視角”只不過是舊有海南歷史文化研究的一個典型事例而已。
換言之,歷史學者對“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舊史學觀不斷提出反思,希望建構一種霍布斯鮑姆(Eric Hosbawm)眼中的“草根史學”或稱之為“自下而上的歷史”,正是為了突出對于民間視角的關注。“民間視角”不同于國家視角偏重于正史的考據與論述,而是關注地方精英、民眾百姓以及民俗活動在歷史發展中的意義與價值。當然,強調“民間視角”,“并不意味著研究停留在對草根社會的關注,而是要從民眾的角度和立場來重新審視國家與權力,審視政治、經濟和社會體制,審視帝王將相,審視重大的歷史事件與現象”[4]26。“民間視角”的呈現不僅可以為我們了解曾經發生了什么以草根的感受,為我們呈現國家是如何真正作用于地方進而與地方一同構建了一個完整的地方社會的,也可以為我們了解歷史延續到現在變成了什么樣子提供真切的一手材料。梁啟超當年批評舊史學只知陳跡不知今務,而“民間視角”的介入至少可以幫助我們不至于重蹈這一覆轍,使我們有寶貴的材料充分體味歷史在民間的完整性與延續性。
如果歷史學視角的轉換反映出歷史文化研究舊有范式的重要問題,那么,我們也該冷靜思索:是否真的應該存在一個鮮活的“民間視角”下的冼夫人?尤其是在海南瓊北、瓊東一代冼夫人文化至今仍有廣泛影響的當下,流傳于當地的冼夫人文化與正史所記究竟是不謀而合還是貌合神離?海南冼夫人文化研究在完成了對正史的梳理之后,是否應當進一步關注我們看待歷史的方式及其對當下的啟示?而對于這一問題的思索必須從海南冼夫人文化變遷的歷程說起。
一、先民接納與國家冊封:英雄化的冼夫人
關于冼夫人的記載見于《隋書》《北史》《資治通鑒》《正德瓊臺志》《道光瓊州府志》等正史之中。根據正史記載,冼夫人生活于南朝梁武帝天監年間(502-519)至隋文帝仁壽年間(601-604)①。冼家世為南越首領,在嶺南之地是掌控十余萬家的部落首領,在當地絕對算得上世家豪酋。其夫家馮保原本是北燕苗裔,其先人在嶺南擔任郡守州牧之類的地方官員已歷三世。然而,多年的經營仍然無法幫助他們真正推行自己的主張,政令不行的局面直到馮保娶了冼夫人為妻之后才從根本上得以改變。這段對于冼夫人家庭出身的描述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冼夫人在兩廣之地的巨大影響力。
盡管在冼夫人生活的年代中國已然看到了由亂世走向統一的曙光,然而,當時中原政權對于嶺南仍然缺乏實質性控制。因此,史官突出冼夫人在嶺南之地的影響力,實際是為了下文描述冼夫人維護國家統一的多次平叛之舉做鋪墊。倘若在嶺南有著巨大影響力的冼夫人真的試圖像南越王趙佗那樣與朝廷分庭抗禮,中原統治者的確將面臨巨大的危機。然而,冼夫人先后平定了南朝梁時高州刺史李遷仕、南朝陳時廣州刺史歐陽紇和隋朝時番禺人王仲宣的叛亂,用自己的大智大勇維護了國家的統一。“石龍太夫人”“譙國夫人”“誠敬夫人”等封賜足以表明冼夫人已然贏得了中原統治者的認可。
問題是,海南冼夫人文化的形成是否源自皇帝的一次次冊封?換言之,代表著國家形象的皇帝對冼夫人的態度是否也令海南先民認可了這位南越巾幗英雄?事實上,這種推測顛倒了因果關系。自秦漢時期中原政治力量介入海南的發展開始,地方官員對于奇珍異寶的貪婪追求時時激起海南先民的起義。向千里之遙又蟲瘴叢生的海南派遣大軍往往被視為得不償失之舉,漢元帝最終采納了賈捐之廢棄海南郡縣的建議便是有力證據。因此,海南郡縣的廢立不斷以及中原政權對于海南實質控制力的下降成為了此后五百余年海南政治生活的常態。在這種情況下,海南先民連皇帝對冼夫人的封賜都未見得能夠及時了解,又怎會因此而認同冼夫人呢?
問題的答案在于那個時代海南民眾對于冼夫人的態度。首先,《隋書·譙國夫人傳》在陳述冼夫人的歷史功績之前,首先提到了“越人之俗,好相攻擊”[5],而且突出強調了冼夫人之兄南梁州刺史冼挺便時常恃強凌弱,攪擾地方不安。此種情形不僅令中原政權難以應對,就連嶺南民眾也備受其苦。若非這種情況在包括海南在內的嶺南之地頗為普遍,當冼夫人規諫其兄平復民眾怨憤之時,一海之隔的海南先民又怎會有“千余峒”歸附?魏征等史官在反復推敲之下仍然將冼夫人規諫冼挺進而海南島千余峒歸附的事情放置在多番平叛之前,充分表明海南先民對冼夫人的認可已然引起了史官充分的重視。
其次,除卻生活在海南多年的少數民族外,海南先民大多為中原遷居避亂而來的移民。遠離故土背井離鄉在蟲瘴之側求生,他們最看重的不外乎有個安穩的生活。然而,就這個再平凡不過的要求也在混戰與政治動蕩中變得遙不可及。冼夫人數次平叛與并建議在海南設立崖州,不僅為海南的發展創造了安定、和平的政治空間,而且向海南傳播了先進的生產生活技術、醫療知識等先進文化,幫助海南農戶將珍珠、沉香等海南特產售賣于往來于海南與大陸的商賈,促進了海南經濟社會的發展。若不是冼夫人深得海南民眾的認可,梁武帝蕭衍又怎會如此放心地將海南交與馮冼夫婦掌管?
再次,冼夫人晚年之時,番州總管趙訥貪贓枉法,俚僚等少數民族難以忍受他的貪婪暴虐,多有逃亡叛離之舉。冼夫人不顧年邁之軀,深入調查趙訥的罪證,不但督促長史張融向朝廷奏報趙訥的不法行徑,而且當親持朝廷敕書安撫各方逃亡叛亂之人,使得十余州的少數民族百姓都可以回歸故里,安居樂業。這件事依然證明了冼夫人在當地民眾心中所具有的地位與影響。
盡管諸位史官更加看重冼夫人在維護國家統一的方面的貢獻,但同時我們也可以理解海南先民認可冼夫人的原因。換言之,史官們借助了代表著“國家視野”的正史訴說了他們眼中的冼夫人,只不過這種訴說不是引導民眾關注冼夫人,而是順應民意的結果。其實,對于經歷了數百年動蕩亦或是逃難海島的海南先民而言,無論是宋齊梁陳,還是隋唐五代,他們最關心的并不是冼夫人究竟代表哪個皇帝,而是她為當地帶來了難得的和平與發展。冼夫人去世不久,除了馮冼兩個家族的后人對于先人的紀念之外,陸陸續續修建的冼夫人廟宇則表達了海南普通民眾對于冼夫人的緬懷之情。
其實,在那個中原動蕩之時,諸位史官對于冼夫人平叛歷史功績的充分肯定從一個側面表明經歷了兩漢、魏晉時期的摸索,中原政權統治者終于意識到僅靠派員前往的統治策略無法真正實現對嶺南的掌控,借助當地少數民族領袖的力量實現“土官”統治才能真正將“國家”力量滲透到嶺南[6]。而民眾對于冼夫人的認可正好符合中原統治者治理理念的轉變。民之所愿,國之所系。封賜冼夫人不但可以避免馮冼家族行僭越之舉,而且可以順應嶺南少數民族的人心,一舉兩得之事自然成為中原統治者不必猶豫的選擇。此時的冼夫人,已然不僅僅是正史之中記載的歷史人物,而是承載了“國家”與“民間”雙重期待的英雄人物。得民心者得天下,對冼夫人的封賜充分體現了國家對民意的看重。隋唐時期,海南的冼夫人文化正是在民心所向的基礎上逐漸發展起來。
二、精英推崇與宗教發展:走向神壇的冼夫人
盡管在陳亡隋興之際,嶺南民眾便已經尊冼夫人為“圣母”,但當時的冼夫人仍然是一個英雄人物的形象存于海南先民心中。然而,在冼夫人辭世后的數百年間,冼夫人形象逐漸完成了從英雄人物向神祗的轉變。
隋唐時期,海南島總體上保持了相對的穩定與發展。此時的海南先民對于冼夫人的功績感念于心,開始為她立廟祭拜。海南現存于儋州中和鎮的寧濟廟最早便修建于唐朝后期,當年蘇東坡被貶海南之際還曾未給該廟寫下“馮冼古烈婦,翁媼國于茲……”的詩句。廟宇的存在不僅表達了當時海南先民對冼夫人的懷念之情,而且也為冼夫人的神化預留了空間。根據《正德瓊臺志》記載,儋州寧濟廟修建于冼夫人辭世之后,修建的原因不僅在于當年歸附冼夫人的千余峒仍舊感恩于她,而且還在于她“于儋有移城之功”[7]55。“移城之功”的故事在坊間流傳的梗概大致如下:
相傳,冼夫人想把州治從舊州坡遷到山清水秀的高坡(即今中和鎮),遭到當地黎人頭領的反對。冼夫人想出了一條妙計,選了一個有大風的日子起大梁。適時,一陣狂風將橫梁上的紅布卷起,一直飄落到高坡。冼夫人趁機說遷城高坡是上天的旨意,才得以順利遷城至高坡[8]25。
這段流傳于民間的故事蘊含了冼夫人“上通天意”的意味。在那個科學尚不發達的年代,認為“上通天意”的冼夫人與海南島的穩定發展之間存有密切聯系的觀念自然極易深入人心,以至于在此后但凡有黎人歸附朝廷,有司也往往在這座紀念冼夫人的廟宇之中與黎人歃血約誓。無論官方還是民間對于冼夫人的信服使得這位已然辭世的巾幗英雄身上逐漸增加了不少神化的光環。
在此后大約兩個世紀的歷史中,史料對于海南冼夫人文化的發展缺乏足夠的描述。前文提到,蘇東坡貶謫海南之際曾為冼夫人廟賦詩一首,使得海南冼夫人文化再次進入歷史文獻的視野之內。詩中除了對冼夫人的功績給予充分肯定之外,還提到這座建于唐末的冼廟當時正處于“廟貌空復存,碑版漫無辭”的狀況。數百年時間似乎足以使得一座曾經香火隆盛的廟宇變得蕭條破敗,但時間的消磨并不是冼夫人廟破敗的唯一原因。根據正史之中的記載可知,自冼夫人逝世謚為“誠敬夫人”后直至北宋一朝,只有南漢政權時曾經追封冼夫人為“清福夫人”,可見在這個時期,中原政權對于冼夫人的重視程度難以與南朝隋唐時期相比。缺乏了朝廷的支持就意味著在廟宇的修繕等方面缺少了足夠的經費來源,盡管蘇東坡詩中也提到當時海南父老對于冼夫人的思念之情,然而,這也無法阻止冼夫人廟宇的衰敗。可以說,直到南宋建立前,海南冼夫人文化淡出了正史的視野,保有了民眾自發的樣態。
兩宋更替之際,中原戰亂頻仍,大批漢人南遷,海南相對穩定的環境與大片尚未開墾的土地為這些南來避亂的中原漢人提供了理想的避風港。加之貶官的到來為海南培養了大批文化政治精英,這使得海南冼夫人文化的復興既具備了難得的歷史機遇,又擁有了寶貴的智力支持。這些地方文化知識精英深知,只有將海南的穩定與冼夫人的庇佑聯系起來,才能使遠在千里之外的皇帝真正認可冼夫人,進而改變冼夫人淡出歷史記載的尷尬現實。例如,宋高宗紹興年間,在貴州擔任教授之職掌管地方學校事宜的羊郁就向宋高宗請旨對冼夫人進行封賜。宋高宗認為“彌寇攘之患”“格豐登之祥”“寬朕之憂”都是冼夫人神佑之功,因此,面對羊郁的上書他欣然應允,封冼夫人為“顯應夫人”,而儋州的紀念冼夫人的廟宇也更名為“寧濟廟”[7]551-552。從“顯應夫人”的封號,再到“惟神之功”的廟誥,冼夫人已然從一位馳騁疆場的巾幗英雄演化為有求必應的神靈。在地方政治文化精英的作用下,這一轉變不僅反映出海南冼夫人文化在經歷了幾個世紀的沉寂之后又一次走到了歷史的前臺,更邁出了冼夫人神化的重要一步。
及至明清時期,神化了的冼夫人與多位海南地方精英發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系。例如,曾在明朝萬歷年間屢立戰功的海南籍名將梁云龍不但因為冼夫人的保佑而科考得中,而且還經常夢到冼夫人指點他戰略戰術。經過神明指點的梁云龍運籌帷幄,不論是平定松山叛亂,還是遠征高麗、抗擊倭寇,都能夠得勝還朝。感念于冼夫人的保佑,梁云龍回鄉后便創建了梁沙村冼夫人廟[9]。現存于海口得勝沙的冼夫人廟源自清官軍抗擊海賊的戰役。道光年間,海盜張十五突襲海港,官軍猝不及防,彈藥器械喪失殆盡。參將黃開廣“緊嚴防范,并叩禱冼夫人英靈”。冼夫人不但親自騎白馬帶兵駕云而來,而且還招安了張十五,使得海事得以平息。海口民眾為了答謝冼夫人顯圣救助共同集資建立了得勝沙冼夫人廟[10]。不論是托夢梁云龍,還是顯圣平海盜,冼夫人都不是以前輩先人巾幗英雄的形象出現,而是以有求必應的神祗形象出現。這種文化符號經過梁云龍等地方文化政治精英的強化,成為了海南冼夫人文化難以磨滅的個性特征。
當然,皇帝與地方精英的推崇并不意味著冼夫人一定要以神化的姿態出現,海南道教的發展也對此產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唐宋時期,道教開始傳入海南。北宋時期宋徽宗(1100-1125)等皇帝對于道教的推崇,使得海南的道教經歷了飛速的發展。目前存于海口五公祠內的《神宵玉清萬壽宮詔》通碑正是宋徽宗在位年間所立,此碑佇立海南,從一個側面證明了皇帝對道教的篤信對海南道教發展的影響[8]242-243。此后,諸如白玉蟾等道人的推動下,海南道教深入海南民眾的日常生活。道教的介入使得冼夫人神化有了成熟的宗教載體,借助道教既有的話語體系,在道教民間化的進程中,關于冼夫人顯靈的各種故事流傳下來,冼夫人也被最終“打造”成為一位有求必應的道教神靈。
當然,盡管明清時期海南民眾將冼夫人作為神靈祭拜,但當時的海南民眾并不單一供奉冼夫人。當時,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宗教都在海南擁有各自的信徒。即便是道教內部,諸如關公、雷神、媽祖等神靈也深得海南民眾推崇。因此,此時的冼夫人文化并不是排他性的文化存在。
三、海南軍坡節與冼夫人文化的民俗化
如果說,在明朝之前海南島仍然被視為懲治政敵、發配貶官的蠻荒之地的話,明太祖朱元璋則將海南視為“習禮儀之教,有華夏之風”的南溟奇甸[11]。可以說,明清時期,國家對于海南態度的轉變使得海南的經濟社會發展擁有了更為切實的政治保障。墟市數量不斷增加,戲劇等文化藝術形式獲得長足發展,作齋等民俗活動興起,這些從各自側面反映出這一時期海南民間社會的發展。
民間社會的發展,孕育了軍坡節走上歷史舞臺的社會基礎。軍坡節原本是海南先民模仿冼夫人率兵出征的儀式而興起的民俗活動,是海南冼夫人文化的集中體現。軍坡節究竟形成于何時學界尚無明確的結論,唐胄在《正德瓊臺志》中曾經記載瓊山百姓在陳村廟進行“裝軍容”的祭拜儀式,“隨者千人計”的記載足見軍坡節的聲勢之大[7]540。由于此前的文獻未見關于軍坡節的相關記載,因此,軍坡節至遲形成于明代的推論當無爭議。
軍坡節的形成使得海南冼夫人文化有了最為集中的文化載體與呈現窗口。這個窗口既向我們展示了冼夫人由人到神的轉變過程,也為娛人娛神的巧妙共生預留了空間。盡管各地的軍坡節細節略有不同,但不少地方的軍坡囊括了裝軍、行公、上刀山、過火海、婆祖巡游、跳神舞和穿仗等環節。所謂“裝軍”,指的是民眾抬著祭祀的神像仿照冼夫人出征時的樣子而進行的民俗活動。盡管史料中缺乏對“裝軍”形成狀況的詳細介紹,但我們完全可以想象最初的“裝軍”活動大概始自民眾對冼夫人出征儀式的聲勢浩大與象征意義的記憶與理解。但此時的冼夫人仍然以保一方平安的巾幗英雄的形象出現。而上刀山、過火海、跳神舞、穿仗等民俗活動的呈現則顯然帶有濃郁的宗教色彩,最終希望表達的意義無外乎彰顯神力,使得民眾更加相信自己祭拜的神祗有能力保佑自己。此時的冼夫人便不再是保境安民的南越首領,而是一位富有神力的天上神明。
也許正是這種神力為海南廣大先民所看重,因此,每次軍坡節時往往都會“四方雜集,殊稱盛會”[12]。這種大規模的集會表面上看起來是為了祭祀冼夫人而舉辦,其實是集祭神、廟會與聚會于一體的大型民俗活動。活動的中心自然是從裝軍開始直至穿仗活動結束的祭神儀式,然而,在這些儀式開始之前,來往的商旅便在路旁支起攤子,開始了各自的買賣。這種狀況至今仍是如此。筆者在海南東部某縣調研時發現,軍坡節正式開始的大約三天時間,街旁的攤位便已經開始陸續營業,臨近村鎮的鄉人都到這里趕集。這份熱鬧尤其令那些孩童興奮,不論之前是否相熟,在這條暫時熱鬧的街道之上,在短短幾天的時間里,他們足以成為要好的朋友。一位地地道道的年逾八旬的老者告訴筆者,年輕的時候(民國時期)他們都會在軍坡的時候趕去看看,不光是看看抬公巡游,而且也順便買些特產回來。這都充分表明軍坡節所承載的遠不止祭神拜神的單一功能。
實際上,海南民眾所用的“鬧軍坡”的稱法形象地體現了軍坡節的情形。“鬧”,突出了在嚴肅的祭神活動中蘊含的熙熙攘攘與人頭攢動,更突出了民眾在參加軍坡節時的歡快與喜慶。這顯然與一般意義上的祭神有著巨大的不同,更像是中原地區的廟會在海南的再現。在轟轟烈烈的活動之中,娛神與娛人獲得了巧妙的共生。民眾的參與程度越高,期間獲得的喜悅感與歡快感越高,就越能說明神靈在凡間的擁躉越多,香火越旺,因此,神靈下凡保佑世人的可能性就越大。與此同時,即便是對那些不信鬼神的世人而言,單就持續幾天的、豐富多彩的商業及文化活動,就足以令人倍感欣喜。
從這個意義上講,其實有多少人仍舊信奉冼夫人的神力已經顯得并不那么重要了。每年的軍坡節已然成為了鄉人聚會、集市買賣、搭臺唱戲最為理想的平臺。這個承載著美好祝愿的民俗活動將宗教信仰、商業活動、天倫之樂、娛樂消遣巧妙地集合起來,儼然成為了海南獨特的民俗活動之一。而在這個過程中,冼夫人文化也從神靈崇拜走向了民眾的日常生活。
四、海南冼夫人文化的文化意蘊
海南冼夫人文化變遷所經歷的三個階段雖然各有特點,但其背后的共同之處頗為耐人尋味。這個變遷過程不僅彰顯了海南民眾持有的價值追求,而且也反映了在這種追求之上國家與地方之間的互動過程。
(一)實用理性:民本的敘說
前文已述,海南先民之所以接納南越世家豪酋冼夫人,并不是源自馮冼家族在嶺南的地位與影響力,而是因為她可以幫助海南先民真正擺脫貪官污吏的盤剝與戰亂動蕩的侵擾,過上期盼已久的安定生活。因此,“海南文化信仰的關鍵在于神能否保佑他們順利、平安、丁旺、救苦救難、恩澤子孫,是直接的功利主義。”[13]推崇冼夫人并不因為她代表哪個皇帝或者哪個宗教,而是看她對于民眾生活影響的實際效果。這正是在經歷了與惡劣的自然環境和動蕩的政治局面的長期斗爭之后,海南先民形成的實用理性的價值追求。
可以說,海南軍坡節充分體現了這種實用理性的價值追求。作為紀念冼夫人的民俗活動,軍坡節供奉的對象卻未必是冼夫人。在海南一些市縣,軍坡常常與公期、婆期混而為一。公期與婆期是海南北部地區祭祀境主的民俗活動,所謂境主指的就是這片區域的地域神。要想在這片土地安居樂業,祭拜境主是海南先民認為必不可少的祭祀活動。令人奇怪的是,一些地方在不知道“大公”和“婆祖”的來歷及其與冼夫人聯系的情形下,仍然堅持舉辦軍坡節的民俗活動。這些地方的民俗活動之所以沿用了“軍坡”一名,是因為供奉的對象主要是冼夫人手下將領或者歸降冼夫人的黎族或俚人首領。這些被供奉的將領或首領原本大都負責一方領地的治理,他們雖然不是這片領地的血緣祖先,但卻對此地的經濟社會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海南先民希望這些將領能夠像冼夫人一樣給本地帶來安定的生活,因此將他們視為這片地域的神祗加以供奉,并選擇了與紀念冼夫人同樣的“軍坡”一詞。
如果說,最初海南先民祭拜這些保一方平安的將領是源自對于他們功績的感念,那么在“記不清”祭拜對象之后仍然保有這種民俗活動則是實用理性作用下的文化慣性使然。只要能夠保佑子孫后代,何必執著于祭臺之上的神靈究竟是誰呢?在數百年的演進過程中,軍坡節祭拜的對象是誰似乎已經變得不那么重要,更為重要的是全村可以藉此一聚,表達對于未來、對于子孫的期望,交流彼此的感情。更何況,海南先民從來未曾因為信奉了冼夫人而拒斥其他可能保佑自己的神靈。在這場轟轟烈烈的活動中,搭建起來的戲臺、路旁擺放的攤位、成群嬉戲的孩童與那個高懸臺上的供奉對象之間存在著巧妙的聯系。與其說大家相聚一起是為了紀念冼夫人或者保境將領,倒不如說是那些祭拜的神祗為民眾的相聚搭建了一個聚村而歡的平臺。因此,臺上是誰、臺上究竟有幾位神仙似乎都不是那么重要了。不信“一”,并不表示海南先民沒有信仰。恰恰相反,它正反映了海南民眾所持有的實用理性導向的民本觀念。
(二)國家化與海南化:雙向的互動
如前所述,“民間視角”不僅關注民間視野中的歷史變遷,也關注國家與民間“如何共同構建一個地方社會,如何共享一種文化”[4]27。而實用理性價值取向的存在,使得海南冼夫人文化不僅表現出民眾視野中的精神追求究竟指向何方,而且為我們理解海南如何成為中華版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提供了寶貴的窗口。
秦漢時期,中原政權在海南島設置郡縣往往被視為海南正式進入中華版圖的開始。然而,最初的政治力量介入的結果恐怕連中原統治者都始料未及。郡縣的設立并沒有讓海南先民深切體會到王權到來的榮耀,反而為那些貪官惡吏欺凌盤剝百姓創造了機會。在山高皇帝遠的海南島上,代表國家力量的派駐官員未能給邊疆百姓樹立良好的國家形象,其結果自然會使得國家與邊疆民眾陷入緊張與對立之中。由此也不難理解冼夫人能夠贏得海南民眾認可的現實原因。更為重要的是,隨著中原政權對于嶺南重視程度的不斷提高,包括海南在內的嶺南之地不再是可有可無的蠻荒之地。尤其是在各個中原政權面對著來自北方的軍事壓力的情形下,嶺南之地成為了他們逐鹿中原的一塊心病。因此,如何能夠合理解決嶺南問題成為了中原政權必須面對的困境。在這種情形下,海南民眾認可的冼夫人與馮冼家族進入了中原統治者的視線。而冼夫人也成為了“國家視野”中的一個典型符號。此后的數百年,皇帝對于冼夫人的不斷封賜,更是彰顯了“國家”對于嶺南的重視。因此,毋庸置疑,海南冼夫人文化是國家力量介入的產物。
當然,海南民眾對于國家推崇的冼夫人進行了海南化的“加工”。一方面,在實用理性的指引下,冼夫人連同她所率領的將領都被一步步塑造成了有求必應的神明。與此同時,海南民眾并未拒斥其他任何一個可能給自己的生活帶來福祉的各方神明。因此,海南冼夫人崇拜只不過是眾多神明崇拜的冰山一角。此時的冼夫人所具有的文化符號的意義已然遠遠超出維護國家統一、促進民族團結的國家視角下的政治意義,帶有了更多海南民眾對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與期盼,帶有了更多國家與民間互動的痕跡。
海南冼夫人文化的發展用最為生動的事例向世人展示了王權不僅僅代表著自上而下的統治力量,也展示了這種力量背后必須依賴的民意基礎。冼夫人維護國家統一的形象必須建立在民眾安居樂業的基礎上才不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因此,透過海南冼夫人文化的發展,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國家與邊疆在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雙向互動過程中共同構筑了一個中華版圖之內的海南,彰顯了一個不斷關涉民意的國家。
注釋:
①關于冼夫人的生卒年代目前學界仍然存有爭議,例如海南籍著名歷史學家、民族學家王興瑞曾在《冼夫人與馮氏家族》一書中指出冼夫人生于梁武帝天監十一年,卒于隋文帝仁壽二年,享壽九十一歲,而《大清一統志》等史料中則提出冼夫人“年八十卒”的觀點,前后相差竟有十歲。此外,還有許多學者也提出了自己對于冼夫人生卒年代的考證。盡管不同學者提出的觀點各異,但認為冼夫人生活于梁武帝天監至隋文帝仁壽年間的觀點得到了大多數學者的認同。
[1]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M].林同奇,譯.北京:中華書局,1989:142-143.
[2]張國剛.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2卷[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493-499.
[3]楊念群,等.新史學:多學科對話的圖景[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678-688.
[4] 趙世瑜.小歷史與大歷史:區域社會史的理念、方法與實踐[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5]魏征.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3:1801.
[6]吳永章.黎族史[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24-25.
[7]唐胄.正德瓊臺志[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
[8]張朔人.明代海南文化研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257.
[9]梁生榆,等.冼廟史話[C]//梁定和.心曲共鳴:新坡冼夫人紀念館建館二十周年紀念文集.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10:20-22.
[10]李文恒.咸豐瓊山縣志[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245;464.
[11]符策超.海南文化史[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8:89.
[12]馬日炳.康熙文昌縣志[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46.
[13]閆廣林.海南島文化根性研究 [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