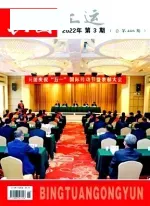都是一個情字
□傅強
1966年初夏,父親響應兵團黨委的號召,從北疆重鎮石河子前往農一師,自愿報名支援農業第一線。
六十年代的道路坑洼不平,原單位給我們安排了一輛車廂上撐起篷布的老解放大卡車,母親帶著3 歲多的弟弟坐在駕駛室,其他人都坐在嘎吱嘎吱一路搖晃的大篷車里,雖然路途遙遠、車輛顛簸,大篷車里也是悶熱難耐,但我們幾個孩子伴著嘎吱嘎吱的節奏一路歡笑著,如同坐在搖籃里,整整一周的路途都感到無比的歡快。
一路上,父親和我們幾個孩子在大篷車里說著、笑著。困了,倚著車廂睡一會;累了,伸個懶腰或站起來搖搖晃晃地活動一下。進入南疆,一路上都是成熟的桑葚。司機是個非常和藹可親的中年男子,每每遇到高大、成熟的桑子樹,就會把車停在樹下,輕快地爬到車廂板上用力地為我們搖樹枝。一陣“桑子雨”,熟透的大桑子伴著我們的呼喊聲落滿車篷,從天而降的美味讓我們忘記了旅途的艱辛,也成了我們扎根南疆的第一件難忘記憶。
父親是個執著的人,認準的事情就要堅持。抵達阿克蘇,農一師黨委要把父親安排在師里工作,父親婉言謝絕。父親更希望到農業一線中的一線,于是我們一家來到了距阿克蘇100 多公里之外的勝利十四場(后改名叫農一師九團)。隨后,父親又經過一個多月的“軟磨硬纏”,再次謝絕場黨委的好意,堅持從場部搬到護林隊安了家。
我們的新家,是一間寬敞的“地窩子”,“房頂”中間留一個臉盆大的洞,鋪一塊塑料紙,周圍用泥巴糊住作為窗戶。要進“地窩子”,首先要經過一個約一米寬兩米長的下坡,才能來到門跟前。所謂“門”,就是由一塊厚板子做門邊,和幾塊木板釘在一起,厚板子的兩頭要各長出其它木板8-10 公分,做成“門軸”,鑲在上下兩個木頭做的窩窩里面,門就可以旋轉了。白天從外面進去,就算不關門,里面也是十分昏暗,若是突然關上門,眼睛睜得再大也絲毫不起作用,足足等上七八分鐘,才能分清東西南北。
父親說,咱們的新家可是冬暖夏涼,以后這里就是我們的“避暑山莊”了。我們幾個孩子從沒見過這樣的房子,一會兒鉆到暗處藏起來,一會兒又跑到“房頂”蹦蹦跳跳,家里瞬間落滿厚厚的塵土。“避暑山莊”后面有一條大干渠,寬大的干渠和清澈的渠水十分壯觀。下班后,父親會帶著我們到干渠洗澡、游泳,洗去一天的汗漬和疲憊。
時至今日,干渠邊的熱鬧情景依然歷歷在目。水性好的大人和孩子們,在水里做著各種優美的泳姿和造型:有人踩著水,半截身子都露在水面上,顯示著高超的技藝;有人躺在水面上一動不動,享受著漂浮的樂趣;有人潛泳,好半天不露出水面,讓站在岸上的人都捏了一把冷汗,直到浮上來,眾人才松了一口氣。一些大一點的男孩,他們的水性極好,一個“猛子”可以潛到對岸。
天氣一轉涼,釣魚的人就多了起來。那時的渠里,魚可真叫多,有塔里木河特有的大頭魚和黃魚,有鯉魚、草魚、鯽魚,還有一種肉頭魚,就是現在人們常說的“狗頭魚”。大人們釣大魚、下排鉤,父親帶著我們找一根直一點的樹枝,用家里的縫衣線,綁一根彎好的大頭針,纏一點牙膏皮(當時的牙膏皮都是錫做的),再拿一點面泥,做好了釣魚的“裝備”。 碰到大魚,小孩子無論如何也是拉不上來的,有時候甚至把“魚竿”都拉到水里去了。兒時的餐桌上,美味的肉頭魚和鯽魚大大改善了我們的生活,成為了我們至今都無法品嘗到的回憶。
時光帶走了童年,卻留下了內心深處的暖。那些童年不忘的記憶,帶給我們的歡樂,遠遠勝過當今孩子們上網、打游戲和看電視。愛上塔里木——我可愛的家鄉,都是心中的那個情字,也正是這種情,讓遠離家鄉的人們無論身處何方,無論經歷了什么都再無牽掛,都會扎根新家努力奔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