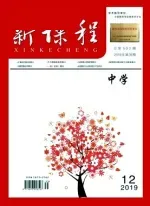如此散文成就如此《背影》——淺析《背影》體裁之必須
唐 娟
(廣東省深圳市南山區大學城麗湖實驗學校)
朱自清先生創作于1925 年的《背影》一文,廣為傳誦,實屬經典。作者當時為什么選擇用敘事性散文這種體裁,而不是小說或者其他,筆者認為這其中有兩個必然因素。
內容“情”定散文,組建完美“婚姻”
首先,《背影》一文所寫事件發生在1921 年,文中所寫的“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親的差使也交卸了”雖寥寥幾字,但背后卻隱藏著風起云涌的故事,其中關鍵的兩點,一是作者的父親因妾室失衡負債失去工作,二是作者與父親已經處于嚴重失和狀態。但作者以這個材料寫就《背影》一文卻是4 年以后,是什么促成了他寫的?
朱自清曾在《文藝知識》連叢(第一集之三)中談到寫作本文緣由,“就因為文中所引的父親的來信里的那句話。當時讀了父親的信,真的淚如泉涌。我父親待我的許多好處,特別是《背影》里所敘的那一回,想起來跟在眼前一般無二。我這篇文只是寫實,似乎說不到意境上去……”因此,出于內容寫實的需要,小說是不適宜的,敘事性散文自然地成了第一選擇。
另外,我們知道,朱自清的父親是典型的封建專制式的家長,父子關系決裂也歸因于此。因此,在朱自清以前的理解中,能表現父子情深的事件或場景不多。但是,這個時期的朱自清已經為人父,并在追逐理想的過程中深悟生存之艱難,也漸漸對父親有了諒解和感念。
“他少年出外謀生,獨立支持,做了許多大事”“總覺得父親與搬行李的腳夫講價時說話不漂亮。”“他又是叮嚀又是囑咐茶房”“那時真太聰明了”,這樣的句子里,有對父親能力的深佩,更有朱自清自己的深愧、自責與自省。而且,那時的朱自清非常希望父子關系能夠緩和走向正常。因此,選擇一件事作為載體,來訴說內心的諸多感慨,成為必然,選擇敘事性散文也就水到渠成。
所以可以這樣說,《背影》之所以厚重,之所以感人至深,離不開獨特背景的支撐,而這一背景也促使作者在寫作本文時,對父親的形象進行了細致的刻畫,通過敘事性散文的形式藝術地展現出來。因此也可以認為,作者所選的內容決定了《背影》的體裁必然是散文,兩者的“聯姻”堪稱完美。
表達垂青散文,彰顯先驅魄力
《背影》選擇了散文,也是作者表達、抒情的需要。這里,我們特別要了解朱自清對現代散文的突出貢獻。
以《歌聲》涉筆散文領域的朱自清,從1923 年后轉向散文創作,以后就一直沒有間斷過。他在《背影·序》中說:“我寫過詩,寫過小說,寫過散文。二十五歲以前,喜歡寫詩;近幾年詩情枯竭、擱筆已久……我覺得小說非常地難寫,不用說長篇,就是短篇,那種經濟的嚴密的結構,我一輩子也學不來!我不知道怎樣處置我的材料,使它們各得其所。至于戲劇,我更是始終不敢染指。我所寫的大抵還是散文多。既不能運用純文學的那些規律,又不免有話要說,便只好隨便一點說著;憑你說‘懶惰’也罷,‘欲速’也罷,我是自然而然地采用了這種體制。”
回到《背影》的寫作時間1925 年,這一年,對所有中國人而言,是極不太平的一年:社會上的政治風暴頻繁,爆發五卅慘案;于朱自清個人而言,家累繁重,五年后重返北京清華,可謂輾轉辛苦。他的心一直受磨受難,感到在大時代里,自己是“一張枯葉,一張爛紙”,是“尋常人所難堪”的“苦在話外”。心理失衡,促使他較多關注父子、夫妻、師生和朋友間的感情,檢點自己在人倫關系中的細節,因此文學創作上從即景抒情走上“憶之路”——對往事的回憶。《背影》即這年10 月收到父親的信后,有感抒懷。
此外,朱自清在散文方面提出了“意在表現自己”的命題,這和歷來賦予知識分子“文以載道”的使命大相徑庭。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朱自清寫《背影》《荷塘月色》《燈光槳影里的秦淮河》等散文,顯示了“舊文學之自以為特長者,白話文也并非做不到”,盡了“對于舊文學的示威的歷史任務”(魯迅《南腔北調集·小品文的危機》),是在承擔著實踐并推廣“表現自己”的寫作初衷,及推進白話文寫作的偉大使命。
另據朱自清的學生黎見明對1941 年在西南聯大上學的回憶:“課余之暇,隨行散步,我們向他(朱自清)請教,談到陶淵明詩,也談到《背影》。他回答很簡單,就是‘我在《背影》里寫出了可貴的性格’(《可貴的〈背影〉》)這“可貴的性格”,當是“意在表現自己”的命題得以踐行,當是朱自清散文以獨特的風格自成一派,樹立了“白話美文的模范”。由此可見,《背影》必須是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