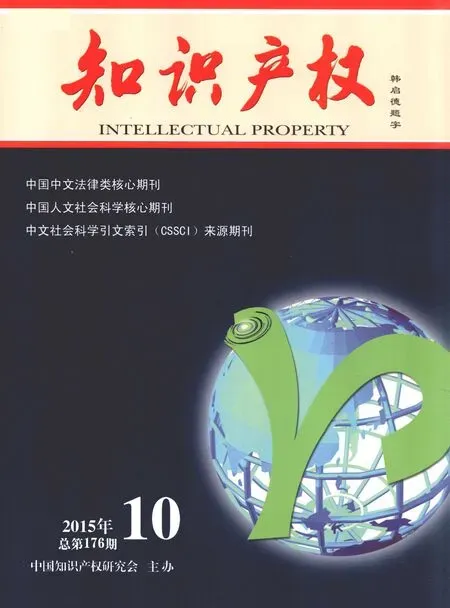臺灣地區“智慧財產法院”訴訟制度考察與借鑒
朱 理
臺灣地區“智慧財產法院”訴訟制度考察與借鑒
朱理
內容提要:我國臺灣地區在設立“智慧財產法院”的同時,為智慧財產案件審理制定了特別訴訟制度。這些特別訴訟制度對于“智慧財產法院”的成功運作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臺灣“智慧財產法院”的訴訟制度特色及其經驗與教訓,對于完善大陸知識產權法院訴訟制度頗具啟發性。
“智慧財產法院” 訴訟制度 啟示
我國臺灣地區“智慧財產①臺灣地區使用的“智慧財產”與大陸使用的“知識產權”一詞是同義語。考慮到表達習慣,在涉及臺灣地區的法院名稱和法律名稱等專有名詞時,本文將使用“智慧財產”一詞,在涉及大陸法院及其訴訟制度時,將使用“知識產權”一詞,特予說明。法院”成立于2008年7月1日。在設立過程中,臺灣地區立法機關還根據智慧財產案件的特點,同時制定了專門的“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確立了智慧財產案件特別訴訟制度。 深入研究和考察臺灣地區“智慧財產法院”的訴訟制度特色及其運行效果,對于完善大陸知識產權法院訴訟制度頗具啟發性。長期以來,大陸對臺灣地區“智慧財產法院”的組織設立關注較多,對其獨具特色的訴訟制度及其實踐效果了解甚少。本文旨在通過可得的實證證據考察臺灣地區“智慧財產法院”特色訴訟制度的運行效果,總結其經驗與教訓,進而為完善大陸知識產權法院訴訟制度提出建議。
一、臺灣地區“智慧財產法院”的訴訟制度特色
(一)案件管轄與審理制度
臺灣地區“智慧財產法院”是國際范圍內第一個實行知識產權民事、行政和刑事審判“三合一”的專門法院。該院管轄智慧財產權第一、二審民事案件、第一審行政案件以及第二審刑事案件。與上述民事訴訟事件和行政訴訟事件有關的保全證據及保全程序事件,亦屬“智慧財產法院”的受案范圍。②參見“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2條和第4條。“智慧財產法院”審理智慧財產民事案件時,一審民事案件由一位法官獨任審判,二審民事案件由三位法官組成合議庭審理。由于全臺僅設置一個“智慧財產法院”,若牽涉到搜索、扣押、人犯解送等問題,必須確保即時性、就地性與方便性,故第一審刑事案件仍由各地法院刑事庭審理,第二審才統一由“智慧財產法院”合議庭審理。③參見“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第3條第2項。
根據臺灣理論和實務界的通說,臺灣地區“智慧財產法院”對知識產權民事、行政案件是優先管轄而不是專屬管轄,只有刑事上訴案件是專屬管轄。所謂優先管轄,是指智慧財產民事、行政案件原則上由“智慧財產法院”審理,但是,如果普通法院對是否為智慧財產案件的認定有誤而進行審理,其判決亦屬有效,④參見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9條。并不會因法院無管轄權而發生裁判無效的情形。規定優先管轄而不是專屬管轄的原因在于,如果將“智慧財產法院”的管轄界定為專屬管轄,則容易發生因管轄錯誤發生裁判違法的爭議。當智慧財產案件的邊界不清晰時,當事人和法院均可能在案件管轄問題上耗費精力。依照臺灣地區“民事訴訟法”的規定,違反專屬管轄構成裁判違法,上級法院應撤銷原判決。界定為優先管轄,則可以避免此種過于強烈的法律后果。
(二)技術審查官的設置
“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第15條規定,“智慧財產法院”設技術審查官室,置技術審查官,從而確立了技術審查官制度。根據該條第4項的規定,技術審查官的職責為:承法官之命,辦理案件之技術判斷,技術資料之收集、分析及提供技術意見,并依法參與訴訟程序。“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4條進一步將技術審查官的職責明確為以下五項:一是為使訴訟關系明確,就事實上及法律上之事項,基于專業知識對當事人說明或發問;二是對證人或鑒定人直接發問;三是就該案向法官為意見之陳述;四是于證據保全時協助調查證據;五是于保全程序或強制執行程序提供協助。①其中 第5項職責為2014年6月4日修正時新增。
技術審查官僅系輔助法官為技術判斷、技術數據之搜集分析,其提供技術意見在性質上屬咨詢意見,并非證據方法。審理案件時,法官應斟酌當事人辯論和全部證據綜合評判,并不受技術審查官所提供意見的拘束。若法官因技術審查官提供而獲得特殊專業知識,根據“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8條的規定,應該給予當事人以辯論的機會,始得采為裁判的基礎。如果審判長或受命法官沒有踐行向當事人說明爭點、適時表明其法律上的見解及適度開示心證的程序,則屬重大程序瑕疵,構成撤銷判決的事由。②參見 臺灣地區“最高法院”100年度臺上字第1013號民事判決。
臺灣地區“智慧財產法院”的技術審查官來源有三種:正式編制、借調和約聘。選聘人員主要來自非公職人員,而借調人員主要來自專利審查員等公職人員,一般皆為短期。技術審查官的任期和工作的非固定性,可能是影響案件審查質量的潛在因素。
(三)民事案件中審查智慧財產權的有效性
臺灣地區“智慧財產法院”成立之時,摒棄了德國式的民事侵權與行政無效二元分立體制,實行“智慧財產法院”在民事訴訟中自行審查智慧財產有效性的制度。根據“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6條的規定,如果當事人主張或者抗辯智慧財產權有應撤銷、廢止的原因,法院應就其主張或抗辯有無理由自為判斷,不適用其他法律關于停止訴訟程序的規定。如果法院認定某項智慧財產權有撤銷、廢止的原因,智慧財產權人在該民事訴訟中不得對他主張權利。因此,在專利侵權民事訴訟中,如果被告提出權利有效性的抗辯,法院應就此抗辯加以認定,而不能逕行不予采納或者中止審理。③參見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28條。這是臺灣地區智慧財產訴訟制度的最大突破。在這一制度下,“智慧財產法院”對智慧財產權效力的認定,僅在受理個案中有效,并不具有對世效力。在其他案件中,權利人仍可對于他人主張權利。這一制度使得智慧財產權有效性的認定重心向民事案件審理法院偏移,當事人在行政舉發程序中,亦可援引民事法院的效力認定。但是這一程序并非取代行政程序,智慧財產權效力的最終認定,仍然必須經過行政程序才能確定。在民事訴訟中,為使法院對智慧財產權有效性作出判斷時對該權利有更多了解,輔助法院作出更加準確的結論,“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7條還確立了法院在必要時可以裁定智慧財產專責機關(即“智慧財產局”)參加訴訟的制度。
(四)營業秘密保持命令④臺灣 地區使用的“營業秘密”與大陸使用的“商業秘密”為同義語。
為強化營業秘密保護措施,使當事人不必擔心在訴訟中過程中二次泄密,兼顧當事人訴訟權與商業秘密持有人利益,“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引進了日本法上的秘密保持命令制度。受商業秘密保持命令約束的人,只能在訴訟中閱覽商業秘密資料,不得用于訴訟外目的;如果在訴訟外使用,將負刑事責任。為確保秘密保持命令之威懾力,“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賦予營業秘密保持命令以嚴格的法律效力。違反秘密保持命令,將營業秘密披露給第三人使用的,根據“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5條的規定,應負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單獨或并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五)證據提出義務和具體答辯義務
臺灣地區“民事訴訟法”規定了文書提供命令制度,在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從提出文書之命”或“因妨礙他使用,故意將證據滅失、隱匿或致礙難使用”的情況下,法院“得審酌情形認他造關于該文書之主張或依該文書應證之事實為真實”。①參見 臺灣地區“民事訴訟法”第282條之一、第345條、367條等。這是一種通過間接強制的方式迫使當事人主動配合提出證據的制度。在智慧財產民事訴訟中,證明侵權事實、損害事實及損害范圍的證據往往僅存在于當事人一方,如果當事人不向法院提供證據,法院就無法獲得完整事實并作出精確判斷。為此,“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在“民事訴訟法”的基礎上作了補充規定,對于文書或者勘驗物的持有人,無正當理由不服從法院命令提出文書或者勘驗物的,法院可以處以罰款,且必要時可以裁定為強制處分。②“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0條第1項、第2項。j可見,“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在通過罰款加重間接強制效果的同時,也酌定采取強制處分的直接強制方法促使當事人履行提出證據的義務。
為回應各界對于證據保全程序效果不明顯的批評,強化證據保全的效力,同時平衡雙方當事人的利益,“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對證據保全作了補充規定。一是強化證據保全的直接強制力。相對人無正當理由拒絕證據保全之實施時,法院得以強制力排除之,但不得逾必要之程度。③“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8條第4項。二是技術審查官參與證據保全。法院實施證據保全時,可以命令技術審查官協助調查取證,以提高法官對于保全證據的鑒別、判斷能力,避免法官因欠缺相關專業知識而被當事人誤導。三是提高證據保全的程序保障。為兼顧相對人或者第三人利益,防止侵害他人營業秘密,法院在證據保全有妨害相對人或第三人營業秘密之虞時,可以根據當事人請求,限制或者禁止實施保全時在場之人,并就保全所得的證據資料命另為保管及不予準許或限制閱覽,同時可以準用秘密保持命令,對在場受證據開示的申請人或其代理人,發秘密保持命令。
在營業秘密侵權案件中,權利人收集證據更為困難。為解決此問題,加強營業秘密保護,提高臺灣地區產業競爭力,2014年6月4日修正的”智慧財產審理法”補充規定了營業秘密案件中被控侵害人否認侵害主張時的具體答辯義務,“以促使當事人協助法院為適正之裁判,同時兼顧當事人在訴訟程序之保障”。④參見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增訂第10條之一規定:“營業秘密侵害之事件,如當事人就其主張營業秘密受侵害或有受侵害之虞之事實已釋明者,他造否認其主張時,法院應定期命他造就其否認之理由為具體答辯。前項他造無正當理由,逾期未答辯或答辯非具體者,法院得審酌情形認當事人已釋明之內容為真實。前項情形,于裁判前應令當事人有辯論之機會。”具體答辯義務的規定,降低了營業秘密權利人的侵權證明標準,客觀上減輕了其證明負擔。
(六)行政訴訟中新證據的審酌義務
“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施行前,臺灣地區在傳統上將撤銷、廢止商標或者撤銷專利權行政訴訟與一般行政訴訟等而視之。法院判斷關于撤銷、廢止商標權或專利權的行政決定是否違法時,均以被訴行政決定作成時的法律及實時狀態為基準。與此相適應,法院在行政訴訟中原則上不采納當事人未在行政程序中提交的新證據。此時,當事人可以新證據或者新事實為由,再次啟動行政處理程序。考慮到訴訟經濟、一次性解決糾紛和維護正當權利的需要,“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一改常規,增加了在行政訴訟程序中法院可接納新證據的規定。其第33條規定:“關于撤銷、廢止商標注冊或撤銷專利權之行政訴訟中,當事人于言詞辯論終結前,就同一撤銷或廢止理由提出之新證據,“智慧財產法院”仍應審酌之。智慧財產專責機關就前項新證據應提出答辯書狀,表明他造關于該證據之主張有無理由。”所謂“同一撤銷或廢止理由”,是指同一異議、評定、舉發或廢止申請的應撤銷或廢止商標權或專利權事由范圍內,“智慧財產法院”就當事人所提出的證據加以審酌而言。例如專利舉發案均屬主張不具創造性的同一專利權撤銷事由。①參見司法院編:《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新制問答雜編》,2008年6月,第39頁。
為防止當事人濫用此制度,將該制度演變為惡意阻滯訴訟的手段,“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對該制度的適用進行了限制。根據其第40條第1款的規定,如果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或因重大過失,未依訴訟進行程度,在言詞辯論終結前的適當時期提出新證據,因而有礙訴訟終結情形的,法院可以依法予以駁回。
二、臺灣地區“智慧財產法院”訴訟制度運行效果考察
臺灣地區“智慧財產法院”運行已經七年,為我們評估其各項制度的成敗提供了一個極好的觀察樣本。本部分旨在利用可得的實證材料,考察“智慧財產法院”各項訴訟制度的運行效果,并對其經驗和教訓進行總結。
(一)案件管轄與審理制度效果考察
臺灣地區“智慧財產法院”實行智慧財產民事、刑事和行政審判“三合一”,旨在集中審理和裁判智慧財產案件,最大程度實現審判組織專門化改革的目標和制度價值。法官可通過同一類型案件的審理快速累積經驗,提升審理能力;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不同類型案件的裁判結果沖突,提高判決的協調性和一致性;盡可能保證同類型案件達成審理思路共識,提高案件法律適用及其結果的可預期性,進而提高當事人對裁判結果的認同度。從表1、表2有關統計數據來看,“智慧財產法院”在案件審理效率和質量方面均有不俗表現。②除非 特別說明,本文有關臺灣“智慧財產法院”的統計數據均來源于該院。

表1 “智慧財產法院”法官月結案件及上訴抗告維持率

表2 “智慧財產法院”各類案件折服率
根據上述數據,有評論認為,臺灣地區“智慧財產法院”的裁決“折服率高(即上訴率低)、維持率高(即廢棄、撤銷率低)”,是“專業法院成功之象征”。③熊誦 梅:《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臺灣智慧財產訴訟新制之檢討與展望》,載《月旦民商法雜志》總第38期,2012年12月。但是,智慧財產案件的集中管轄和審理,也帶來另一方面問題。第一,一個“智慧財產法院”集中審理全部智慧財產案件,缺乏競爭;法官固定處理專業案件,視野受限,對于某些問題可能過早形成定見,意見過于集中,較難接受新的觀點或者從其他視角思考問題。第二,智慧財產一審民事案件基本集中于一個法院管轄,管轄區域過大,增加了當事人訴訟成本,造成當事人訴訟不便利。如果結合原告勝訴率方面考察,或許可以促使我們對前述折服率和上訴抗告維持率的解讀保持一點警惕。自2008年7月至2012年6月,該院審理的案件中,民事一審案件原告的平均勝訴率約為21%,其中專利案件原告平均勝訴率僅約為12%,行政一審案件原告平均勝訴率約為17%。民事一審案件原告勝訴率可以參見表3。

表3 民事一審案件原告終結勝訴率(2008.7-2012.6)12.6
與“智慧財產法院”成立前地方法院審理同類案件時的原告勝訴率相比,“智慧財產法院”審理案件的原告勝訴率已有較大降幅。據學者統計,自2007年1月至2008年6月,地方法院總計47件專利侵權案件中,原告勝訴17件,勝訴率為43.59%。①參見 謝銘洋、劉孔中、李素華:《智慧財產法院判決統計與分析》,發表于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總體檢研討會(2009)。與美日法院相比,其落差亦非常明顯。有研究表明,美國法院專利侵權案件中,原告勝訴率為50%左右。②K imberly A. Morre, Judges, Juries, and Patent Cases: An Empirical Peek Inside the Black Box, 99 MICH. L. REV. 365, 380, 390 (2000); Jean O. Lanjouw& Mark Schankerman, Protec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re Small Firms Handicapped?, 47 J.L. & ECON. 45, 59 (2004).東京知識產權高等法院成立后,專利權人勝訴率不斷攀升,從2007年的24.32%上升至2011年的40%。③羅秀培:《專利舉發與無效抗辯雙軌制課題之初探——以日本法為中心》,司法院行政訴訟及懲戒廳編輯,智慧財產訴訟制度相關論文雜編(2010),第708頁。造成這一差距的原因比較復雜,但不容忽視的是,“智慧財產法院”法官“意見過于集中,反而形成正當權利人行使權利的障礙,或造成寒蟬效應”,④同注 釋。o或許是個中原因之一。
“智慧財產法院”對智慧財產第一、二審民事案件均有管轄權,這種制度設計成為“智慧財產法院”案件管轄和審理制度最受詬病之處。此外,在法官配置上,由于一、二審法官未分庭或分別設置,法官關系緊密。外界普遍質疑,同一法院、同一群法官同時負責審理第一審和第二審案件,法官能否不顧及同袍情誼獨立裁判,當事人的審級利益能否得到保障?“智慧財產法院”也面臨著自我撤銷判決的尷尬。從前述統計數據顯示的高上訴維持率看,這種質疑并非毫無道理。
(二)技術審查官制度運行效果考察
目前,“智慧財產法院”設有技術審查官13名,其中12名來自臺灣地區“智慧財產局”借調,1名通過社會選聘,尚無正式編制的技術審查官。實踐運作表明,技術審查官在專利侵權訴訟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其對案件之影響甚至不亞于審理法官。技術審查官協助法官辦理知識產權案件,能幫助法官精確判斷技術問題,增強法官處理技術問題之能力,對知識產權案件裁判品質之提升和審理效率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對此制度,業界總體評價均為積極正面。根據臺灣地區“司法院”2013年10月2日新聞稿,“智慧財產法院”近一年來受理的民事一審、二審案件及行政案件(商標案件除外)中,經法官指定技術審查官協助辦理的比例分別約為65%、59% 和74%。⑤轉引自郭雨嵐:《技術審查官角色與提升我國智慧財產訴訟品質之檢討》,發表于臺灣專利產業與爭端解決法治政策與國際化之檢討及展望研討會(2013年12月)。統計數據顯示,“智慧財產法院”新制施行后,智慧財產案件結案期間呈大幅縮短趨勢,縮短時間超過百日以上,上訴維持率和判決折服率也隨之提升,足以顯示技術審查官的輔助的確有助于法院審判質量與效率的提升。“智慧財產法院”成立前后審理效率指標,參見下表:

表4 “智慧財產法院”成立前后審理效率指標
但是,由于技術審查官的意見不向當事人公開,當事人對其沒有表示意見之機會,實踐中可能形成法官對于技術審查官意見的過度依賴等原因,業界對其亦有批評之聲,甚至將技術審查官稱作“影子法官”。從這一角度而言,技術審查官參與訴訟的方式、意見是否公開等,尚有進一步探討的余地。技術審查官的技術報告不予公開,主要理由和顧慮如下:一是制度移植的結果。臺灣地區技術審查官制度繼受日本及韓國制度,相關條文與日本東京高等知識產權裁判所關于調查官的規定極為類似。日本司法實務界一致認為,調查官系法院內部協助法官的技術助理,其報告與合議庭評議前受命法官預先草擬的書面備忘相似,僅屬合議庭評議過程的過渡性參考,不得單獨對外公開。二是技術審查官意見的特殊性。在“智慧財產法院”實務中,技術審查官可以口頭或者書面提供技術上的意見。隨著案件審理過程的深入,可能前后會有多數報告,其意見可能會增刪修正,甚至完全相反。如果技術報告一律予以公開,則前后意見不同的技術報告可能造成混亂,無助于定紛止爭。而且,法官需要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證據調查制結果作出裁判,并不受技術審查官所提供意見的拘束,公開似無必要。①引自 筆者“智慧財產法院”訪問記錄,有關資深法官對筆者提問作出上述答復。業界對技術審查官制度的疑慮則在于,技術審查官在專利訴訟中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其報告卻不公開,如果將技術審查官意見采為裁判的基礎,則當事人將喪失辯論機會。加之技術審查官經驗有限,容易形成技術偏見或者預判,且員額過少,回避問題難以解決。實務中,“智慧財產法院”重視落實“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8條的規定,在因技術審查官提供的意見獲得特殊專業知識時,均會在裁判前對當事人予以適當揭露,給予當事人以辯論的機會,避免發生裁判突襲的情形。臺灣最高法院也在多個案件中要求適時適度公開心證,避免突襲性裁判。②參見 臺灣“最高法院”100年度臺上字第480號、第1013號、第2254號判決。由此可見,對于技術審查官之報告,盡管目前并不全文公開,但是對于與法官形成心證提供積極輔助作用、與裁判結果有重要關聯性的報告,實務中已經通過法官公開心證的方式予以披露。
臺灣地區“智慧財產法院”設立技術審查官以來,在審理實務中,多數仰賴技術審查官意見,少有鑒定人、專家證人等參與審理,法院似乎多不采納雙方提交的鑒定報告,因而業界有批評認為,法院過度仰賴技術審查官意見,忽視證據調查。技術審查官人數必定有限,其同樣有專業知識的局限,而智慧財產案件涉及領域廣泛,所需知識遠非某一位法官、某一位技術審查官所能掌握。技術審查官不可能完全取代各方面的專業人士。因此,業界素有將技術審查官制度與鑒定制度、專家證人制度、專家咨詢制度等結合使用,可以相得益彰的建議。臺灣地區“最高法院”也在多個判決中表示,不能因為有技術審查官的參與,即可忽略或者舍棄必要的證據調查。③參見臺灣“最高法院”98年度臺上字第2373號判決、99年度臺上字第11號判決。
此外,對于技術審查官的來源、員額、任期等,業界也有改良的呼聲。臺灣地區“智慧財產法院”技術審查官目前多自智慧財產權局借調。因技術審查官需要兼具智慧財產法律知識和技術知識,且其培養不易,故自智慧財產權局借調是最便利且簡單易行的做法。由于技術審查官借調自“智慧財產局”,期滿后又回到“智慧財產局”,這一做法也引發了業界關于技術審查官既是球員又是裁判員的質疑。因此,是否有必要拓寬技術審查官的來源、如何確保其獨立性,仍有進一步探討的余地。在員額上,亦有意見認為,應該根據各專長技術領域及案件數量予以調整。在任期上,目前臺灣地區“司法院”規定,借調技術審查官,其最長期限不得超過兩年,必要時可以延長一年;約聘的技術審查官則采取一年一聘的處理方式。技術審查官的任期與案件審理期限及人員養成規律密切相關。民事一審專利案件通常涉及法律與技術爭點,審理期限較長,一般為一年左右,二審則相對較短,一般為3—6個月。為使技術審查官能夠跟隨案件處理整個過程,接受完整的歷練,加上熟悉法院業務也需要一定時間,其任期似乎應該更長。任期過短,更換頻繁,不僅不利于技術審查官熟悉業務,也不利于法院裁判案件。因此有主張延長技術審查官的任期為3年。④參見 芮嘉偉:《從程序保障觀點論技術審查官制度之改革》,中原財經大學法律學系2011年度碩士論文。
(三)侵權訴訟中法院自行判斷智慧財產有效性制度的運行效果考察
“智慧財產法院”在民事訴訟中自行審查智慧財產權的有效性,是臺灣地區“智慧財產法院”在審判機制上最具影響意義的舉措之一。這一制度借鑒了美國、日本法院的先行經驗,旨在解決民事侵權和行政無效二元分立體制下民事侵權程序久拖不決、訴訟效率低下等弊端,以求達到知識產權紛爭快速、有效解決之目的。該項制度被認為是“智慧財產法院”新制中最引人期待也最符合改革目的之設計。新制度施行后,權利有效性的確定成為法院審理智慧財產權案件的重要爭點。據統計,自2008年7月至2009年9月,臺灣地區“智慧財產法院”審理的專利權、著作權及商標權民事訴訟案件中,被告提出有效性抗辯的比例分別為83.53%、9.09%和6.45%。①參見范曉玲:《臺灣智慧財產法院》的建置與智慧財產權訴訟新制》,載張凱娜主編:《兩岸知識產權發展研究》,元照出版公司2011年11月版,第124頁。從實踐效果看,在技術審查官制度、集中審理制度等配套機制下,該制度的實施不僅大大提高了案件的審理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補救了“智慧財產局”專利授權品質不高的問題,總體上評價較高。表4““智慧財產法院”成立前后審理效率指標”足以說明這一點。“智慧財產法院”成立后,法官審結智慧財產民事一審案件所用天數縮短了165天;審結智慧財產二審民事案件所用天數縮短了357天。可見,實行在民事訴訟中審查智慧財產權效力這一制度后,訴訟效率提高極為明顯,效果顯著。
但是在實務運作過程中,“智慧財產法院”在民事訴訟中認定專利無效的比例過高,引起了較多關注。以下通過“智慧財產法院”專利無效抗辯成立比率來說明這一問題。

表5 專利民事案件有效性抗辯成立比率(2008年7月至2012年12月)12
2008年7月至2012年12月,“智慧財產法院”審理的專利民事案件中,有效性抗辯的成立比例很高,平均約為60%左右,其中發明案件中有效性抗辯成立比率為64.84%,顯著高出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案件中有效性抗辯的成立比例。考慮到發明專利經過實質審查才能得到授權,其質量應顯著高出無需實質審查就可授權的實用新型與外觀設計專利,發明案件中有效性抗辯成立比例之高頗令人費解。如果對比“智慧財產局”審查專利舉發案件②專利 舉發案件類似于大陸專利法上的專利無效宣告請求審查案件。時舉發成立的比例,則上述數據更是發人深思。
2008至2012年期間,專利舉發案件在“智慧財產局”得到支持的比例自50%至54%不等。③數據來源于“智慧財產局”2012年專利統計第55頁。轉引自李素華、張哲倫:《專利審查品質與專利訴訟的實證考察——臺灣智慧財產法院成立五年的數據回顧》,載《月旦裁判時報》2013年12月第24期,第9頁。與此相比,“智慧財產法院”在專利民事案件中對有效性抗辯的支持比例則高出6至10個百分點。如此高的有效性抗辯支持比率,造成了專利權人的極低勝訴率,引發業界關注。本文認為,有效性抗辯成立高比例的原因或許在于,“智慧財產法院”在專利民事案件中對專利有效性的判斷尺度比“智慧財產局”更為嚴格。之所以如此,恐怕與在審查有效性抗辯時法官和技術審查官的心理壓力有關。一旦有效性抗辯不成立,則被告通常需要承擔侵權責任。在這種心理壓力下,專利創造性判斷中的“后見之明”現象更易發生,法官和技術審查官無形中提高了專利有效性的判斷標準。令人擔憂的是,如果“智慧財產法院”在專利民事案件中認定專利無效的比率比行政舉發程序高,則會有民事訴訟程序替代行政舉發程序的可能。因為,舉發程序中無效專利權的可能性比民事訴訟程序更低,反而不如等待專利權人提起民事侵權訴訟后再提出專利權無效抗辯,利害關系人通過舉發程序挑戰專利權效力的積極性被減弱了。現實也證明了這一點,近年來臺灣地區“智慧財產局”受理的行政舉發案件確有下降趨勢。
在民事案件中審查智慧財產權的有效性,天然具有形成民事審判與行政程序的結果發生沖突的危險,在實務中也引發了不少爭議,確有必要通過有效的制度設計,防止效力認定沖突的出現。為此,“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及其細則主要采取了三種措施:一是命“智慧財產局”參加訴訟制度。在民事訴訟中,當事人或者第三人關于同一智慧財產權的撤銷、廢止已經提出行政爭訟程序時,法院可以斟酌行政爭訟的程序、當事人雙方的意見等,命“智慧財產局”參加訴訟表示意見。但是,由于行政舉發案件正在“智慧財產局”審理中,實質審理尚無定論,“智慧財產局”被迫加入訴訟,其究竟應該肯定還是否定智慧財產權的效力,會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實務中,“智慧財產局”參與訴訟的案件比例約為16%,且參與訴訟時通常不對全案表示意見,僅僅對案件的法律適用發表意見。①引自筆者在臺灣“智慧財產局”訪談時所作筆記。因此,從實踐效果看,“智慧財產局”參與訴訟的價值比較有限。二是限制被告提出智慧財產權無效抗辯的情形。對于智慧財產權有無應撤銷、廢止原因之同一事實和證據,如果已經行政爭訟程序認定舉發或者評定不成立,或者已經超過申請評定的法定期限,或者有其他依法已經不能在行政程序中主張的事由,在智慧財產民事程序中不得再行主張。這一規定避免了民事訴訟程序成為行政訴訟程序的重演,節省了訴訟成本。三是對于同一權利基礎的智慧財產權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同時或者先后系屬“智慧財產法院”時,可以分由相同法官辦理。這一制度設計對于防止不同案件法律判斷沖突很有意義。不過,這一制度也產生了外界質疑,認為其實際上使得不同案件的審理流于形式。此外,“智慧財產法院”的民事案件與行政案件的上訴法院并不一致,其民事案件的上訴法院為臺灣地區最高法院,行政案件的上訴法院是臺灣地區最高行政法院。民事案件與行政案件終審法院的不一致,加大了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中對智慧財產權效力判斷發生沖的突可能性。
專利民事案件與專利行政案件中對專利權效力判斷的沖突主要有兩種表現形式:一是民事判決確認專利有效,行政訴訟認定專利無效;二是民事訴訟確認無效,行政訴訟則認定專利有效。對于前一沖突情形,當事人可否提出再審之訴,臺灣地區智慧財產界對此有不同見解。在2009年智慧財產法律座談會上,多數意見采肯定說。“智慧財產法院”2013年度民專上再字第4號判決則采否定說。該案中,被告在第二審程序中才提出專利無效抗辯,由于有延滯訴訟的問題,根據相關程序規定駁回其專利無效抗辯,故民事確定判決未就專利有效性作判斷,判決侵權賠償確定。后被告另行提出舉發程序,經“智慧財產局”作成舉發成立撤銷專利權審定確定。②參見“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民專上再字第4號民事判決(判決日期2014年9月5日)。后一沖突情形,多數因民事訴訟中當事人提交的無效抗辯證據與行政舉發程序中提交的無效證據不同所致,民事案件的判決與行政案件的判決根據各自程序分別確定后,實質上并無內在沖突。對于民事案件與行政案件中面臨相同證據的場合,由于案件均需經過“智慧財產法院”審理,原則上不會出現沖突。實務中,由于“智慧財產法院”的技術審查官均為“智慧財產局”的資深優秀人士,在其輔助下,“智慧財產法院”在民事訴訟中對專利權效力認定的正確性很高。同時,“智慧財產法院”與“智慧財產局”溝通順暢,即使發生兩者對效力的判斷存在差異的情形,也能夠經由溝通而得以避免。從實踐中兩個機構之間的互動情況看,無效行政程序中“智慧財產局”對專利權效力的判斷顯然受到了民事程序認定的影響。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印證了高素質的技術審查官的重要性。如果沒有高素質的技術審查官,則法院在民事案件中對專利權效力判斷的質量和效率將會受到影響,民事程序與行政程序發生沖突的可能性也會增大。
對于民事審判中對權利效力的認定前后案可能發生沖突的問題,“智慧財產法院”實務中引入了“爭點排除原則”。①該原則在日本被稱為“爭點效”原則,在美國被稱為“爭點排除”原則或者“間接禁止反言原則”。關于美國法上涉及專利無效問題 “爭點排除原則”的最近判例,see In re Baxter International, Inc., 2012 WL 1758093 (Fed. Cir. 2012).即,盡管民事侵權訴訟中對智慧財產權效力的判斷僅限于該案,不及于該案當事人之外的第三人,但是在涉及同一智慧財產權的在后案件中,在后案件的當事人可以援引前案判決作為重要證據,提出攻擊或防御理由,審理后案的法院對此應予考慮。根據“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34條的規定,“智慧財產法院”民事訴訟的確定判決,如果對智慧財產權是否有應撤銷、廢止的原因已經作出實質判斷,關于同一智慧財產權應否撤銷、廢止的其他訴訟案件,當事人就同一事實基礎,提出與確定判決的判斷意旨相反的主張或者抗辯時,法院應審酌原確定判決是否顯然違反法令、是否出現影響判斷結果的新訴訟資料以及是否違背誠信原則等予以認定。這在實質上賦予了前案判決以“優勢證據”的效力,使其拘束力實質上超出了個案,有助于促進裁判結果的協調和節約訴訟成本。
如果被告在民事訴訟中提出智慧財產權無效抗辯的同時,智慧財產權人則主張其已經向智慧財產專責機關提出更正專利范圍的申請,法院應如何處理?②“更正”類似于大陸專利審查指南所規定的無效程序中的“修改”。如果對此置之不顧,逕行繼續審理,結果可能是認定智慧財產權無效,顯然不利于維護智慧財產權人的利益。為此,“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細則”第32條規定,除智慧財產權人的更正申請顯然不應被準許,或者依照準許更正后的請求范圍不構成侵權,可以繼續審理的情況外,法院應根據更正程序進行程度和當事人的意見,決定審理時間。此時,智慧財產民事侵權訴訟程度可能會暫時中止,等待更正程序的結果。可見,在允許法院在民事程序中對智慧財產權的效力予以審查的同時,也需要平衡智慧財產權人的利益,保障其修改權利范圍的權利。
(四)保全制度運行效果考察
關于證據保全制度。“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雖強化了智慧財產訴訟的證據保全制度,但是其實施效果并不理想。自2008年7月至2013年10月,在全部239件申請中,全部準許的僅有20件,部分準許的有12件,核準率僅為10.87%。③數據來源:“智慧財產法院”歐陽漢菁法官在臺灣專利產業與爭端解決法治政策與國際化之檢討及展望研討會(2013年12月)上的演講材料,筆者根據其材料綜合分析得到上述數據。由此推知,“智慧財產法院”在實務中對于證據保全采取非常保守的態度。與“智慧財產法院”成立前及成立不久時之情況相比,證據保全的核準率有較大變化。據統計,自2004年1月至2011 年9月,臺北地方法院就專利案作出73件證據保全裁定,核準率為22%;2002年1月至2011年6月,新北地方法院作出75件專利案件證據保全裁定,核準率為43%。④參見李素華、張哲倫:《專利審查品質與專利訴訟的實證考察——臺灣智慧財產法院成立五年的數據回顧》,載《月旦裁判時報》2013年第24期,第6頁。兩相對比,可見“智慧財產法院”對于證據保全的運作呈現保守趨勢。其原因或許有二:一是法官通常認為智慧財產案件與一般案件不同,易被濫用以打擊競爭者名譽、窺探營業秘密、干擾經營活動。⑤“智慧財產法院”歐陽漢菁法官在臺灣專利產業與爭端解決法治政策與國際化之檢討及展望研討會(2013年12月)上的演講材料即反映出上述心態。二是“智慧財產法院”管轄地域太大而人員編制有限,法官不自覺地以過高的門檻來檢視證據保全申請。在智慧財產權人收集證據的方法和手段受到限制,證據保全往往成為獲得證據的唯一手段的情況下,過低的證據保全核準率肯定會影響智慧財產權人的勝訴率。這一點與專利權人的過低勝訴率相吻合。
關于定暫時狀態假處分⑥臺灣“民事訴訟法”上的定暫時狀態假處分與大陸的行為保全有類似之處。。臺灣地區“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關于定暫時狀態假處分制度借鑒了美國最高法院eBey案所確立的四大要件,并要求達到釋明的證明標準,因而被認為采取了“本案化審理”的模式。從“智慧財產法院”實踐來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的核準比例同樣不高。自2008年7月至2014年11月,已經審結的77件申請中,準許的僅有12件,部分準許8件,核準比率約為20.77%。另據了解,自2008年7月“智慧財產法院”成立至2013年10月,“智慧財產法院”第一審專利權定暫時狀態假處分申請共計12件,全部被駁回。①數據來源:“智慧財產法院”歐陽漢菁法官在“臺灣專利產業與爭端解決法治政策與國際化之檢討及展望”研討會(2013年12月)上的演講材料。可見,在“智慧財產法院”實踐中,對于定暫時狀態假處分審核條件亦較為嚴格,特別是在專利案件中,定暫時狀態假處分幾乎不可能獲得。
證據保全申請和定暫時狀態假處分申請的較低支持率或許已經產生寒蟬效應,近年來該兩類申請呈下降趨勢,顯示權利人對于該制度缺乏信心。
(五)行政訴訟中接受新證據的利弊分析
對于“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3條規定的法院在行政訴訟中應審酌新證據的制度設計,在立法中曾引起較大爭議。否定該制度的理由主要在于:在行政訴訟程序采納未在行程處理程序提交的新證據,違反了行政救濟程序中“使行政機關得自我審查”、“第一次判斷權”之原則,逾越了司法權與行政權的分界;當事人很可能會怠于在行政處理程序中盡其舉證責任,前置的行政處理程序可能被徹底架空;對于訴訟中的另一方當事人有失公允,由于新證據未在行政處理程序中提出過,在后續審級提交后,會出現“證據突襲”的情況,亦會使對方當事人產生審級利益損失。肯定該制度的理由主要在于:避免發生循環行政訴訟而拖延未決,促使糾紛一次性解決;“智慧財產法院”法官的專門性提升,且有技術審查官輔助,在專業技術上有足夠的能力作出正確判斷;審級利益與迅速解決糾紛的利益同等重要,兩者均不能絕對化,至少法院應該在具體案件中有靈活處理的決定權,才能適應豐富多彩的現實。從實踐中看,“智慧財產法院”對于新證據應否采納,往往考慮當事人遲延提交的理由和訴訟延滯情況予以決定。該制度實行后,在業界得到普遍認同,少有批評之聲。這一制度設計對于盡快明確智慧財產權效力狀態發揮了積極作用。
三、臺灣地區“智慧財產法院”訴訟制度的啟示
臺灣地區“智慧財產法院”訴訟制度運行的經驗和教訓,足以為完善大陸知識產權法院訴訟制度提供鏡鑒。結合大陸知識產權法院當前面臨的問題和困境,如下幾點尤其值得我們深思。
(一)配套制定符合智慧財產案件審理規律的專門程序法
在“智慧財產法院”成立前,臺灣地區將智慧財產民事、刑事和行政案件當做一般民事、刑事和行政案件對待,分別適用相應的訴訟法,不可能針對智慧財產案件的特殊性給予特別的程序處置。臺灣地區在決定設立“智慧財產法院”的同時,即考慮到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的特殊性問題,制定了專門的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與“智慧財產法院”組織同時公布和施行。該法根據智慧財產案件審理的特殊需要,集中規定了智慧財產案件行政訴訟、民事訴訟及刑事訴訟的特殊制度,同時對不宜適用相應的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和刑事訴訟法之處予以明確。專門程序法的制定,使得智慧財產案件的審理擺脫一般民事、刑事或行政案件普遍性程序規則的束縛,更好地回應了智慧財產案件的特殊需求。智慧財產案件專門程序規則的制定,對保障“智慧財產法院”充分發揮效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臺灣地區的經驗表明,知識產權法院的運行要取得預期效果,不僅需要有形的機構和人員,更需要無形的制度配套,后者的重要性遠遠超出前者。如果缺乏適應知識產權案件審理規律和特殊需要的訴訟制度設計,知識產權法院的設立不過是原先知識產權專門法庭的獨立與擴大而已,其實質價值肯定要大打折扣。大陸在設立知識產權法院的過程中,對于知識產權法院的訴訟制度設計、知識產權案件審理所需要的特別訴訟規則等未給予足夠重視。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在北京、上海、廣州設立知識產權法院的決定》僅僅規定了知識產權法院的組織問題。對此,我們必須深刻反省,重視并研究為知識產權法院制定專門訴訟制度和特殊訴訟規則的必要性,以更好地實現設立知識產權法院的初衷與目的。
(二)科學設計案件管轄制度
臺灣地區“智慧財產法院”案件管轄制度表明,實行智慧財產民事、刑事和行政案件“三合一”對于避免不同類型案件的裁判結果沖突,提高判決的協調性和一致性確有必要。但是,由一個法院單純管轄智慧財產案件,法官固定處理專業案件,也可能使得法官視野受限、思維狹窄,無法從宏觀角度思考問題和作出適應社會經濟科技發展需要的裁判。從這一角度而言,即使對于專門法院,亦不宜過分強調其專門化,將其案件管轄僅限于某一類案件,而應根據案件特點以及與其他案件的聯系程度,適當選擇其他類型案件交由其管轄,這樣可以防止法官的過度專門化和視野狹隘化。與此相關的是,由一個法院單純處理知識產權案件,缺乏競爭,容易導致意見過于集中,對此亦應有所考慮。
大陸知識產權法院實行民事與行政案件“二合一”,不管轄刑事案件,亦不管轄除知識產權以外的其他案件。可見,在案件管轄制度的設計上,大陸知識產權法院既沒有借鑒臺灣地區知識產權民事、刑事與行政案件“三合一”的經驗,又似乎在案件管轄的單一性方面重蹈了臺灣地區的覆轍。此外,目前有關部門正在研究未來成立知識產權高級法院的可能性。對此,是建立一個管轄范圍覆蓋全國的高級法院,還是考慮到競爭和防止單一意見的需要,分地區建立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高級法院,亦值得慎重研究。裁判的統一性值得追求,裁判的多樣和活力同樣有其價值。畢竟在高級法院之上,還有唯一的最高法院,仍可以在最高法院層級上實現裁判標準的統一。如果過分注重在高級法院層級統一標準,就要承擔失去裁判的競爭與活力的代價。
(三)充分發揮技術審查官制度功能
臺灣地區“智慧財產法院”關于技術審查官的實踐運作表明,技術審查官對技術類案件裁判品質之提升和審理效率的提高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對此,業界已經形成共識。但是,對于技術審查官參加訴訟的方式及如何避免法官對技術審查官意見的過度依賴,仍有探討余地。為保障當事人訴訟權利,避免裁判突襲,以適當方式程度公開技術審查官意見實有必要。從實務中看,臺灣地區“智慧財產法院”雖然不全文公開技術審查官的報告,但對于與法官形成心證提供積極輔助作用、與裁判結果有重要關聯性的報告,實務中已經通過法官公開心證的方式向當事人披露。這對于當事人及時針對技術報告發表意見和提供證據至為重要。此外,對于技術審查官與鑒定專家、專家證人、專家咨詢等制度的關系,亦需要正確處理。從臺灣地區“智慧財產法院”的教訓看,過度仰賴技術審查官意見,忽視證據調查,不積極支持專家證人、鑒定人等參與審理,不利于正確查明技術事實。因此,即使設立了技術審查官制度,亦需要將其與鑒定制度、專家證人制度、專家咨詢制度等結合使用,建立多元化的技術事實查明機制。對于技術審查官的來源、員額、任期等,亦應進行合理設計。在技術審查官來源上,除主要從知識產權局借調外,為防止技術審查官既是球員又是裁判員的風險,確保其獨立性,可通過聘用方式從社會公眾中選擇。在任期上,適應案件審理期限及人員養成規律,其任期不易過短,以3年為宜。在員額上,應該根據案件數量動態調整,不宜固定不變。
大陸知識產權法院借鑒了臺灣地區“智慧財產法院”的有益經驗,首次建立了技術調查官制度。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出臺了《關于知識產權法院技術調查官參與訴訟活動若干問題暫行規定》。從上述規定關于“技術調查官提出的意見應當記入評議筆錄,并由其簽名”、“技術調查官提出的技術審查意見可以作為法官認定技術事實的參考”等表述看,該規定對于技術調查官的意見似采取不向當事人公開的立場。由于大陸法律缺乏適當公開心證并給予當事人辯論機會的規定,發生裁判突襲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對此,司法實務似應借鑒適時公開心證的做法,以保障當事人的辯論權利。此外,對于技術調查官的來源、員額和任期,亦應科學規劃,以充分發揮技術調查官的職能作用。
(四)探索在民事案件中適度審查知識產權效力
法院在民事訴訟中自行審查智慧財產權的有效性,打破了民事侵權訴訟與行政無效訴訟二元分立的傳統,是臺灣地區“智慧財產法院”在審判機制上最具影響意義的改革措施之一。在技術審查官制度等配套機制下,民事訴訟不需要等待行政程序的結果,法院可以自行判斷和繼續審理,因而克服了民事侵權程序久拖不決、訴訟效率低下等弊端,訴訟效率大大提高。但是,由于臺灣地區“智慧財產法院”在專利民事案件中對專利有效性的判斷尺度比“智慧財產局”更為嚴格,致使民事程序中認定智慧財產權無效的比例過高,該制度的副作用被放大了。不過,如果僅以此種副作用為由否定該制度的價值,則未免因噎廢食。當然,該制度的實行,可能造成較為復雜的局面,需要予以防范。一是該制度天然具有發生效力判斷沖突的危險,需要有效的配套制度設計予以避免。二是該制度對于智慧財產權應否無效或撤銷的理由未作任何限制,所有在行政程序中可以提出的無效和撤銷的理由均可以在民事訴訟程序中提出,可能將民事程序轉變為行政程序的預演或者重演。三是該制度有益效果的實現,不僅需要技術審查官等制度配套,還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尤其是在智慧財產權人已經向有關機關提出更正權利范圍的申請的情況下,該制度提升審理效率的功能將受到限制。
大陸知識產權法院在設立之時,盡管同樣面臨因民事侵權與行政無效二元分立而造成的訴訟拖延、效率低下等問題,但對該問題的解決未作針對性設計,至為遺憾。不過,司法實踐對于此問題早已有所認識并開展了可貴探索。最高人民法院曾以司法政策的方式要求,“合理強化民事程序對糾紛解決的優先和決定地位,促進民行交織的知識產權民事糾紛的實質性解決。對于明顯具有無效或者可撤銷理由的知識產權,權利人指控他人侵權的,可以嘗試根據具體案情直接裁決不予支持,無需等待行政程序的結果,并注意及時總結經驗。”①《第三次全國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工作會議材料》(2013年3月21日)。這一司法政策以不保護具有明顯無效理由的知識產權的方式,引導法院在民事侵權案件中對知識產權有效性進行有限審查,在現行立法框架內實現了對專利民事行政二元分立體制的謹慎突破。本文認為,大陸知識產權法院在此方面完全可以借鑒臺灣地區和日本的經驗,在此方面進行大膽探索。主要理由在于:首先,因專利民事行政二元分立體制造成的司法效率低下和結果不公平在大陸已經較為嚴重,必須尋找解決方式。知識產權法院在此方面首當其沖,理應率先探索。其次,知識產權法院已經設立了技術調查官制度,這一制度可以較好地保證民事程序中法院對知識產權效力判斷的準確性。第三,該制度的復雜性和裁判沖突的風險完全可以通過相應的制度設計予以避免和緩和。例如,堅持民事侵權程序中認定知識產權效力的相對性和有限性、引入爭點排除原則、充分發揮上訴審和審判監督程序在統一裁判尺度以及標準方面的功能作用等,均可以有效將裁判沖突的制度風險降至可以接受的幅度之內。②關于該問題的具體探討,詳見朱理:《專利民事侵權程序與行政無效程序二元分立體制的修正》,載《知識產權》2014年第3期,第37-43頁。
(五)加大證據保全力度和合理運用行為保全制度
臺灣地區“智慧財產法院”關于證據保全和定暫時狀態假處分的實踐表明,過高的審查標準、過低的支持率對于智慧財產權人維護權利較為不利,原告敗訴率居高不下,寒蟬效應明顯。近年來,臺灣地區“智慧財產法院”受理的智慧財產案件數量呈下降趨勢,“智慧財產局”受理的專利申請量也有下降之勢。這似乎一定程度上表明,智慧財產的創造者和權利人正在發生“逃離臺灣”的現象。每一個司法系統都是與全世界競爭的,如果某個司法制度不能控制司法成本和復雜度,不能提供優質高效的司法服務,權利人將輕易地選擇其他更好的解決方案或者去其他地方解決紛爭。
長期以來,大陸法院在證據保全申請和行為保全申請上亦或多或少存在與臺灣地區法院類似的現象,對于證據保全申請和行為保全申請的審查門檻設置過高。或許是由于大陸這一巨大市場的吸引力,大陸法院對待證據保全和行為保全申請時偏消極的處理傾向并未對權利人尋求司法救濟的積極性造成顯著影響。但是,臺灣地區的教訓足以警示我們,對此決不能掉以輕心,應該更加合理規范證據保全和行為保全的條件和程序,積極合理發揮其制度效能,依法采取保全措施,提高知識產權司法救濟的及時性、便利性和有效性。
(六)合理接受行政程序中的新證據
臺灣地區“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規定的法院在行政訴訟中應審酌新證據的制度設計,雖在立法之初存在爭議,但是實施過程中少有批評。該制度對于避免發生循環行政訴訟而拖延未決,促使糾紛一次性解決,盡快明確智慧財產權權利狀態發揮了積極作用。實踐結果表明,立法之初否定該制度的意見不具有說服力。首先,所謂在行政訴訟程序采納未在行程處理程序提交的新證據,違反了行政機關“第一次判斷權”的原則的說法難以成立。“第一次判斷權”原則并非絕對,例如在行政訴訟程序中的補強證據問題,如果一律堅持行政機關“第一次判斷權”,則未免過于僵化。而且,在行政訴訟程序中,可以給予行政機關就新證據發表意見的機會。其次,關于當事人可能因此怠于在行政處理程序中盡其舉證責任問題。該種風險確實存在,但是其可以通過相應的制度設計予以避免。例如,可以對接受新證據的情況予以限制,對于故意或者重大過失遲延提交證據的當事人,可以拒絕采納。第三,關于證據突襲和審級利益損害問題。在行政訴訟程度階段,對于當事人提交的新證據予以審酌時,應該給予對方當事人相應的答辯期間,證據突襲的危害因此大大減弱。關于審級利益問題,對此不應絕對化,審級利益固然重要,迅速解決糾紛同樣重要。在個案中,應允許法院根據當事人遲延提交的理由、審級利益和迅速解決糾紛的需要等多種因素,作出適當選擇,不宜一概拒絕接受新證據。
近年來,大陸法院在行政訴訟實踐中對于新證據的接受已采取了相對靈活的立場,但是這一靈活立場多針對補強證據的情況以及不接受新證據則當事人將喪失救濟機會且沒有其他救濟渠道的情形,適用范圍相對較窄。從臺灣地區經驗看,允許法院在行政訴訟中審酌新證據,強化了知識產權效力判斷的裁決性,淡化了行政處分的特征,更符合知識產權效力判斷的本質屬性。大陸行政訴訟實踐中,由于法院缺乏對知識產權效力判斷的司法變更權,亦缺乏大陸法系通行的課義務判決的操作模式,致使循環訴訟現象屢有發生。在此情況下,適當擴大接受新證據的范圍,更加必要和迫切。
結 語
北京、上海、廣州知識產權法院成立已近一年,在加強人員、機構等硬件建設的同時,不容忽視、甚至更加重要的是知識產權法院訴訟制度建設。從知識產權法院的實踐看,訴訟制度改革舉措頂層設計的缺乏和不足,已經對其充分發揮效能形成較大制約。盡快改革和完善知識產權法院各項訴訟制度,已是迫在眉睫。希望本文對于我國知識產權法院訴訟制度的頂層設計和實踐運作能夠有所助益。
At the same tim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urt, Taiwan legislature enacted special litigate system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cases. This special litigate system is crucial to the success of Taiw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urt.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 of Taiw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urt and its litigation system can enlighten us on perfecting the Chinese mainl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urt system.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urt; litigation system; enlightenment
朱理,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法官,法學博士
本文完成于作者在我國臺灣地區“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訪問期間(2015年1月-3月)。臺灣地區“智慧財產法院”、“智慧財產局”、專利代理師公會等機構提供了大量幫助,謹致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