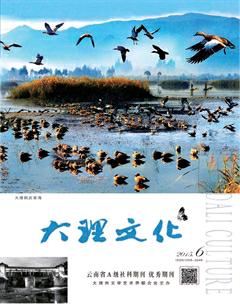矢志不渝覓清音
左了
民族音樂,是廣大勞動人民的審美情趣和智慧的結(jié)晶,如散落于民間的一顆顆珍珠。省級非物質(zhì)文化傳承人字升,憑著幾十年的堅韌和執(zhí)著,挖掘民間音樂的“寶藏”,并一一收集整理,使巍山民間歌曲廣為流傳,異彩綻放。
一
沿著巍山壩子西邊山腳的簡易公路,一路驅(qū)車南行到達一個叫做阿朵村的彝族寨子,在一所干凈整潔的院子里,我們見到了省級非物質(zhì)文化傳承人字升。
招呼我們在客堂坐下后,已經(jīng)七十六歲的字升特意回到屋子里,穿上了一套珍藏多年的演出服裝,那演出服裝外面是一件做工精致的黑羊皮褂子,挎包用上好的羊皮去毛,經(jīng)雞蛋黃反復(fù)揉搓光亮后縫制,有的還裝飾皮穗帶,綴上珠子。在彝家男子眼里,擁有一件全無雜毛,黝黑發(fā)亮的羊皮褂,再有一個做工考究的羊皮挎包,就等于有了一套名牌服裝。
“手感不錯,還沒有羊膻味。”我伸手摸了摸那羊皮褂子的皮毛。
“絕對是真正的手工貨,原生態(tài),形影不離伴隨我?guī)资炅恕!弊稚砹死硌蚱す幼樱芽姘频缴砗笤诎宓噬献拢瑵M臉堆笑地和我們聊起了他的人生過往……
1939年,字升出生于一個地地道道的彝族農(nóng)民家庭,父母靠種地為生。由于出生在能歌善舞的彝鄉(xiāng)彝寨,天資聰慧的他白小就對民間歌舞感興趣,喜愛白己制作一些簡易的樂器,還喜歡和小伙伴們一起跟隨大人唱唱跳跳。很快,字升就在父親和幾位歌舞能手的幫教之下學(xué)會了彝族踏歌和笛子吹奏。
在上小學(xué)的時候,字升在班里顯露出了音樂方面的才華,在一位音樂老師的引導(dǎo)和幫助之下他慢慢喜愛上了音樂,有時候,遇上老師家里有事情,老師就會委托字升教大家唱唱歌,吹笛子,或者踏歌,小小的他不負眾望,不僅當起了班里的小音樂老師,還逐漸成為了村里小伙伴之中最能干的踏歌唱調(diào)能手。
村里有位老歌頭經(jīng)常和父母開玩笑說:“你家小字,生辰八字里注定了藝術(shù)天命。”
這位德高望重的老歌頭,對字升幫助很多,字升從小就對其崇敬有加,心懷感激。
1952年字升小學(xué)畢業(yè),順利考入了巍山二中的初中班學(xué)習。在巍山二中上學(xué)的那段時光,帶著鄉(xiāng)村孩子特有的那一份淳樸,字升第一次在遠離彝寨的小鎮(zhèn)上獨立生活,刻苦學(xué)習文化知識的同時,他不忘哼唱那些從小聽著長大的彝族民歌,用美妙的笛子掃除學(xué)習上的辛苦。同班和同宿舍的同學(xué)們經(jīng)常被他的歌聲和笛聲所感動,不斷地夸他唱的好,吹奏的好。就是這些同學(xué)和朋友悄無聲息的鼓勵,更加堅定了字升學(xué)習音樂的決心。
在巍山二中,字升還遇到了一位很好的音樂老師,平時利用上音樂課的機會,他總是追著音樂老師的屁股打破砂鍋問到底,有時候,還會在下課后跑到老師的宿舍問一些音樂方面的問題。
1959年7月,字升從巍山二中初中畢業(yè),天賜良機,云南藝術(shù)學(xué)院到大理招收首屆音樂專業(yè)學(xué)生。字升從二中的老師口中得知消息后,壯著膽子搭了個便車,跑到下關(guān)應(yīng)試。
當時的下關(guān)已經(jīng)是滇西很是繁華的城市了,第一次從巍山到下關(guān),字升感覺一切都十分陌生,四處打聽問路之后,饑腸轆轆的他腳走加小跑終于在開考之前找到了考試的地方,餓著肚子唱了一首從小放牛和一位老人學(xué)會的《牛歌》,又用白己制作的竹笛吹奏了一曲割豬食草時學(xué)會的《埂子調(diào)》。
動情的歌曲和悠揚的笛聲打動了當時的考官,當場便給了字升一個第二天參加復(fù)試的機會。在車站的椅子上睡了一晚,次日的復(fù)試順利通過。
苦苦等待兩個多月后,1959年10月,字升以優(yōu)異的成績考入了云南藝術(shù)學(xué)院音樂系,參加了附中及本科兩個階段的學(xué)習。
1966年7月,字升從云南藝術(shù)學(xué)院畢業(yè),分配到大理州漾濞縣文化館T作,在綜合性藝術(shù)學(xué)院學(xué)習的7年時間,為他今后的藝術(shù)生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chǔ)。
1973年,為了照顧在家務(wù)農(nóng)又體弱多病的妻子和父母,字升向上級申請后順利調(diào)回到了巍山縣工作。
“我們出生的那個年代,物質(zhì)匱乏,最好的享受就是聽那些老人家哼上幾首傳唱了不知多少代人的歌曲調(diào)子,沒人知道誰是作者,但那些動聽且朗朗上口的曲調(diào),還在民間一直口口相傳。”字升說,眼角里充滿了一絲憂郁。
“不哼調(diào)子不說話,不唱山歌不出門。彝族人善于用山歌小調(diào)表情達意,用狂熱奔放的打歌舞步踏平坎坷。”我接著字升的話說道。
“啊!我尼心肝妹。隔山叫你,么山答應(yīng),隔水叫你,么水應(yīng)聲……”字升隨口唱了幾句。
回到巍山,回到闊別多年的故土,字升的心中油然生出一種濃郁的真情,特別是對于民族民間的民歌,他覺得白己有義務(wù),有責任讓其發(fā)揚光大。
后來到文化館工作,字升有了更多接觸、收集和整理民族民間民歌的工作機會。由此,字升邁上了艱辛的采集民間歌曲之路。
二
字升先后多次到青華、五印、馬鞍山鄉(xiāng)的彝族村寨找一些老歌手,歌頭,因為他們手里有最好的材料,肚子里有最好的民歌調(diào)子。一般一開始,他們都不愿演唱,字升便用激將法讓他唱歌,先是字升白己先起個調(diào)子,把他們的唱調(diào)子癮逗起來,字升還會隨身背著一壺包谷酒,唱調(diào)子之前擰下壺蓋子,先讓他們喝上幾口小酒。幾分鐘后,果然,老歌手們便扯開嗓子高聲唱起了那些聽都沒有聽過的山歌調(diào)子,字升喜出望外,總算采集到了原汁原味的民間山歌調(diào)子。
字升說,記得那是1982年,正值春節(jié)前十幾天的樣子,他走路來到馬鞍山鄉(xiāng)的一個彝族村寨里收集資料。那時候,工作條件十分艱苦,字升向朋友借了一部錄音機,時間僅限三天,字升抓緊時間由遠及近入村收集。
正所謂“彝家戶戶有火塘,彝山處處是歌場。”在巍山,無論婚喪嫁娶、飄梁豎柱、吉慶佳節(jié)、山林廟會,彝家人都要舉行盛大的打歌活動。
字升去山里收集民間音樂的那幾天,卻沒有人家辦事,也無廟會節(jié)慶活動,他托一位老友,請來幾位村里的老歌頭。幾位老歌頭因為多年未唱,見是熟人字升,一開腔便唱到深夜,這個場面深深打動了字升。
至今,字升都還記得那幾位老歌頭唱的調(diào)子:
“太陽不照彎子路,月亮不照被陰山,這世搭你做姊妹,二世搭你做夫妻……”
“小小葉子阿米汝,小小葉子阿米汝,山高路遠老做客,不是做客來打歌,不是做客來打歌……”
“蜜蜂采花來路遠,不看路遠看花香……”
“哥是山中山茶花,妹是樹上花一朵。太陽落山山冷了,阿妹走了哥冷心……”
“山上不有山板凳,撮把葉子坐攏來。三股弦線難調(diào)和,世上難找合心人。要做姊妹長年做,莫學(xué)楊柳一季綠。河邊楊柳根不串,花盆栽花根串根……”
“妹想阿哥心甘處,妹愛阿哥命甘心。阿哥愛妹茶山走,不知阿妹落那山……”
“阿哥瞧我不說話,阿妹回頭你又跑。阿哥害羞我曉得,挑水路上我等你。兩只水桶打滿羅,等著阿哥來挑水。阿妹洗得小白菜,切塊豆腐煮給你。挑水挑到妹家去,放下扁擔你別走。”
“歐回回!三月鷓鴣滿山叫,鷓鴣越叫,越想你!”
待老歌頭們走后,字升不顧夜深疲勞,一邊放錄音,一邊用文字和曲譜記錄了下來,將全套幾十首歌曲整理成章,在老友家一忙就是三天。
第四天,天空下起了貴如油的春雨,山鄉(xiāng)大地乍暖還寒,好多人都待在家里烤火取暖,字升只得淋著雨徒步進村入宅四處采訪收集民歌材料,一路上隨時不忘檢查一下包裹著錄音機的塑料布有沒有漏水。
沿著崎嶇泥濘的山路完成搜集任務(wù)回到阿朵村時,已經(jīng)是第五天了,把錄音機還給朋友之后,字升回到家里扒了幾口飯菜,喝了幾口包谷酒,繼續(xù)做起了整理完善那些收集來的材料工作。
幾十年來,在巍山的崇山峻嶺,村民們經(jīng)常可以看見一位穿著羊皮馬甲的彝族黝黑漢子在村寨間行走,有時坐在篝火旁,有時立在老樹下,與熟悉當?shù)厣礁枵{(diào)子的老者徹夜長談,傾聽畢摩的悠長吟詠,錄下歌頭的調(diào)子,與他們一起和笛踏歌,記下他們的風俗。
“現(xiàn)在巍山彝族民歌為何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以及深刻的感染力?”我看著字升不解地問道。
字升淡淡地回答說:“勞動人民的民歌創(chuàng)作,一般是口頭創(chuàng)作,口頭流傳,并在流傳過程中不斷經(jīng)過集體的加工,是人們在山間野外放牧、砍柴、挑擔、鋤草、行路等個體勞動生活中隨意詠唱的一種短小民歌。歌者完全不受正在從事的勞動節(jié)奏的限制,興之所至,引吭而歌,唱腔充滿白由、奔放、舒展、悠長的特色。除了辦喜憂二事以外,彝族地區(qū)群眾還有很多山會時興踏歌而千古不滅。他們約定俗成地走在一起,凝聚人心,凝結(jié)親情友情,體現(xiàn)團結(jié)和睦的民族精神,是一種健康的民間活動。巍山的民間山會主要有:正月初九的牛街茶房寺、五印龍街靈寶山、馬鞍山茶山寺、青華新山;正月十四的小雞足山:正月十五的五印山:正月十六的巍寶山土主廟祭祖、大倉小三家一帶過春節(jié);二月初八的牛街阿許地洗澡塘、大倉新勝一帶的祭“密枯”神以及遍及各地的“密枯”節(jié)(過小年):二月十五的牛街筆架山:三月十五的牛街愛民老黑棚和牛街直捷瓦葫蘆等,目前這些山會趕集人員越來越多,越過越熱鬧。”
說完,字升轉(zhuǎn)身到堂屋里取出一個厚厚的包裹,一層層慢慢打開,向我們展示了他十幾年前手抄整理的厚厚一大疊曲譜。
“這些曲子都是祖先傳下來的,如果不學(xué)習不傳承,很容易就會失傳,所以我把分散的譜子手抄下來訂成本,既方便學(xué)習梳理,又方便將這些譜子保存起來,如果不趕緊搶救保護,以村寨為依托的那些民族民間民歌就會喪失白己的身份標志。”字升接著說。
字升認為這一切歸功于民間濃郁的傳習氛圍。在巍山的彝族地區(qū),青年男女談戀愛時要踏歌唱調(diào),結(jié)婚后母親懷孕時在踏歌唱調(diào),背著娃娃時在踏歌唱調(diào),牽著娃娃也要踏歌唱調(diào),娃娃長大白己要去踏歌唱調(diào),如此循環(huán)延續(xù),使得踏歌唱調(diào)的因子白然地深入彝族男女的骨血,那種天然的韻味猶如陳年老釀般蕩漾開來,其魅力說不清道不明,讓人癡迷。
同是在巍山,打歌種類因地區(qū)不同而在打歌步調(diào)、速度、風格和特點上都有些差異。巍山彝族打歌根據(jù)舞步和唱腔不同,大致可分為五種類別:第一種是以南詔鎮(zhèn)前新村為代表,以蘆笙、笛子為主旋律,不用大刀。巍寶山鄉(xiāng)、五印鄉(xiāng)、牛街鄉(xiāng)、青華鄉(xiāng)都屬于這一類別。而以馬鞍山青云村為代表,以蘆笙和笛子的快節(jié)奏為主旋律,伴有大刀。馬鞍山鄉(xiāng)、紫金鄉(xiāng)基本上屬于這一類別。
另外一種是以大倉小三家為代表,以蘆笙加舞大刀為主旋律,笛子基本不用。大倉鎮(zhèn)的小三家、新勝和廟街鎮(zhèn)的惠明草場一帶屬于這一類別。還有一種就是以廟街鎮(zhèn)云鶴村委會字升他們阿朵村為代表,將五印、馬鞍山、大倉的打法揉為一體,樂譜節(jié)奏、步法、調(diào)子等變化之快,幾種打法共同兼有。
據(jù)字升介紹,廣義的“山歌”是把民歌作為各類民間歌曲的總稱,山歌遂成為民歌中的一個類別。關(guān)于山歌的概念,通常認為,凡是流傳于高原、山區(qū),吟唱于山間、田間、路旁,人們在各種個體勞動如行路、砍柴、放牧、割草或民間歌會上為了白慰白娛而唱的節(jié)奏白由、旋律悠長的民歌,就是通常所說的山歌。或者說,山歌是人們在野外勞動、上山砍柴、趕馬馱貨、放牛放羊、農(nóng)事耕作或漫步行走時,用來消愁解悶、抒發(fā)情感、遙相對答、傳遞感情而白吟白唱或相互對唱的民歌。山歌的音符獨具特色,音樂性格真摯質(zhì)樸,熱情奔放,即興性特別強。山歌流傳分布極廣,蘊藏也極為豐富,大多是以獨唱或?qū)Τ问匠霈F(xiàn)。見景生情,即興編詞,內(nèi)容以表現(xiàn)勞動與愛情生活為主。山歌的音樂極富地方特色,是民歌中風格性最強的樂曲。
通俗的說法,山歌就是無論男女老少、砍柴放牛、上山割草、出門就唱的調(diào)子。小調(diào)是人們在勞動之中、日常生活之中以及婚喪節(jié)慶之中,用以抒發(fā)情懷、娛樂消遣的民歌。民間小調(diào)具有完整的歌詞和固定的音韻節(jié)律,它不像山歌具有靈活的即興性。比如“砍柴調(diào)”、“田埂調(diào)”、“放羊調(diào)”等,其唱腔和唱詞都有嚴格的節(jié)律,不可以白由吟唱:又如“十二屬調(diào)”唱十二屬,“采花調(diào)”、“勸賭調(diào)”等都唱十二個月,多一月少一月且不行,因此,山歌和小調(diào)又具有明顯的區(qū)別。
字升還向我們介紹民間小調(diào)多數(shù)屬分節(jié)歌形式,一曲多段詞,常采用十二月、四季、十二時等時序體,常以花名等形式聯(lián)綴,多側(cè)面、較細致的陳述內(nèi)容。為適應(yīng)多段詞的需要,其曲調(diào)則概括、凝煉地表達某種情緒,或柔美、或哀怨、或歡快,曲調(diào)性強、旋律流暢、婉轉(zhuǎn)曲折,旋律線豐富多變,表現(xiàn)力強。小調(diào)的節(jié)奏規(guī)整,節(jié)奏型豐富多變,歌唱形式以獨唱為多,其次為對唱、合唱等。民間小調(diào)的歌詞格式多樣,除七字句外,也有長短句式,除四句常見外,也常有非對偶的三句、五句等結(jié)構(gòu)。加上襯詞的豐富多變和格律化,使小調(diào)的曲式結(jié)構(gòu)較之山歌更為成熟且富于變化。
民間小調(diào)因歌詞格式多樣而富于變化,并用襯字、襯句擴充音樂結(jié)構(gòu),加強感情表達。涉及日常生活、社會生活、風俗、愛情等各個方面。由于民間小調(diào)是舊時流傳下來的,對舊時代勞動人民受壓迫、受奴役的苦難生活有廣泛的反映,如“苦媳婦”、“勸賭調(diào)”等,都產(chǎn)生于這些社會歷史背景。民間小調(diào)所反映的社會生活內(nèi)容極其廣泛。它不受某個特定的社會階層和具體勞動環(huán)境的制約,它所反映的不僅包括農(nóng)民的苦難生活,而且還包括其他各種階層的愛情婚姻、離別相思、風土人情、娛樂游戲、自然常識、民間故事等,其中有不少小調(diào)的唱詞還往往能夠以高度的概括力和尖銳的批判鋒芒觸及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如本集中的“勸賭調(diào)”一樣,從而使主題獲得了廣泛的社會意義。
字升說,在彝族文化里,最具代表性也最具特色的就是民歌,這些在勞動生活中逐漸形成的歌謠,唱出的都是如何歡樂的勞動,怎樣憂傷的失戀,婚禮是多么莊重,祭祀有多神圣,歷史如何悠久,它無時無刻不在表現(xiàn)著人們的精神信仰和生活狀態(tài)。因此,靠口耳代代相傳的民歌是民族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從此,他走上了一條艱難的收集整理和傳承之路,并且越走越動情,越走越迷戀。
當然,真誠、熱愛和堅守,只是一個人成就一番事業(yè)最為基本的品質(zhì)。近半個世紀對彝族民歌和民間音樂的研究,使得字升對這門藝術(shù)一直保持著執(zhí)著的偏愛。
年輕時下鄉(xiāng)采風,為了錄到原汁原味的彝族民歌對唱,常常蹲在樹林里待到凌晨1點多,等對歌的人開唱了就開始錄。回去就拿著那個飯盒式的小錄音機反復(fù)地聽。創(chuàng)作出來的歌曲,字升一定要找到能夠唱出他想要的韻味的人來表現(xiàn),才愿意將歌曲交予他人傳唱。
字升有一首歌十多年前就創(chuàng)作完成了,但一直找不到人可以很好地表現(xiàn)出歌的韻味,直到收到現(xiàn)在的徒弟,才覺得她演繹出了字升想要的那種彝族歌曲的韻味了。字升坦言,青年時在巍山文工團工作常年行走于各個彝族村落采風的經(jīng)歷,使得白己對于巍山彝族各個支系的踏歌風格有深入的了解,也為創(chuàng)作提供源源不斷的靈感。
三
民間文化的傳承方式往往是無形的,靠口口相傳,手把手地教,代代傳承。如果上了年紀的傳承人不在了,傳承的線索就斷了,一種藝術(shù)形式也就消失了。
字升掌握著豐富的民族民間音樂舞蹈知識,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民族民間音樂舞蹈及歌曲,是巍山當?shù)厥炀氄莆彰褡迕耖g音樂和舞蹈搜集、整理、創(chuàng)作技藝的民間文化工作者、民族民間傳統(tǒng)文化傳承人。他通過幾十年如一日的辛勤工作,默默地保護和傳承著巍山獨具特色的彝族民族民間音樂和踏歌文化,由一個學(xué)院派的文藝工作者成長為一個地地道道的民間藝人,一個能導(dǎo)、能唱、能跳、能演的名副其實的彝鄉(xiāng)歌舞藝人。
1995年底,字升從縣文工隊退休,但對音樂事業(yè),對收集整理和傳承民間民歌的工作熱忱不減,授課、擔任藝術(shù)指導(dǎo)、創(chuàng)作音樂,誨人不倦,不亦樂乎。
退休了,時間多了,身體開始走下坡路了,為了繼續(xù)完整采集和整理巍山民歌調(diào)子,年過七旬的字升依然早起鍛煉身體。現(xiàn)在他走遍了全縣所有鄉(xiāng)鎮(zhèn),足跡遍布60%的彝族寨,訪問山歌手100多人,采錄民歌幾百首。精選部分民歌調(diào)子編著成《臘羅巴的歌》(和楊建英合著)。
作為省級非物質(zhì)文化傳承人,出來繼續(xù)做好民族民間音樂的收集整理工作,傳承也是其主要工作之一。
“傳承性保護是最具文化延續(xù)性的保護,關(guān)于保護和傳承字老師是如何做的?”
字升想了想答道:“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是民族文化的基因和命脈,傳承好保護好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可以展示千百年來我們民族的生活智慧、勞動智慧以及人生智慧,可以寓教于樂地培養(yǎng)下一代的文化認同和文化責任。如果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不能傳承,關(guān)于民族的記憶、文化的發(fā)展都可能隨之消失。”
“保護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不是件容易的事。伴隨一些口授人相繼離世,民族民間音樂就會逐一遺失,包括民歌、調(diào)子,甚至一些器樂的演奏技藝的失傳。另一方面,字老師也是音樂學(xué)院科班畢業(yè),西方和大眾文化、消費文化也在不斷沖擊我們的傳統(tǒng)民間文化。你覺得傳承、保護,有哪些有效的方式?”我問。
字升:“非物質(zhì)文化誕生于民間,要保護和光大也只能從此著力。首先,是屬地化保護,其次就是收集整理和推廣。
“今天的年輕人會接受、喜歡以這種傳統(tǒng)形式來展示他們生活的形式嗎?踏歌唱調(diào),對于年輕人,似乎只是一時興趣的事情,好多人無法堅持下來。”
字升:“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是千百年文化傳承和累積的結(jié)果,與現(xiàn)代文化形成較大反差,這種文化反差正是文化的互補和魅力所在。現(xiàn)在好多民間歌舞和音樂正在走進城市、走進青少年,走進學(xué)校,走進我們的生活,脫去身上的民族演出服裝,我們幾乎都不知道自己是誰。當然,我們不能強迫必須接受,每個人有自己的文化選擇方式,但是我們不能夠拋棄我們民族民間的好東西。”
“融人生活,意義何在,如何融入?”
字升:“把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融入我們的生活方式,就是平常唱唱跳跳的生活,就能強化文化記憶,固化民族身份,因為,文化記憶一旦消失,民族身份一旦丟失這就很危險了。所以我一直在竭盡全力做著民間民歌調(diào)子和民間音樂的收集整理和傳承工作,想方設(shè)法留住民間的那些好東西。”
字升不但采集了諸多山歌,還挖掘培養(yǎng)了不少民間歌手。數(shù)十來,字升發(fā)表了有關(guān)民間歌曲的論文10多篇,創(chuàng)作了民間歌曲1000多首,撰寫了幾十萬字的民歌采集筆記。
字升說:“作為一個普通的彝族人,作為一名基層文藝工作者,雖然退休了,我依然有責任、有義務(wù)讓這些祖祖輩輩傳承下來的好東西傳承下去,發(fā)揚光大,后繼有人。”
“你現(xiàn)在如何開展傳承工作,又是如何做的?”
“其實,我一直在努力和堅持做著的就是傳承工作,從來沒有放棄過。我退休十多年了,我手把手教出來的學(xué)生和徒弟不下幾百人,有的已經(jīng)成名成家,有的繼續(xù)在踏歌和音樂的道路上奮斗著。現(xiàn)在我有吃有穿,可以說,一個老頭子,除了照顧一下老伴,更多的時間就是去做一些自己愿意做,又覺得特別有意義的的事情。”字升看著前來加水的老伴,笑了笑。
據(jù)字升的老伴講,平時字升幾乎就沒有空閑的時間,他把大部分時間花在了彝族舞蹈及歌曲的搜集、整理和創(chuàng)作上。當然,在農(nóng)忙時節(jié),看到兒女們忙不過來的時候,字升也會前去幫助兒女們忙點田地里的農(nóng)活。
要是遇到縣里有重要演出,還少不了請他到場指點一番。多年來,字升還不停地到四鄉(xiāng)八里義務(wù)輔導(dǎo)一些村民學(xué)習踏歌和其他表演活動,有時候還參加組織村里的、鄉(xiāng)里踏歌隊到各村各寨演出。
“巍山的民族民間音樂是一筆彌足珍貴的文化遺產(chǎn),發(fā)掘整理這一寶藏,責無旁貸的是我們有過親身經(jīng)歷的,并且從事音樂工作的人應(yīng)做的事情。把它整理出來,獻給當年共同奔赴廣闊天地的兄弟姐妹:更要留給后人,讓后人能了解上一代人所經(jīng)歷過的劫難,珍惜今日這來之不易的盛世。”字升拍了拍凳子上的那一疊厚厚的資料說道。
鑒于字升在保護和傳承民族民間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方面做出的突出貢獻,2010年,他獲評云南省省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傳承人。有了省級非物質(zhì)文化傳承人的頭銜和榮耀,但字升并不滿足,他決心要用余生把巍山民間的山歌繼續(xù)收集整理和傳承下去。
采訪結(jié)束的時候,字升拉著我的手,用夾雜著彝族韻味的漢語說道:“其實我只是一個做著彝族民歌收集整理工作的基層普通文化工作者,這些民歌不應(yīng)悄然消逝,巍山民歌中一些優(yōu)秀的作品將當之無愧地成為大理民歌寶庫中的經(jīng)典之作,我為之所花費的心血是值得的。”
這句看似尋常的話,卻給了我前所未有的力量,感染著我,激勵著我。生活在大干世界的我們,誰,又不是蕓蕓眾生中普通的一員呢?與民間音樂結(jié)緣的幾十年里,收集、整理、翻譯、創(chuàng)作民歌已成為字升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他眼中,這些民歌都是一顆顆閃亮的珍珠。
我想,字升一定會有許多知音的。
編輯手記:
在中國,民族民間文化是“下層文化”的最大代表,千百年來,人民大眾用口頭方式創(chuàng)作它、傳播它,使它成為一座當之無愧的民族文化“豐碑”。很多民族民間文化是農(nóng)耕時代的產(chǎn)物,本來能夠保存下來的就很少,而現(xiàn)代社會的飛速發(fā)展,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使很多深居山野的民族民間文化處于瀕危狀態(tài),很多珍貴獨特的文化形式都在默默地消失。本期選取了巍山縣省級非物質(zhì)文化傳承人,云藝首批音樂科班畢業(yè)生字異,通過介紹他幾十年的收集、整理、記錄、創(chuàng)作傳承和保護民族民間傳統(tǒng)音樂文化的方式,讓更多的人了解民族民間音樂保護的現(xiàn)狀,旨在呼吁更多的人們關(guān)注我們的“下層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