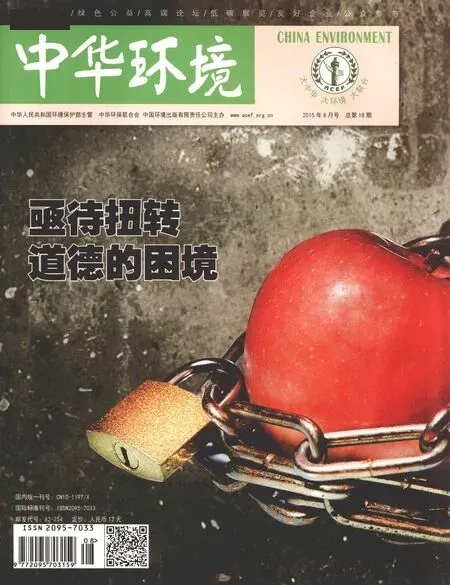荒廢湖泊該不該填?
馮應馨
7月23日,新法實施后北京市首例環境公益訴訟正式立案。因違規開發湖泊濕地,民間環保組織自然之友將北京市都市芳園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北京九欣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告上法庭。

售樓處還貼著當初的宣傳海報,突出的“清水”二字格外顯眼。
穿過半截塔村口集市此起彼伏的叫賣聲,西行約300米,就來到了事件中心的都市芳園小區。碩大的風光花壇和看似規范的安保門禁與塵土飛揚的村郊公路形成鮮明對比。小區內,主路西側拉起的黃色警戒線首先引起記者的注意。一道約2米深、1米寬的長溝順林蔭路延伸,下有已鋪設完成的天然氣管道,但還未填埋。
記者沿警戒線走進一塊已建好的別墅區域。在兩棟小樓間枝繁葉茂的花園后,空曠的沙土地突兀地充當著背景。果不其然,這大片的沙土便是傳說中的清水湖。這是一片類似“工”字的區域。記者所在剛好處于“豎”的中腰,是一塊東西向狹長地帶。目測南北兩岸約20米寬,東西相距上百米。東西兩端各連接一塊更加寬廣的區域。整個“湖區”約有200畝。
目之所及,“湖區”大都已被黃色沙土覆蓋,只零星長起幾簇野草,低洼地塊還積著近日的雨水。黑色鐵柵欄上依然掛著“禁止下湖”紅色標牌。沿“湖”一周,錯落排布著各式的紅頂獨棟別墅。可能是剛過中午,記者并沒有看到什么居民,這片區域更顯冷清。
“在家門口就能看到幾百畝波光粼粼的大湖,數百只大小野鴨,還有數位悠閑的垂釣人,這是人與自然與動物和諧相處的典范。”
“當湖水干涸、野鴨飛走,我們除了惋惜,只有接受。如今,湖區長滿了蘆葦和大樹,春天生機勃勃,夏日蛙聲陣陣,也不失為一種風景,尤其是秋冬季節,不管外面狂風如何肆虐,但湖區都是溫暖如春,老人和小孩們可以在湖區玩樂曬太陽。”
這些內容,來自小區業主郭文龍于今年4月寫給北京市昌平區區長張燕友的信。

鐵柵欄上依然掛著“禁止下湖”的標牌,警示居民。
濕地改造誰有權
既然是風光獨好的湖區濕地,又為什么會遭到填埋的命運?
記者調查了解到,之前湖區確實有水,但近年來基本都處于干涸狀態,湖心常年被荒草等植被覆蓋。
借購房之名,記者向小區物業管理處咨詢填湖事宜。九欣物業工作人員給出的答復是,湖區荒蕪,計劃改造成公園綠地,由于近日下雨暫時停工。至于綠地改造的決定,則是開發商做出的。
隨后,記者來到都市芳園開發商設置在小區南門外的售樓處,工作人員同樣給出了地下水位下降導致湖泊干涸的說法。售樓處的墻上還掛著當初的宣傳海報:陽光下紅頂小別墅坐落于波光粼粼水邊,突出的“清水”二字格外顯眼。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這幅圖來自于當初的實景拍攝。同時他也證實了改造公園的說法,稱“總比荒著強”。
資料顯示,都市芳園開發商曾于2014年10月21日張貼《通知》,決定將小區湖面進行平整綠化,并于次日開始進行填埋作業。
其后,部分小區小主表示反對,并多次張貼橫幅制止。

售樓處拍攝到的小區沙盤,湖泊濕地顯示為藍色“工”字區。

8月1日晚9點從衛星地圖上看到的湖區現狀。中心“工”字為湖區。
“……渣土車仍然我行我素強行撞入,兩次發生不明身份人員毆打業主(有錄像,有派出所出警記錄),多次有不明身份人員在小區游蕩,上門威脅滋擾維權業主(均有錄音錄像)……”
“小區門口卻頻繁出現無牌照警車、遮擋牌照的警用摩托車,狐假虎威,還有光頭壯漢在小區游蕩,極盡所能威脅。”
這是郭文龍信中的描述。
記者采訪發現,業主對于湖區填埋的態度并不一致,也有的表示贊成。
根據《物權法》第七十三條,“建筑區劃內的綠地,屬于業主共有,但屬于城鎮公共綠地或者明示屬于個人的除外”。據了解,小區內的湖泊資源歸小區業主共同所有,按所購買房產面積享有相關比例。如果需要改變用途,應當提請業主大會討論決定同意后,依法辦理有關手續。
第三方機構介入
200多畝的湖區濕地究竟是應該保持荒蕪的自然狀態,還是應該合理規劃為公園綠地?
自然之友的公益律師馬榮真認為:“填湖工程作為具有環境影響的建設項目,首先應該經過環境影響評價,其次應該經過業主同意。”
“這片濕地是小區及周邊地區的天然 “綠肺”,生態服務功能豐富,不僅景色宜人,適合休閑觀光,還能涵養水源、凈化水質、調節小氣候、維護生物多樣性。此外,都市芳園小區所處地勢比周邊區域低洼,且無雨水外排系統,小區內的濕地承擔著雨水蓄集和排出的作用,對防洪排澇起著十 分重要的作用;一旦湖面被填、排水不暢,在天降暴雨之際,將威脅 周邊眾多居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這是起訴狀中,自然之友方面所陳列的事由。
為此,記者咨詢了國際生態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百煉教授。生態學上一般堅持“有水則清,無水則青”的原則,湖泊濕地的改造要根據其本身承載量、地形、地貌、地勢整個結構統籌安排,還要根據歷史數據考慮,萬一遭遇百年不遇的洪水要如何應對。李百煉強調:“即便要將其改造為公園的形式,湖泊與濕地的功能也應該保留相當一部分。”
7月23日,自然之友以固體廢物污染責任糾紛為由,向北京市都市芳園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和北京市九欣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發起公益訴訟,要求二被告:停止侵害,不得繼續傾倒渣土等固體廢物,不得繼續破壞原有生態;同時,要求其承擔生態環境修復費用,包括制定、實施修復方案的費用和監測、監管等費用,共 950 萬元,用于原地恢復當地植被以及修復生態服務功能;此外,被告還需賠償涉案湖泊區域植物群落、 濕地生態受到損害至恢復原狀期間服務功能損失費,用于北京市昌平區濕地保護等公益事業。

之前的湖泊濕地已被填埋。同時,填湖行為遭到部分業主的反對。
“我們關注的是填湖行為對環境和生態本身的影響,也即‘環境公共利益’”馬榮真表示。
目前,該案已由北京市第四中級人民法院受理。
公益訴訟從《環保法》修訂到新法實施,一直都是業內人士關注的焦點。2013年12月1日,由中華環保聯合會主辦的“中華環保民間組織可持續發展年會”,恰逢《環保法》修訂條草案常委會三審階段展開。會議討論環節,最被各家NGO義憤填膺的便是公益訴訟主體不適格。
這一問題在新法實施后得到改善。隨著《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進一步出臺,目前我國共有700多家社會組織可以進入公益訴訟的渠道。
不過,雖然公益訴訟的主體范圍明顯擴大,案件數量的增長卻一直是不溫不火。最高法環境資源司法理論研究基地研究員馬勇告訴記者,截止到7月底,全國共有20起公益訴訟被各級地方法院受理,分別由9家環保組織提出。相較于700多家的適格主體,目前,不論是案件數量還是主體數量,都不算多。
由于屬地管理、NGO自身能力,以及地方保護主義等外界阻力的存在,馬勇表示:“公益訴訟會有明顯增幅,但不會有爆發式的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