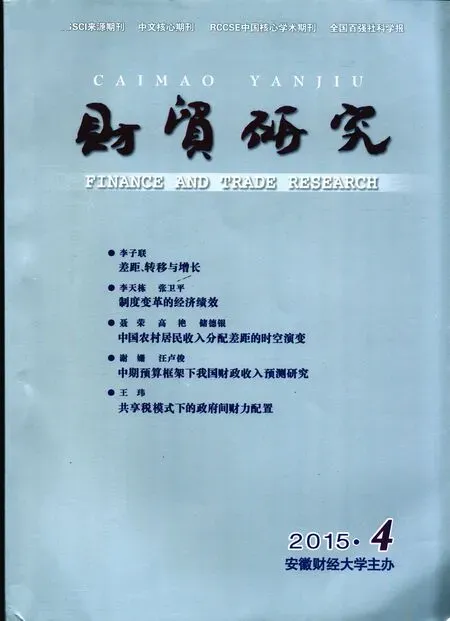制度變革的經濟績效:以加入WTO為例的實證測算
李天棟 張衛平
(復旦大學 經濟學院,上海 200433)
制度變革的經濟績效:以加入WTO為例的實證測算
李天棟張衛平
(復旦大學 經濟學院,上海 200433)
中國為加入WTO而實行的貿易專營制向普營制的制度變革對進出口及GDP的影響是測算制度變革經濟績效的重要案例。TRAMO方法可以用來客觀地分離出進出口的異常值及其規模和時點,運用Chow檢驗可以結合TRAMO方法確定的異常值的時點對制度變革的時點予以檢驗和確認。在此基礎上,以制度變革時點為界區分出不同的階段然后對制度變革前后的經濟績效提出具體的測算方法,實證測算的結果表明,中國加入WTO所進行的制度變革的經濟績效極為可觀,在2007年前后占GDP的比例高達30%以上,在美國金融危機之后,制度變革的經濟績效開始趨于減弱,中國經濟需要尋求新的發展動力。
制度變革;經濟績效;參與門檻;異常值分離;Chow檢驗
一、引言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后,大西洋貿易成為各國積累財富增強國力的重要路徑。盡管起步較晚,但憑借制度優勢,英國最終超越最先開展大西洋貿易的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國而成為從大西洋貿易中獲益最大的國家。Acemoglu等(2005)認為,英國對大西洋貿易實行的是只要備案就可參與的貿易普營制,而歐陸各國均實行需要國王特許狀的貿易專營制,此為英國最終超越先行諸國的決定性因素。
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在世紀之交我國經歷了由中央政府主導的從貿易專營制向貿易普營制的制度轉變。隨后,我國以超乎尋常的高速增長,使經濟總量在20余年的時間內攀升至世界第二位。貿易制度的普營制變革與此后我國的經濟奇跡之間的先后順序僅僅是巧合還是存在一定的因果關系?如果存在因果關系,那么該制度變革的經濟績效又是怎樣的?明確解答上述問題不僅有助于理解我國的經濟奇跡,而且對未來制度變革的方向和路徑亦有重要啟發。
毫無疑問,我國貿易制度的普營制變革是在中央政府的主導之下進行的。這符合制度變革的基本邏輯。問題是,國家推動的制度變革并非一定會出現正面經濟效果,歷史上失敗的制度變革俯拾皆是。因此,不能通過制度變革本身而應該根據其經濟后果對制度變革進行評價,從而倒推和歸納對經濟有正面促進作用的制度變革所應該具備的特征,這也是本文實證測算我國普營制變革績效的初衷之一。
對于制度變革的經濟績效的測算,兩種做法較常見:一是用結構性數據進行構造,如非國有部門產出占總產出的比例(賀菊煌,1998)、工業化市場化國際化指數(宋德勇,1999)等,然而這種類型指標的最大問題是無法辨清數據與制度變革的因果關系。二是通過構造指數的方法,目前主要有五種類型的指數:反映政治自由度的Gastil指數(Kormendi and Meguire,1985;Scully,1988;Barro,1996)、產權安全度指標(Knack and Keefer,1995;Easterly and Levine,1996)、經濟自由化指數(Ali,1997;Dawson,1998;Easton and Walker,1997)、產權發展指數(Norton,1998;Hall and Jones,1999;Chong and Calderon,2000;Acemoglu,et al,2001)以及總治理指數(Kaufman,et al,1999)。這種做法的最大問題在于指數的客觀性會有問題,因為這些指數通常是借助問卷或者主觀判斷等形式給出的。
本文采用TRAMO分離異常值方法和Chow斷點檢驗相互印證的方法確定制度變革的經濟時點。以TRAMO分離異常值方法可以識別具有真實經濟效果的制度變革,具有客觀性;以Chow斷點檢驗可以對TRAMO方法識別出來的制度變革發揮作用的時點進行數據結構是否存在斷點進行判別,兩種方法的相互對照有助于強化識別出來的制度變革的客觀性和真實性。以此為據區分兩個階段,通過對比便可以測算出制度變革的經濟績效。
二、研究背景
表1是各個不同階段我國經濟年度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的統計指標。從平均值和標準差來看:1992—1999年間盡管經濟平均增速最高,但通脹率的均值也最高,且增長的穩定性也較差;2000—2008年間經濟平均增速保持次高的同時穩定性也非常好;2009—2013年間經濟的平穩性最好,但平均增速最低,是后美國金融危機時代宏觀穩定政策的反映。

表1 我國分階段的經濟增速和通貨膨脹率
我國2000—2008年間經濟穩定高增長的起因和動力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2000年之后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貿易規模大幅增長,對該現象最普遍的解釋是要素價格優勢,或者更具體的說是人口紅利的作用。然而該解釋的說服力并不是很強,因為我國的要素價格優勢一直存在,1992年之前的勞動力成本比2000年之后更便宜,人口紅利更大,但彼時既不見我國國際貿易規模增長,也不見外匯儲備的增長,國家甚至要通過強制結售匯制度獲得外匯。
實際上,我國在世紀之交為加入WTO而實行的貿易專營制(進出口自營權需要審批,沒有進出口自營權的生產企業需要通過貿易代理公司進行對外貿易)向貿易普營制(進出口自營權不需要審批,只需備案即可獲得)的轉變*1984年國務院正式將貿易代理制(專營)確定為我國對外貿易的基本形式。1999年之前,除公有制的貿易代理公司外,部分國有企業和所有的外商投資公司有自營進出口權,私營企業沒有進出口自營權,這與WTO的規定存在沖突。談判中,我國承諾在加入WTO 后三年內完全實現外貿經營的依法登記制。1999年開始向第一批20家私營生產企業授予自營進出口權,2000年上半年第二批授予179家,下半年干脆直接取消自營進出口權審批制,改為登記制;隨后,2001年7月外經貿部發布《關于進出口經營資格管理的有關規定》,我國從審批制徹底轉變為登記制,提前實現了貿易專營制向普營制的轉變。盡管直到2008年1月29號,商務部才明文徹底廢止1991年8月29號開始實施的《關于對外貿易代理制的暫行規定》,貿易代理制才在法律上結束其歷史使命。然而,《關于進出口經營資格管理的有關規定》發布之后,貿易代理制即使在名義上依然存在,其地位和作用已經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是貿易規模大幅增長的主要原因和根本動力,因為加入WTO及配套的貿易專營制向普營制的變革使參與國際貿易的成本大幅降低,同時也去除了資本規模和其它因素的限制,解放了企業家的創造力,使經濟穩定高速增長。
與專營制相比,貿易普營制有兩大優勢:
一是從事經營活動不再需要向國王、政府等權力機構付出額外成本,因而在該領域的投資就會增加。設從事貿易獲得的總收益為R,成本包括兩部分:從事經營活動本身的成本C1,為獲得開展該項業務的資格而額外付出的成本C2,則凈收益為NR=R-C1-C2,最優化條件為MR=MC1+MC2。當C2下降,MC2必然減小甚至為負數,則投資要求的邊際收益MR也可以隨之下降,投資規模必然隨之增加。這個可以認為是貿易制度的成本效應。
二是參與門檻降低,專營制下有企業家精神但缺少資格和資本的人有機會在普營制下脫穎而出。設有企業家精神的人成功的概率為pH,無企業家精神的人成功的概率為pL,pH>pL;經營成功的總收益率為RH,失敗的總收益率為RL,RL<1

圖1 出口總額中國有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和其它類型企業占比的變化
通過出口總額中不同性質企業占比的變化也能看出貿易制度變化的影響,圖1是出口總額中國有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和其它類型企業占比的變化。從趨勢上可以看出,國有企業出口占比持續下降的同時其它類型企業出口占比持續上升,而后者上升趨勢斜率大體上發生在2000年前后,與貿易制度普營制變革非常契合。
三、制度變革時點的確定:TRAMO異常值分離與Chow斷點檢驗
現代數據分析技術的發展提供了一種新的分析數據結構性變化的思路,即TRAMO分離異常值的方法。TRAMO(Time Series Regression with ARIMA Noise, Missing Observations and Outliers)的主要功能是對遵循ARIMA過程的時間序列進行參數估計和預測,發現其中的缺失值、異常值、日歷效應和干預效應。通過控制參數取值,TRAMO可以單獨用于分離時間序列中的異常值,即發生于某一時刻的暫時或永久的水平變動。利用TRAMO的異常值分析功能,可以偵測異常值的位置并估計其形式和影響程度*關于TRAMO的基本原理和程序,參見:http://www.bde.es/bde/es/secciones/servicios/Profesionales/Programas_estadi/Programas_estad_d9fa7f3710fd821.html。。因此,可以先用TRAMO方法通過數據分離識別制度變革的具體時點,然后用Chow檢驗對TRAMO辨別的時點予以確認,這樣就可以讓數據自己展示其因制度變革而產生的變化及其衍生出來的經濟績效,因為只要能夠真實地甄別出數據隨時間而產生的變化,它就是最客觀也最真實可信的。
本文先運用TRAMO分離異常值方法對進出口數據進行分離,初步確定制度變革發生的時點;然后以Chow斷點檢驗方法對TRAMO方法確定的時間點予以驗證。
(一)應用TRAMO對進出口的異常值分離
TRAMO能識別只影響一期的異常值(AO,Additive Outliers)、影響不斷衰減的異常值(TC,Transitory Changes)和影響持久的異常值(LS,Level Shifts)*LS(Level Shift)的直譯是“水平移動”,該類型異常值意味著一旦出現就會持續較長時間,并且在存續期限內既不會像AO一期后消失,也不會像TC那樣逐漸衰減,而是一直以同樣的比例持續。。其中,LS類型的異常值識別最具意義。只要LS類型的異常值能夠被識別出來,通常就意味著經濟趨勢的強化或逆轉,因此可以稱之為結構性變化,它們一般是由比較重大的事件、改革或重大的政策變化所致。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結構性變化都能被識別出來。因為結構性變化的影響需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慢慢體現出來,存在時滯性;同時,當判定指標與結構性變化之間的傳導路徑比較長時,其它因素的影響無法控制,可能會抵消結構性變化的效應。因此,一旦LS類型的異常值能被TRAMO方法識別出來,其對應的結構性變化通常是比較重大的。
之所以將進出口作為分析的對象,是因為其與外貿領域制度變革的傳導路徑最短,可以盡可能地避免其它因素的影響。
選擇進出口的季度數據對1992年到2012年進行分離,結果參見表2。

表2 TRAMO分離的出口和進口(季度)異常值及其類型
從異常值分離的結果可見,出口有四個LS類型的異常值:1994年2季度、2000年1季度、2008年4季度和2009年1季度,分別對應人民幣匯率并軌、貿易專營制變為普營制、美國金融危機(后兩個皆是),出口額(原始數據)相對于原來的趨勢(分離之后的數據)分別增長了15.42%、28.16%、-19.59%和-26.04%。
進口只有1個LS類型的異常值,發生在1999年2季度,是對貿易專營制轉化為貿易普營制的提前反應,進口額(原始數據)相對于原來的趨勢(分離之后的數據)增長了20.51%*對比我國進口產品與出口產品的結構,可以發現我國進口最多的產品是工業半制成品或自然資源,而出口最多的產品是工業制成品。從產品結構角度看,我國大部分進口品是用于再生產的資源、零部件等生產要素。1994年人民幣匯率并軌使出口規模大幅度擴張,然而當時我國經濟規模比較小,對生產要素進口的需求相對較低,因此進口數據并沒有像出口數據那樣出現LS類型的異常值;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對我國的進口規模也沒有造成LS類型的異常值,可能是因為我國政府推出的4萬億刺激計劃拉高了對進口商品的需求。。
根據對進出口異常值的分離,人民幣匯率并軌以及貿易專營制向貿易普營制轉變的經濟績效是非常顯著的。這兩大制度變革使得我國的出口規模增長了47.92%,既提升了我國參與太平洋貿易的程度,也加快了我國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進度,還締造了我國世界工廠的地位,是最近20年我國經濟高增長的重要動力。
(二)Chow的結構斷點檢驗
為進一步核實制度變革是否造成數據的結構性變化,有必要對TRAMO異常值分離確定的制度變革的時間點進行Chow斷點檢驗。相對于TRAMO方法,Chow檢驗需要主觀指定結構變化的具體時點。TRAMO異常值分離的結果與Chow檢驗確認的時間相互印證確定的制度變革的時點具有更強的可信性,Chow檢驗結果參見表3。從中可見,2000年和2009年我國的進出口數據的確發生了結構性變化,與TRAMO分離異常值方法得到的結論相互印證,并且結合具體發生的對外貿易制度由專營制向普營制的制度變革,可以認為2000年是我國貿易制度發生重大變革的時間節點。因此,有理由相信,2000年前后我國經濟的表現差異有相當的部分源于制度變革。

表3 進出口原始數據的Chow斷點檢驗
四、制度變革的經濟績效測算
(一)制度變革經濟績效測算:方法和步驟
制度變革發生后,GDP可以分解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沿著原有趨勢增長的GDPO(上標O是Original的縮寫,下同),可進一步分解為CO、IO和CAO;第二部分是制度變革新生的GDPRS(上標RS是Regime Shift的縮寫,下同),可進一步分解為CRS、IRS和CARS。出口擴張的背后必然是相應的投資增加,同時出口部門擴張會吸引更多勞動力進入出口部門,工資增加必然會使消費增加,分解后的GDP的構成為:
制度變革的經濟績效以制度變革造成的新增GDP與現實的GDP之比表示,可稱之為制度變革的經濟貢獻度:
在確定制度變革的具體時點后,通過下面三步測算制度變革對產出的貢獻。第一步,假設進出口都是帶有時間趨勢的AR(1)過程,對甄別出來的兩個時間段分別進行回歸,確定其時間趨勢,并對其殘差進行單位根檢驗,以核實它們的穩定性從而AR(1)假設的合理性;第二步,以制度變革之前的時間段得到的回歸方程對后面的時間段進行預測,得出制度變革未發生情況下的數據序列,兩者之差就是制度變革對進出口的影響*之所以采用這種方法估算制度變革對進出口的影響而不是用TRAMO分離出來的時間序列直接計算,是因為TRAMO的估算是以制度變革之前的時間序列作為標準。當某一項制度變遷之后又出現另外一項重大變化,后者變化的影響是以前者已經形成的數據序列為基礎進行估算的,這就無法準確反映制度變革的影響。;第三步,假設生產函數是CD形式的,以此測算制度變革形成的出口需要的投資以及對應的消費,然后加總并與實際形成的名義GDP進行對比,最終得出制度變革的經濟績效*從異常值分離的結果看,貿易制度的普營制改革使進口和出口同步增加。進口品可以分為兩類:用于消費的進口品和用于生產的進口品。根據GDP核算原理,不管是用于消費的進口還是用于生產的中間品進口都會形成外國的GDP。作為生產中間品的進口對GDP的貢獻取決于生產出來的最終產品是否是出口產品,若是出口產品,則其對GDP的貢獻體現在與出口相關的計算之中,若不是用于出口,而是用于本國居民的消費,則需要分離出這一部分進口的數據,但當前缺少相應的結構性數據以完成該分離。 如果考慮到用于生產的進口品,則貿易制度變革對GDP的貢獻還會更大。本文的測算是保守的。。
(二)制度變革經濟績效測算的過程
1.測算制度變革造成的凈出口增加

表4 不同時間段進出口的時間趨勢:AR(1)回歸的結果
根據表4的殘差單位根檢驗結果,這些AR(1)過程都不存在單位根,即都是穩定的帶時間趨勢的AR(1)過程。就時間趨勢的系數而言,它們的確差異顯著。對于出口來說,1994—1999年間時間趨勢的系數僅為0.033,2000—2008年間為0.14,金融危機最嚴重的階段出口顯著下滑之后又快速恢復,恢復速度即時間趨勢項的系數高達1.346。進口的回歸結果類似,在199401到199903間為0.033,在199904到200812間為0.099,金融危機之后的恢復速度與出口同樣快速,達到1.318。
既然TRAMO異常值分析和Chow檢驗都認可1999年實行的貿易專營制向貿易普營制的制度變革造成進出口數據在2000年前后出現了重大的結構性變化。以TRAMO得到的時間作為分界點將進出口數據分成前后兩段,出口數據區分為199401—199912和200001和201212,進口數據區分為199401—199903和199904—201212。先對進出口的前一段進行回歸得到其時間趨勢,然后以它為標準得出第二個時間段進出口的預測值(實際值與預測值分別參見圖2-1和圖2-2所示),最后用現實的進出口值減去進出口的預測值就可得到進出口的新增額。

圖2-1 出口的原始值與預測值

圖2-2 進口的原始值與預測值
2.測算新增出口對應的新增投資
3.測算新增凈收入對應的新增消費
(三)測算結果及分析
經過上述計算后可得出制度變革對經濟的貢獻度,其結果繪制在圖3中。鑒于GDP統計的頻率最低是季度,我們將通過上述方法計算得出的制度變革之后的新增GDP也轉換為季度數據。
從圖3中可以觀察得到如下現象:
(1)為加入WTO而實行的貿易專營制向貿易普營制的制度變革的經濟貢獻度經歷了持續上升的過程,也是要素向對外貿易部門的再配置過程。因為制度變革使對外貿易的交易費用降低,對外貿易部門更有利可圖。同時,持續上升表明制度變革具有累積效應。

圖3 加入WTO及從貿易專營制向普營制轉變對經濟的貢獻度
(2)制度變革對經濟的貢獻度是有極限的。制度變革的經濟貢獻度在2007年上半年達到最高,約為33%,此后由于美國金融危機的影響,進出口都急劇萎縮,其貢獻度也急劇下降。之后隨著世界各國廣泛采取經濟刺激措施,我國進出口又快速恢復。然而,進出口對經濟的貢獻度再也沒有回到2007年的最高點。
(3)制度變革并非完全的“免費午餐”。對外貿易的制度變革在為我國經濟提供強大發展動力的同時,也因深度融入世界經濟而隱藏著巨大的且極易受到外部經濟波動影響的風險。從圖3可見,當外部經濟出現動蕩,我國進出口規模也會大幅波動,并不可避免地造成經濟動蕩。制度變革對經濟的貢獻度在2008年末2009年初形成一個極深的凹口(圖中已用橢圓圈出),這固然表明我國進出口的恢復能力非常強,同時也意味著我國經濟的穩定性因我國經濟深度融入世界經濟而降低。
盡管對外貿易制度變革降低了我國經濟的穩定性,但對經濟的促進作用卻是主導性的,是我國在新世紀實現經濟快速發展的根本原因。
五、小結
本文通過TRAMO異常值分離方法和Chow檢驗,得出我國為加入WTO而實行的從貿易專營制向普營制的制度變革是我國經濟奇跡的根源。通過具體測算,結論如下:
(1)制度變革的要義是降低參與的成本和門檻。只要某一領域的參與成本和門檻降低,原來因資格所限而不能參與的人就可以進入,而要素數量的增大必定會擴大該領域的規模。
(2)TRAMO異常值分離的結果顯示,為加入WTO而實行的貿易專營制向普營制的轉變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國貿易的規模和格局,Chow檢驗也確認數據結構的確因貿易制度變革而出現了斷點。
(3)我國的對外貿易由專營制向普營制的制度變革對我國經濟的貢獻度持續上升,并在2007年達到最高點,約為33%,此后因為美國金融危機而出現雪崩式下降,但又因各國相繼采取擴張性政策而快速回升。目前,其對經濟的貢獻度保持在10%~15%之間。
我國對外貿易制度改革的成功經驗表明,降低參與的成本和門檻是制度變革的要義。只要國家能夠提供具有高度可信性的、能夠降低參與成本和參與門檻的制度架構,企業自會在利潤導向下最優化其要素配置,促進經濟發展。這為我國頂層設計和制度建構提供了極有現實意義的鏡鑒。
白重恩,錢震杰. 2009a. 國民收入的要素分配: 統計數據背后的故事[J]. 經濟研究(3):27-41.
白重恩,錢震杰. 2009b. 誰在擠占居民的收入[J]. 中國社會科學(5):99-114.
賀菊煌. 1998. 中國經濟增長的兩個主要因素[M]//中國經濟增長與可持續發展.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羅長遠,張軍. 2009. 經濟發展中的勞動收入占比: 基于中國產業數據的實證研究[J]. 中國社會科學(4):65-79.
單豪杰. 2008. 中國資本存量K的再估計:1952—2006年[J].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10):17-31.
宋德勇. 1999. 工業化、市場化、國際化與中國的經濟增長:對“中國奇跡”的一種解釋 [J]. 華中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73-75,82.
張軍,吳桂英,張吉鵬. 2004. 中國省際物質資本存量估算:1952—2000[J]. 經濟研究(10):35-44.
ACEMOGLU D, JOHNSON S, ROBINSON A. 2005. Institutions as a fundamental cause of long-run growth [J].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1):385-472.
ALI A M. 1997. Economic freedom, democracy and growth [J]. Journal of Private Enterprise, (Fall):1-20.
BARRO R J. 1996. Democracy and growth [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1):1-27.
CHONG A, CALDERON C. 2000. On the causality and feedback between institutional measures and economic growth [J]. Economics and Politics, 12(1):69-81.
DAWSON W. 1998. Institutions, investment and growth: new cross-country and panel data evidence [J]. Economic Inquiry, 36(4):603-619.
EASTERLY W, LEVINE R. 1995. Africa’s growth tragedy [R].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1503.
EASTON S T, WALKER M A. 1997. Income, growth, and economic freedom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7(2):328-332.
HALL R E, JONES C I. 1999. Why do some countries produce so much more output per worker than others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4(1):83-116.
KAUFMAN D, KRAAY A, ZOIDO-LOBATON P. 1999. Aggregating governance indicators [R].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2195.
KNACK S, KEEFER P. 1995.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ross-country tests using alternative institutional measures [J]. Economics and Politics, 7(3):207-227.
KORMENDI R C, MEGUIRE P G.1985. Macro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growth: cross-country evidence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6(2):141-163.
NORTH D C. 1973.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M]. [S.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ORTON S W. 1998. Poverty, property rights, and human well-being: a cross-national study [J]. Cato Journal, 18(2):233-245.
SCULLY G W. 1988.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6(3):652-662.
(責任編輯彭江)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Institutional Change:Empirical Estimation after China′s Accession to WTO
LI TianDongZHANG WeiPing
(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The impact of system reform, transferred from trade franchise to non-licensed one for China′s accession to WTO, on import and export and GDP, is an important case to estimat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institution change. Outliers and their time points are separated by TRAMO method, and then the Chow test is used to verify and validate time point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s. After that, different stages are identified by institution change point and an estimation method is proposed to estimate economic performance before and after the institution change. The estimation shows that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the institution change after China′s accession to WTO is rather great. It accounts for 30% of GDP around 2007, but tends to decrease after American finance crisis. China′s economy needs new motive force for development.
institutional change; economic performance; barriers of participation; separation of outliers; Chow test;
2014-12-25
李天棟(1975--),男,山東青島人,經濟學博士,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
張衛平(1979--),男,山東煙臺人,經濟學博士,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
上海哲學社會科學資助項目“我國雙順差的形成機理:不完全產權視角的研究”(2013BJL002);廣義虛擬經濟辦公室資助研究項目“廣義虛擬經濟視角下我國科技發展的路徑研究”(GX2012-1006)。
F061.2
A
1001-6260(2015)04-0012-08
財貿研究20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