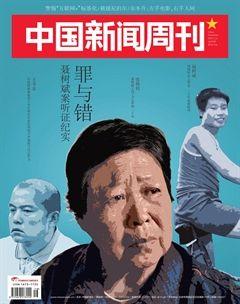微商 or“危商”
薛茜文 高敏
你永遠不知道微信朋友圈里誰會是下一個微商。
然而,這幾天,微商正成為眾矢之的。一個自稱年收入7位數的90后網絡紅人賣有毒面膜的新聞讓更多的公眾開始關注朋友圈里的微商。而購買微商面膜中毒的案例也連見報端,中毒輕則過敏,重則血液鉛含量超標,使用過的孕婦甚至有流產的風險。
當電商搭上社交平臺的順風車,似乎激發了人們潛在的謀利欲望,在“動動手指就賺錢”的宣傳之下,微商利用熟人網絡,規模裂變式膨脹,從起初宣傳的面膜傳奇到如今的群“膜”亂舞,微商潛藏的風險與隱憂也迅速顯露出來。
瘋狂的網上“圈地”
微商,一般指個人憑借互聯網社交媒體,發布信息,以銷售商品為目標的小型個體行為。幾乎所有的微商品牌都是采用代理模式,通過在全國招不同級別的代理,授權各級代理商分銷產品,實現盈利。
2012年底微商開始走入公眾視線,它最初只是通過微信朋友圈賣水果、母嬰以及零食等產品的初級分享平臺。
2014年3月份,微商開始嶄露頭角,以某品牌為代表的面膜在朋友圈里瘋傳,各種賣家在賣面膜的同時,也會“不經意”的曬單,公布銷售記錄和銷售額,類似“一天賺了一萬多”的微信開始充斥在朋友圈中,而動動手指可賺錢,實現創業夢的理念像病毒一樣在社交平臺上傳播。
在國家鼓勵創業的大背景之下,以“創業”為噱頭的微商在互聯網社交平臺大行其道。大量企業推出微商品牌,產品以面膜為主。2014年可以算作是微商的1.0時代,一些微商“本土”品牌迅速成長,“十五天就可以打造一個品牌,” 中國微商產業聯盟籌備委員會主任陳其勝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種速度在傳統企業和傳統渠道內是不可能出現的。
這種速度亦有數據支持。據易觀智庫發布的《2014年微信購物發展白皮書》顯示,2014年中國移動購物用戶規模突破3億,移動購物的交易規模接近10萬億,增長率達到270%。易觀國際數據統計,目前我國微商從業者已達到數千萬人。微播易創始人徐揚在中國(義烏)首屆移動互聯高峰論壇上也曾提出,阿里巴巴做到2千億交易額需要8年,微商只用一年的時間就做到了1500億。
微商短時間內的迅速擴張源于其龐大的微商代理團隊。陳其勝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所謂“微”是指:低門檻不需要成本,移動端創業不需要店面,碎片化時間不需要坐班。這些特點使得微商在短時間內積聚大量的下線代理商,各級代理商通過不斷的刷好評和曬成交單,來吸引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微商隊伍。
許多微商品牌招代理的門檻大小不一,從全國總代到個人代理,代理費從幾十萬到幾十塊不等,等級越高的代理,產品的進價就越低。許多上級代理會招很多下級代理,通過賣貨給下級代理,賺取產品進價的差價,比如進價2元的產品,賣給下級代理商是10元,中間的差價都歸上級代理所得。
微商代理團隊除了以團隊滾雪球的形式不斷壯大外,一些自媒體大咖也參與其中,有的甚至開設微商的課程,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微商。
“品牌+代理團隊+自媒體大咖,再憑借網絡社交媒體的快速傳播力,這是微商能夠以裂變的方式發展的重要原因。” 陳其勝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變味的鏈條
然而,在巨大的利益驅使下,缺乏監管的低成本運作讓這個微商鏈條開始變味。
微商品牌人氣主要來自于各級代理的宣傳,遍布全國的微商代理團隊可以在短時間內迅速炒紅一個品牌,一些三無產品,穿上“洋裝”,搖身一變成為海外品牌。
在微商圈熱銷的某面膜號稱是香港品牌,產品在瑞士研發,但是在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的備案信息上顯示,生產廠商是廣州市白云區源儂化妝品廠。
“這個面膜花了幾千塊在香港注冊牌子,之后找我們工廠做,配方都是我們工廠的。”源儂化妝品的工作人員向《中國新聞周刊》證實。
“不會再買微商的面膜了。”一位微友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她買了另一個品牌面膜用了一次后,滿臉冒痘,去醫院一查得了激素性皮炎。
低劣質量背后意味著高額的利潤。曾做過微商的一個商戶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有次收貨后,她發現產品包裝瓶子里有只蒼蠅,這讓她產生了懷疑,發現朋友賣的產品并不是臺灣生產的,而是從淘寶上直接進的貨,產地是青島,而淘寶上賣的價格比她進價便宜了一半,“我同學從我這就可以賺一半以上的差價。” 她說。
對于微商而言,并不擔心品牌形象受損。“一旦產品滯銷立馬換另一個品牌做,這種打一槍換一地方的模式,不僅危害了品牌自身的利益,也損害了微商的整個聲譽。” 雅倩微商部營銷經理魏燦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山東濟南,26歲的趙雨欣在準備發貨。微商剛展露頭角時,趙雨欣便開始嘗試這種新型銷售平臺。如今,她擁有3個微信賬號,10多個包括服裝、護膚、鞋帽、配飾等不同種類的微信群,每個群的人數少則200。圖/I C
“基本上都是玩概念、炒概念,玩死一個品牌,再造一個品牌。” 中國微商產業聯盟籌備委員會主任陳其勝認為,微商目前發展呈現的是一種“虛熱”。
不止于此。一位業內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有很多品牌的商品是找工廠代工的,微商團隊只是負責運營和炒作,這些產品的質量無法得到保障。“在廣州這樣的企業很多,在花都區的城中村,幾個老太太就可以做出一個面膜品牌。” 雅倩微商部營銷經理魏燦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這些來自不同渠道的“三無”產品在價格上也會對微商的整個市場產生一定的波動。“同一種類型的商品,代理價很低,各級代理商賣價都不統一,這種亂價也會影響到傳統的線下品牌的銷售。” 魏燦說,一些已經積累了穩定的下級代理的上級代理商,會把原有的正品換成高仿品,同樣也會給正規品牌帶來負面影響。比如看起來同一品牌的肥皂,消費者當然買那些價格便宜的。
在品牌打造過程中,虛假宣傳似乎成了“必修課”。一位微商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一些微商品牌并沒有代理層級限制和退貨機制,這樣會導致已經大量囤貨的微商,為了實現銷售,會“劍走偏鋒”用盡各種方式銷售產品,瘋狂刷屏,同時購買專業刷單團隊刷單來提高人氣和知名度。在微商刷單和刷信譽的QQ群里,各種刷單團隊明碼標價,刷單團隊可以幫助微店提高銷量、收藏以及評論的數量,根據信譽等級,價格也從一百到千元不等。
甚至微商圈看似熱銷的賬單和對話有可能都是造假的。一位曾經做過微商的網友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利用對話生成器和支付寶截圖生成工具即可造假賬單和對話。很多微商還會運用粉絲采集器的軟件,使得微信在固定時間內快速加一些陌生好友,并對好友進行管理。
如何監管
事實上,常見的騙術在微商圈似乎也找到了土壤。
有的微商在賣手機充值卡,稱花兩百元的卡綁定軟件之后,可擁有1000元的話費,聯通、電信、移動的手機號都能用,然而《中國新聞周刊》致電三家通信運營商,均表示未推出此項業務。
此外,付款后遭到微商“拉黑”也是常事。一位網友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她在朋友圈看到一個微商發的時尚衣服圖片,花了300元購買了16件春秋冬款,還沒收到貨,對方就把她“拉黑”了。后來當她告訴對方要到微博上曝光時,對方才發了幾件衣服給她,“全部都是她穿過的,毛衣上油漬都有,鏈子都是斷的。就一雙10塊錢的拖鞋是新的。”這名網友說。
微商中大多個人賣家沒有任何注冊信息,雙方交易全憑相互間的信任,沒有擔保,也無第三方平臺的保證,由此構成一片“灰色地帶”,三無產品和虛假品牌泛濫,買家買到假冒偽劣產品往往只能“吃啞巴虧”。
北京一位女士花了一千多元向做微商的朋友買了三盒面膜,但是首次使用后臉上就出現了很多小紅痘,“質量特別差,還沒有兩三塊的面膜好。”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向賣家反饋后,對方要求她先把化妝品拿到醫院檢測,但檢測時間要一周,費用需要幾千元。
如何監管微商也就迫在眉睫。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分析師莫岱青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監管主要靠微信平臺方和工商部門。微信在3月15日發布的《微信朋友圈使用規范》,明確規定對于欺詐虛假廣告、使用外掛和刷粉行為等可以進行舉報并處以封號的懲罰。但至于工商部門的監管,由于個人微商沒有注冊信息,實際很難實施監管。
“消費者向騰訊投訴最有效。”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特約高級研究員劉春泉對《中國新聞周刊》 分析,也可以向消協投訴。
中國微商產業聯盟籌備委員會主任陳其勝建議,通過對會員企業進行誠信引導,把代理等級限制在三級以內,企業建立退貨機制。目前正在籌備中的“中國微商產品可追溯信息查驗標識”平臺,對微商的產品信息進行登記,消費者通過檢驗平臺可以辨別產品質量是否合格。
陳其勝說,他們正在收集微商不規范行為的數據,并將在今年6月公布中國微商誠信排行榜。“微商是人人都可以選擇的創業渠道,希望大家客觀看待,不要因為初期的亂象而一棒子打死。”
一些微商品牌也開始提高服務意識,限制代理層級。在莫岱青看來,隨著大的電商進駐微商,用戶理性地選擇更正規、更有保障的微商產品,一定程度上會扭轉個人微商的種種亂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