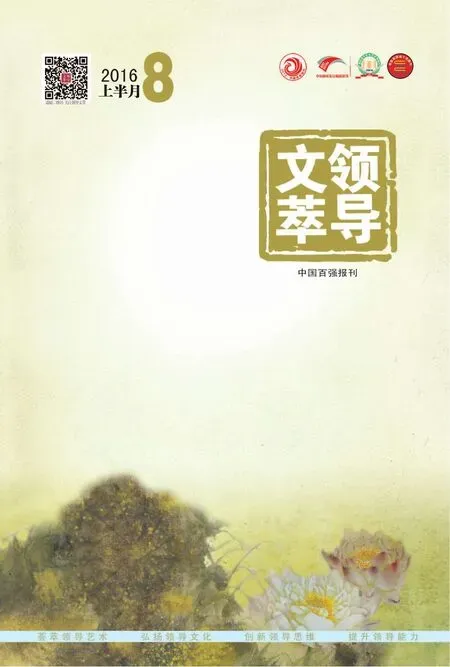美國如何建立對華核威懾力?
□美國《聯合部隊季刊》雜志文章 吳溦編譯
美國如何建立對華核威懾力?
□美國《聯合部隊季刊》雜志文章 吳溦編譯
由美國國防大學主辦的2014年第八屆美國國防部長論文競賽,日前揭曉,美國國家戰爭學院學員大衛·福爾曼憑借《切莫低估中國核威懾力》一文獲得第一名。文章以“核威懾”為切入點,從和平時期、危機或沖突發生期以及核戰爭爆發期3個階段,分析了美國對中國實施核威懾的基本原則,并且,針對美國如何增強核威懾力提出若干建議。在美國就朝鮮、伊朗“發展核武器”不斷揚言制裁的當下,這篇論文的獲獎,再聯想到截至2014年11月,美國仍遲遲不批準《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誰在假裁核已不言自明。
和平時期的核威懾
在和平時期,以非武力的形式達到政治訴求是一個國家實施核威懾的主要目標。這一時期影響核威懾力的因素有三個:一是“聲明政策”。它是由總統、國防部長或政府其他決策人物公開宣布的涉核政策,是一種代表國家意志的強有力的政治工具。二是核威懾力的信度。它是指核武器運載系統和核彈頭在實際應用中展現的真實能力。三是國家非核武器的戰斗力。它是指一個國家在不使用核武器的情況下,僅僅通過傳統手段達成軍事目的的能力。把握好這三個因素,對核威懾力的分析才會準確。
核威懾力的可信度。強大的核威懾力來源于展現出的軍事意圖和軍事實力。軍事意圖可以從“聲明政策”中看出,軍事實力則通過運載系統和核彈頭得以體現。美國仍傾力打造戰略核力量的“三位一體”架構——洲際彈道導彈、潛射彈道導彈和戰略轟炸機,費盡心思保證核武器展現出理想的威懾力。在運載系統方面,美國空、海軍每年共發射5枚不攜帶武器的導彈,這些導彈的發射成功讓美國對其運載系統充滿信心。然而,核彈頭的研發并不是那樣走運。美國上一次真實引爆核彈是1992年。上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開啟了核武器儲備管理計劃。然而,僅僅依靠計算機模擬進行核彈維護,并不能表明核彈的實戰能力是否符合標準。正如國家公共政策研究所貝利博士所言,核武器儲備管理項目并不能替代核試驗。盡管模擬試驗實施嚴格,美國國家核軍工管理局發布的季度報告卻無法使包括中國在內的對手信服,核彈頭的威力也沒有設想的那樣巨大。時至今日,人們不禁思索一個問題:其他國家真的認為美國的核彈頭還擁有往日的威懾力嗎?
國家非核武器的戰斗力。當對手非核武器戰斗力大大超越本國時,實力較弱的國家將會更加依賴核武器以維護自身安全。莫斯科軍事科學院院長馬克姆特·加列耶夫在2004年的一次講話中說:“在目前的情況下,核武器在俄羅斯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這是能保護我們國家的因素,也是我們唯一能反制戰略武器威脅的東西。”當國家面臨危難時,領導人將面臨放棄政權與發動核戰爭的抉擇,此時,核戰爭可能成為最后的救命稻草。
危機或沖突發生期的核威懾
過去10年,中國海軍正大踏步地向現代化邁進。蘭德公司的研究報告分析了1914年英德戰爭、1941年日美戰爭及英美海上霸權之爭,前兩個事件都是以戰爭收場,最后一個事件的結局是英美海上霸主的地位轉換。報告還指出,美國不會成為第二個英國,不會把東亞海上霸主的地位給中國。如果中美關系惡化為當年的英德或日美關系,那么太平洋注定會掀起一場軒然大波。
慎重對待形勢分析。曾擔任老布什和克林頓政府中東問題特別協調員的丹尼斯·羅斯指出,美國誤判了1990年的科威特戰爭。他說:“當時幾乎沒有鄰國和其他國家政府預料到伊拉克會真的入侵科威特,各國的理性都被有關薩達姆的錯誤假設信息所蒙蔽。”中國一樣會想著釋放煙霧彈混淆視聽,事實也正是如此,幾乎沒有分析人士預測到中國在2013年11月宣布劃定防空識別區。鑒于這種情況,必須慎重對待時局。
擺脫“無核戰”的僵化思路。美國的許多戰爭對手都是與美國核力量建設水平相差懸殊的國家,甚至一些是無核國家,然而,中國卻不同,它的核力量不容小覷,因而,對待中美戰爭的思考不能停留在僵化的老路上。當前,許多學者提出的戰略往往忽視核威脅。比如,國防部長辦公室政策研究室顧問白邦瑞就描述了中國的16個擔憂,其中有6項仍停留于傳統危機或沖突層面——島嶼封鎖、襲擊航母、大規模空襲、打擊戰略導彈、干擾與精確打擊、攻擊反衛星系統。哈佛法學院軍事專家肖恩·米爾斯基在《戰略研究雜志》上刊文,探討美國如何對華實施封鎖戰略。他說,美國不需要考慮如何在核戰爭中實施這一戰略,因為那種情況只會在所有核威懾都失效的情況下才會爆發。此外,美國國防大學國家安全研究學院研究員、海軍陸戰隊退役上校哈姆斯還提出“近海控制”戰略,一是阻止中國使用第一島鏈之內的海域,二是保衛第一島鏈周邊的海域和空域,三是掌握第一島鏈的制空權和制海權。這些概念的提出都未抓住本質,即中國不僅有上百艘戰艦,還是一個有核國家。即便是有些軍艦實力不濟,或是艦上官兵素質不過硬,軍事專家也不能完全指望美國通過封鎖摧毀中國經濟。可怕的是,封鎖可能惹惱北京政權,用武力甚至是核武器解決問題。美國當前采取的措施會在很長時間內影響核威懾力建設,這將使美國未來如逆水行舟。
注重軍事外交細節。哈佛大學的談判家威廉·尤瑞和布朗大學的理查德·斯莫克在研究核危機問題時都指出,新的危機時代正在呼喚一種新的談判方式。如果中美兩國燃起戰火,那么陸、海、空、天、網各個領域都會迅速加入戰斗。而戰爭的不確定性決定了戰場的復雜性,美中思維方式的差異又將這種復雜性放大。由此,處理相關事件需要更大的智慧。2001年4月中美撞機事件發生后,美國要求中方認真對待撞機事件并質問中方是否知曉事故全過程。不過,美駐華大使特別助理也坦言:“在駐華官員還沒有與中國外交部溝通之前,太平洋司令部只是在網站上發布了一則簡單描述事實的消息。”試想,在沒有和官方建立任何外交和軍事溝通的情況下,貿然發布“中美撞機”事件的新聞,極有可能將事態的發展推向未知。
危機或沖突發生期的三點政策建議
在危機或沖突發生期的政策建議主要如下:一是美國政治領導人和政策制定者,必須更好地掌握中國核力量的編成以及軍隊決策機制。此外,美國在政策制定上還必須用心,不能表露出有先發制人打擊中國核力量的企圖。在《原子科學家公報》上,劉易斯(編注:約翰·劉易斯,美國斯坦福大學國際安全和合作中心榮譽研究員)和薛理泰(編注:美國斯坦福大學國際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員)在文章中描述了一種可能的情形:中國在危機或沖突發生時向美國發射非核導彈,而美國的反擊必將是傳統武器系統與核武器的結合,這迫使中國核導彈部隊發射核彈。所以,了解中國第二炮兵的實力是當務之急,這有利于美國對中國核威懾力的評估。
二是確保有效的核反擊能力,這是阻止核戰爭爆發的關鍵因素,美國需要著力避免暴露打擊戰略核潛艇的意圖。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最近的調查顯示,“巨浪”-2導彈及晉級戰略核潛艇,標志著中國在海基核力量上占有一席之地,如果中國能順利完成計劃,它可能會調整相關部隊的配置,形成更強的戰斗力。
三是美國需要更新觀念,必須考慮中美交戰時,如何采用非武力手段實現政治和軍事目的。運用軍事手段意味著要精確打擊防空導彈基地以及指揮中心,基于目前美國對于二炮部隊的了解,美軍要做到零失誤幾乎不可能,這很有可能造成戰略上的被動。為防止沖突演化為核戰爭,美國需要讓交戰區遠離中國大陸。中美兩國的政治家和軍事家都應該意識到,戰爭耗費人力物力財力,令人遺憾的是,雖然沒有人希望世界成為火藥桶,但為了在這場未知的戰爭中獲勝,雙方都不會放棄使用核反擊,這必將造成更大的災難。
(摘自《世界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