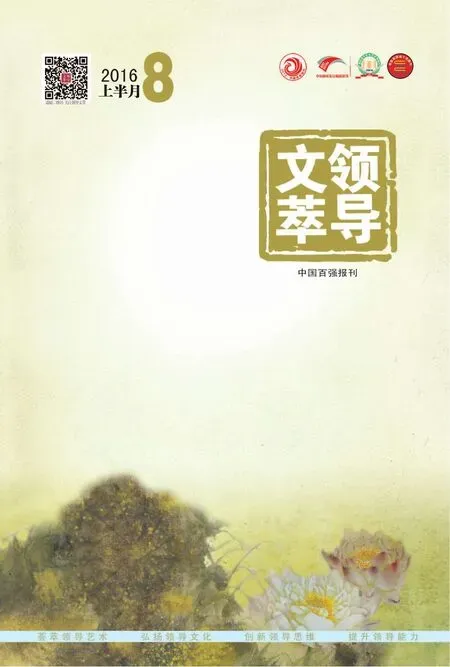帝師已死
□劉剛
帝師已死
□劉剛
中國傳統里,有一種學問,叫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這是怎樣的學問?總之說不清。但有明白的人,比如劉伯溫。
劉伯溫,原本是個科舉制里的讀書人,按照現在填表的格式,他的“個人成份”應該是“學生”。然而,科舉制對于“學生”的要求,并沒有“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這一條。可見劉伯溫是個科舉制框不住的人,他可以從科舉制出身,卻不讓科舉決定終身,所以,在儒教經典之外,他還要另辟蹊徑,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究天人之際”。
據說,中國帝王學里有四大帝師,呂尚、張良、諸葛亮和劉伯溫。這四位,均非從“周孔之教”的模子里出來的,倒像是從神話與歷史交錯的道家學說里跑出來的半人半仙。作為帝師,本來有兩方面的作為,一是政治上的導師,還有就是軍事上的軍師。這兩方面,被儒、道兩家分擔了。政治方面,先是周孔之教,后來有孔孟之道加上程朱理學,做了歷朝帝王的導師。而軍事方面,則沒有常設的帝師,一般都是據亂世的臨時配置,一旦亂世結束,軍師就面臨何去何從的問題。軍師不是意識形態,可以高高掛起,而是需要面對的血肉之軀,是個實際問題。
四大帝師,呂尚之所以能功德圓滿,是因為有分封制,可以封邦建國。而張良面對君主專制,就只能退隱了,退隱還算是善終。至于諸葛亮,嚴格說來,還算不上“一個”軍師,“三分天下”,也就是個“三分之一”的軍師,不過,諸葛亮卻不失為從軍師向行政官僚轉化的范例。諸葛亮能從軍師轉化為丞相,有兩個先決條件。其一,他本就是個“三分之一”的軍師,其二,是因為劉備早死。劉備也就是為了奪取荊襄,才三顧茅廬,拜他為軍師,入蜀以后,有兩個重大的戰略行動,關羽北伐,劉備東征,都沒讓他參與,何也?或如陳壽《三國志》所言“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或許劉備已然發覺《隆中對》里“三分天下”的戰略便是諸葛氏家族的戰略,諸葛氏三兄弟分居于魏、蜀、吳三國,便是其家族戰略的狡兔三窟式布局,諸葛亮實現個人轉型,劉禪卻失敗了。
諸葛亮之于劉禪,已非所謂“軍師”,而是如曹操之于漢獻帝,已然權相,有所區別者,在于“忠奸”二字。亮之忠,孟德之奸,古今已有確論,然,凡為權相,必有奸心,遍觀歷史,無不應驗,不獨孟德大奸,就連諸葛亮也難免。何也?觀其“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貌似大忠,實為自謀,較之曹操玩漢獻帝于掌股,雖有大忠與大奸的差距,但忠與奸本來就是相反相成的一體兩面。亮此言,看似一腔熱血的后面,還有潛臺詞,實乃警告蠢蠢欲動的后主:只要我還在,就不會還權于汝。今日,我們重讀《出師表》,觀其明知“民窮兵疲”,戰無勝算,還要用兵,全無《隆中對》之戰略思想,惟以權謀伏于忠義辭章,動輒祭起先帝遺志,而不見其為國為民著想,無謀富國強兵之策,反以曹操作為軍事投機的榜樣,欲以機會主義的用計,來取代提高綜合國力。孫子言戰,曰“多算勝,少算不勝,何況無算乎!”所謂“算”,就是從綜合國力上來“算”,亮無勝“算”而戰,故其欲勝者非外而在內也,亮以不斷用兵,牢牢掌握兵權,他沒想過要歸政于后主,還權于劉禪。
劉伯溫剛好相反,他沒有完成從軍師向丞相的轉型。據說,朱元璋找他談過一次,先提了幾個丞相候選人,向他征求意見,都被他否定了。于是,朱元璋說,我看你最合適。他馬上回絕了:我不行,還是李善長合適。為什么要回絕?他自說是行政工作太繁瑣,人事協調太煩,他不耐煩。朱元璋說,李善長處處跟你為難,你為什么還要說他行呢?他沒有迎合朱元璋,反而重提李善長。朱元璋當然沒有聽他的話,那幾位被他否定的人選,后來,都被朱元璋用作了丞相,可想而知,他們今后會對他怎樣,而李善長也不會因此而買他的賬。
四位帝師中,惟有劉伯溫是從科舉制里出來的,身上還有股子書生意氣。這意氣,于官僚體制總有些格格不入,時不時地就要發作。50歲以前,他從科舉制出身不難,可仕途上卻磕磕絆絆,書生意氣一發作,他便辭了官,回到老家南田,一個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50歲以后,他被朱元璋發現,一而再,再而三的邀請,他終于出山!出山以來,戰場上克敵不難,官場上還是磕磕絆絆,書生意氣再發作,便得罪了朱元璋的老班底淮右集團,又辭了官,歸去來兮,最后還是遭了官場暗算。暗算者,都說是胡惟庸,因為他生病時,身為丞相的胡惟庸親自給他送藥來了,他服藥以后,病情反而惡化,他把這一情況告訴朱元璋,朱未過問此事,看著他死。因此,有人懷疑,朱是幕后主使,若非以御賜的名義,他豈能隨便服用政敵送來的藥?若被政敵掉了包,朱安能不理?更何況朱明知胡是他的政敵,偏偏讓胡來送藥,是何用意?后來,胡惟庸案發,這筆賬就一并算到胡的頭上去。
帝師沒落是趨勢,每下愈況,張良不如呂尚,劉伯溫不如諸葛亮,劉伯溫以后,再也沒有那樣的帝師了。帝師終結者是朱元璋,看似官場排除異己,實則欲以君主專制消滅書生意氣。
(摘自《經濟觀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