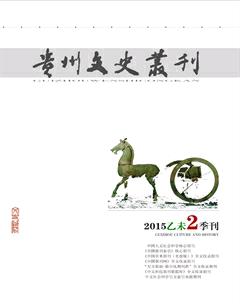漢族、儒家與西南少數民族、祭司及其生態文化比較①
顧久+張彪
摘 要:美麗中國之夢必以生態文明為根。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則為培育生態文明之土。西南少數民族與漢族種族同源、生態文化同型相類,少數民族生態文化與儒家思想一樣,極具智慧、極其宏富,當可共為人類實現永續發展提供良好借鑒。
關鍵詞:漢族 西南少數民族 儒家 祭司 生態文化
中圖分類號:G1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8705(2015)02-7-17
漢族形成于黃河流域,西南少數民族則地處蠻陬;儒家是中華文化的主干,而西南少數民族的祭司卻長期湮滅無聞。但是,兩族的族源和文化,兩者的職業和氣質,都有很強相似性,其生態文化因此具有很強同質性和可比性。
本文擬先對漢族與西南少數民族、儒家與西南少數民族祭司作比較,在此基礎上,對兩者的生態文化進行比較。
文章分兩部分:第一,漢族與西南少數民族、儒家與西南少數民族祭司的比較;第二,儒家與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的謀生方式、生態思想、生態行為、生態制度的比較及其啟示。
第一部分 漢族與西南少數民族、儒家與西南少數民族祭司的比較
一、種族同源
本節的主語,是漢族與西南少數民族族源。
關于種族,以往學者們主要依據有限的化石和文獻,以及豐富的聯想,持“多地區起源說”,比如中國人是北京人的后人,西方人為尼安德特人的苗裔等。并認為中國人最初是由北方向南方逐漸遷徙發展開來的。
但當代分子遺傳學卻提出:人類本同源,皆從東非來。
1987年,加利福利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瑞貝卡·卡恩等在美國《新聞周刊》發表關于線粒體DNA研究的成果報告,最先提出人類“非洲起源說”。2000年11月,《自然遺傳學》雜志發布了彼得·昂德希爾等二十一位研究者的成果,依據全球一千零六十二個具有代表性的男性Y染色體進行研究,也表明現代人群都起源于非洲。
中國褚嘉佑也于1998年在《美國科學院學報》發表文章,提出現代亞洲人類可能起源于非洲。2001年,復旦大學金力等人在《科學》雜志發表《東亞現代人的非洲起源:一萬二千個Y染色體的故事》,支持現代中國人的“非洲起源說”。而且,通過褚嘉佑、金力、李輝等學者的研究,以及一項由全球十個研究機構參與合作的“追尋人類足跡計劃”的研究進一步指出,黃色人種是從東非來到東亞的第二波亞洲人,即“晚亞洲人”;現代中國人的祖先是從南向北擴展的,一路從越南、廣西方向沿海岸線往東北走,一路沿云貴高原的西側向北走。與此同時,歷史語言學家們通過對語系、詞匯等的對比研究,也得出了東亞語言同源的結論。[1]6-30
于是,北京大學教授吳國盛在其頗具影響力的專著《科學的歷程》第三版《自序》中鄭重聲明:“人類起源問題,按照最新的古人類學和分子遺傳學的研究進展做了重新改寫,明確反對人類多地區起源說,支持現代人類的非洲單一起源說,明確中國人并不是周口店北京人的后代。”[2]
關于人類起源地和民族遷徙方向等問題,尚有待進一步證實,但西南少數民族與漢族人種同源、族群同宗,應該是一個相當可靠的結論。
二、職業同類
本節的主語,是漢族的儒與西南少數民族的祭司。
“儒”是早于先秦儒家的一種社會職業,“儒家”為春秋時孔子所開創的一個學術流派,兩者有異;但“儒家”是“儒”這個職業的繼承者,是兩者之同。
(一)儒源于早期漢族的祭司
祭司應該是人類在原初社會里最早溝通神人的知識階層,而儒家是這些人的繼承者。
贊同這個觀點者稱:“儒者,術士也。太史公《儒林列傳》曰,‘秦之季世坑術士,而世謂之坑儒。”[3]104“其實一切儒,無論君子儒與小人儒,品格盡管有高低,生活的路子是一樣的。……他們不僅僅是殷民族的教士,竟漸漸成了殷、周民族共同需要的教師了。……儒是一個古宗教的教師,治喪相禮之外,他們還要做其他的宗教職務。《論語》記孔子的生活,有一條說:‘鄉人儺,(孔子)朝服而立于阼階。”[4]25,33“孔子是傳統的轉化性的創造者。在孔子之前,有一個悠久的巫史傳統。”“孔子將上古巫術禮儀中的神圣情感心態,轉化性地創造為世俗生存中具有神圣價值和崇高效用的人間情誼,即夫婦、父子、兄弟、朋友、君臣之間的人際關系和人際情感,以這作為政治的根本。它既世俗又神圣,既平凡又崇高,‘仁因之成了人所以為人的內在根據”。[5]157,181
陳來等先生不贊同。數年前,陳先生獻疑:“孔子的儒家思想如何能跨越六百年的歷史而直接從商代的術士得到說明,特別是,巫術,巫師如何可能產生出相當程度上理性化和‘脫魅了的儒學來,是有著根本的困難的。”[6]342近來他又重申:“如果我們從思想本身出發,就很容易提出這樣的問題:孔子主張仁義,主張六經的思想,是不是在巫師這里就可以產生出來?或者是不是從相禮、做喪事這樣的職業就可以產生出來?因此,我主張研究一種思想的起源,首要的是要關注這個思想體系的內部的元素在歷史上有沒有出現過,怎么樣發展,怎么樣承接,怎么樣改造。如果我們不研究這些問題,僅僅從職業、僅僅從文字的角度去看這個問題,我們就很難達成一致的意見,而且很可能永遠不知道答案。”[7]4
但贊同者與反對者都沒有從活態的少數民族取材,沒有從民族學的角度研究。下面,我們試就儒家與西南少數民族祭司比較,以支持“儒家源于祭司”說。
(二)儒(儒家)與西南少數民族祭司的比較
1. 作用顯要受人敬重
無論漢族或少數民族,祭司的社會作用大致可以表述為:溝通鬼神、傳承文獻、規范行為、解釋世界、探索意義。他們是該民族的精神領袖,因此地位崇高受人尊敬。
儒(儒家):曾是早期溝通天地神人的重要人物,漢馬王堆出土帛書《要》篇記述孔子語:“贊而不達于數,則其為之巫,數而不達于德,則其為之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5]156 因為掌握典籍,所有也含“老師”之義,如鄭玄《周禮·天官·冢宰》注:“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賈公彥疏:“儒,掌養國子以道德,故云‘以道得民;民亦謂學子也”。[8]648endprint
西南少數民族祭司也如此:在宗教儀式方面,瑤族祭司“由于人們對鬼神深信不疑,并敬畏特甚,一旦有病或遇到什么疑難時,往往求之于鬼神,這樣……師公、道公、先生公們,在群眾的心目中就占有特殊的地位”。彝族“畢摩與彝族人民的生活發生著多方面的聯系,舉凡生死婚嫁,吉兇禍福,年節集會都少不了畢摩作法,這樣,畢摩受到人們的尊重,享有一定的威望”。在傳承文化知識方面,苗族“當鬼師和巫師的, 他們必須熟悉本族的各種歷史神話、傳說故事等等, 并牢記歷代流傳的各種歌謠。所以他們里面的許多人大都是能說今道古并善唱歌的……苗族歷代祖先所積累的許多成套的歌謠如《鼓社祭之歌》等等,很大一部分都是靠了他們才能流傳至今的,并且不少歌詞往往就是經由他們辛勤勞動而創作出來的。因此,他們不僅是苗族社會中的職業性宗教人員,而且稱得上是本民族的‘知識分子。而湘西的苗民, 干脆把他們稱為‘客老師或‘苗老師”。[9]彝族,“因為布摩是彝書的主要創作者,借助文字這種資源將自己神圣化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事。但這些帶著神話色彩的描述依然折射出布摩在現實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他們躋身君長國的統治階層,為國君、大臣乃至一般百姓敘譜、占卜、祭祀——在傳統的彝族社會中,這些全是至關重要的大事,而各個階層的人們亦承認布摩淵博的學識以及溝通三界四極的能力。”[10]27
2.特定的思想特質
由于儒(儒家)與祭司崇高的社會地位,勢必產生出相應思想特質。
(1)品德高尚,是族群的道德標準
儒(儒家):重視品德修養,是漢民族道德的宣教者和示范者,這一點,人所共知,不必贅言。
西南少數民族祭司:哈尼族的祭司“儒瑪”,“只有道德品質優良, 能大公無私地為群眾辦事的人才能充當”。苗族“祭鼓社的主要主持人是‘鼓社頭……鼓頭主持祭祀祖宗的大典,是一個莊嚴的職務。群眾認為他的一言一行都關系著家族的幸福和安全,因而當上鼓頭的就有許多禁忌不得觸犯,如不能殺生,不能捕鳥…… ”。[9]彝族,“布摩、幕史的所有兒子都可以參加學習,但要用下列標準進行檢測,遴選一個合格的傳人:一、潔凈清白。不侮辱文字,講究個人衛生,這是潔凈之意。清白指品德,踩到蟲蟲螞蟻都是過失,要念解冤經解冤。只有走天地人道之路,保持自身的根本,才能通到天樂之處。二、溫柔忍耐。脾氣暴躁的兒子不能傳給他某些書,如使法的書。三、孝順善忠。這是對父母和君主的基本準則。”[10]223
(2)維護族群內的團結
儒家的主要思想之一,是倡導以“親親”為基礎而推而廣之的“仁”。也毋需贅述。
西南少數民族祭司:重視原始宗教儀式以增加“我們是一家人”的情感和信念。仡佬族,“八月節”這一天,“人人著新裝聚于寨中寬敞之處,在‘族老指揮下進行剽牛儀式。剽前,‘族老祈禱一番,……剽后, 將牛心按全族戶數分好,由家長領回供祭祖先,以示全族‘同心”。珞巴族有所謂“那戈”,乃是專供祭祀用的小屋,“是團結的象征,有共同那戈的氏族,對外發生爭端時,要相互支持”。獨龍族的“卡雀哇”,義為“聚族祭祀”。是日, 由“鳥”(巫師)牽牛至祭場, 椎牛祭祀, 之后“將帶皮毛的牛肉平均分給全體參加者, 各自攜家煮食。鰥寡孤獨者從優分配。對未及時趕到的親友, 必托人捎去一份, 以示思念和敬意”。這些, 都證明了祭祀儀式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增強同一血統氏族的團結。[9]
(3)重視群內的等差秩序
儒家:制“禮”以分別各自的身份。《禮記·經解》說:“禮之于正國也, 猶衡之于輕重也, 繩墨之于曲直也, 規矩之于方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 以入朝廷, 則貴賤有位;以處家室, 則父子親, 兄弟和;以處鄉里, 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 莫善于禮。此之謂也。”[8] 1610《禮記·曲禮》也說:“夫禮者, 所以定親疏, 決嫌疑, 別同異, 明是非也”。又云:“君臣、上下、父子、兄弟, 非禮不定”。[8]1231
西南少數民族祭司:侗族“(六月)節前十二天, 同宗主婦按長、次房順序排成隊, 攜竹筒、水桶、粽粑葉、干蕨菜、糯米等物到指定的河邊洗凈, 又依原次序排隊回家,……祭吃的順序也依長次房而行”。哈尼族祭母節時也“按年齡大小順序入席飲酒吃飯。”[9]彝族,傳統社會依次分為君、臣、畢摩三類人。《彝族源流·座次論》說,正是畢摩幫助人們找到了自己的階級的“座位”:“在大地四方的中央左為君座,右為臣座,頂為畢摩座,周圍是民眾座,中間是男女座。坐有座位,不要坐錯座位,不能找錯等級,找準等級后就找到了根。死者有座位,活人才順利。有根作依靠才安寧。”[11]74
因此,儒與西南少數民族祭司,無論是社會作用地位,還是其思想特質,都有相當同質性和可比性。
三、文化同型
本節的主語,是漢族與西南少數民族文化。
(一)本文的“文化”觀
“文化”有廣、狹二義。狹義文化指人類的精神,其實是人腦的功能。我們以為,人類大腦至少有初級和高級兩種功能:初級的至少有感覺、識別、編碼、記憶、引導行動等;高級的至少有人類語言,以及在語言基礎上的思維——大腦活動的過程,觀念——大腦活動的結果,含世界觀、社會觀、人生觀、價值觀等等,意識——對思維的反思,以及上述幾方面的綜合呈現——宗教、文學、藝術、道德等等。
大腦雖重要,但狹義“文化”是有局限的。因為大腦必須長在一個有七情六欲的肉體之上;而作為社會性的靈長目動物,一個個肉體還必須緊密抱團才可能生存下來;要抱團,還必需一定的組織秩序和共同的行為習慣等。所以,本文所言“文化”主要采用廣義的概念——文化人類學家(如費孝通先生)說的“人文世界”。這是某個族群維系生存、不斷傳承的生存體系,主要由四個子系統組合而成:第一,謀生的系統——該系統對應于人腦最原始的部分,如下丘腦,本能地指揮個體如何生存、繁衍、逃避、攻擊等。該系統派生出物質文明和科學、技術等能力;第二,組織秩序的系統——該系統對應于人腦次古老的部分,如邊緣系統等,以解決人類個體如何按一定組織關系抱團。該系統派生出倫理、團體認同與排斥、法律和政治等等;第三,日常禮俗的系統——該系統既對應于最古老的下丘腦也對應于后來出現的邊緣系統,形成日常行為習慣規則,包含了以后的衣食住行的習慣,歲時年節、人生禮俗的安排,民間文藝工藝等等。形成共同體認同的行為秩序;第四,安頓心靈的系統——該系統對應于大腦最后形成的大腦皮層,主要產生各種復雜的符號,保障個體和群體的心安理得。該系統包含思維、觀念、意識、綜合呈現等等。endprint
上述四者,有機地互足互滲,共同形成源于生物而又不同于一般動物的、非遺傳本能的“人文世界”,使生存其間的人們被文明地化育為一,故稱之為“文化”。
(二)漢族與西南少數民族的文化比較
用上述文化觀看待漢族與西南少數民族:
首先,兩者都基于農耕文明基礎上的謀生方式。中原漢族生活在大河流域,有數千年農耕文明的傳統;西南少數民族生活在溝壑縱橫的山地,非游牧如西北,亦非商業如希臘,也有數千年的農耕文明傳統。但漢族生產條件、技術更強,很早就形成定耕農業,而有些西南少數民族在不久以前還刀耕火種、游耕和定耕農業并存。
其次,兩者都構成以血緣為紐帶的家庭、家族、氏族等組織秩序。但漢族因為生產條件和技術更好,所以人口更多,戰爭更烈,交融更廣,此中組成更大更強的國家群體并出現更早更全的文字系統,而大多數西南少數民族處于相對封閉的山野,過著沒有文字的族群或部族生活。
再次,兩者都具有大量日常的神圣習俗維系著日常行為,形成共同的行為準則和認同感。但漢族因為城市、國家、文字、知識精英的出現,其習俗有的早已訴諸文字,形成《三禮》等經典,而西南少數民族大多依靠族老、祭司等口耳相傳、率先引領示范,演繹著世代的故事。
最后,在上述三者基礎上產生出精神文化——安頓心靈方式。但漢族因為文字記載、精英的專職化等,出現以儒家為主干的意識形態——血緣基礎上產生的情感“仁”、等差關系上產生的規矩“禮”之類,而西南少數民族的精神傳統則主要體現在具有宗教色彩的古歌民謠、長輩教訓、典禮儀式、日常習俗等之中。
總之,漢族與西南少數民族的“人文世界”細節有同有異,但其生存體系——文化模式是同型的,具有可比性。
第二部分 儒家與西南少數民族的生態文化比較及其啟示
上面提到,我們的“文化”指“人文世界”,包含著謀生方式、組織秩序、日常習俗和安頓靈魂等四個子系統,而儒家與西南少數民族的生態文化也可以由這四個子系統來觀察。順序略作更換,按謀生方式,安頓靈魂——生態意識,組織秩序——生態制度,日常習俗——生態行為為序。因為按照邏輯,有合適的謀生方式人才能生存,一定的生存方式會產生相應的觀念意識,特定的謀生方式和觀念意識會有相應的組織秩序和日常習俗。
一、謀生方式比較
漢族、儒家與西南少數民族的文化都建立在農耕文明基礎上。而農耕生產對自然生態的依賴性很強,所以都崇尚自然、降低欲求。“崇尚自然”,我們將在下一節說明,本節先分析“降低欲求”。
費孝通先生把這種降欲求、重消遣的生活方式稱為“消遣經濟”,而把工業化、市場化驅動的資本主義謀生方式,叫“消費經濟”。在西方經濟學眼中,農耕者顯得懶散,從而效率低下貧困落后。而他認為,閑散的經濟態度“不但有他的道理,而且這道理是值得我們仔細想想的”。因為農耕社會的生產目的僅是溫飽,這是人生存的基本需求,而工業社會的生產目的是享受,這是超出基本需求的欲望;前者的策略是減少欲望,滿足基本需求,因此減勞作、減生產、減消費,后者的策略則是擴大欲望的“三多”——多勞作、多生產、多消費;前者的“減”帶來了閑暇和消遣,后者的“多”帶來了享受和消費。費先生說:“消遣和消費的不同是在這里,消費是以消耗物資來獲取快感的過程,消遣是不消耗物資而獲得快感的過程。”[12]405-409
費先生所揭示的現象仍可再往前延伸和往后延伸。往前延伸的問題是,傳統農耕文明為什么要“減欲望”?其實是受當時的自然條件、科技水平、生產力高度所模塑的,而現代工業文明的“三多”,是因為科學技術、生產力支撐著人們的高欲望。一定意義上說,市場經濟的核心要素是物質欲望。有了欲望才有需求,有了需求才有市場,有了市場才有生產,有了生產才有就業,才有財富的增長和經濟的發達。往后延伸的問題是,兩種謀生方式對自然資源和環境各自帶來什么樣的影響?農耕文明的謀生方式顯然對自然資源和環境的破壞相對小,因為“消遣是不消耗物資而獲得快感的過程”,而工業文明及其態度對自然環境的破壞相對大,如洛克宣言的“對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
在農耕文明的基礎上生長出來的儒家,顯示出安貧樂道的生活態度。《論語·述而》“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也好,“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13]93,98也好,表現出對節制的物質生活和高標準道德境界的提倡。這種節欲態度到宋明理學家更發展到“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的要求,其實是農耕文明必然的生活態度。而《論語·先進》中“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13]123-124的閑適,更陶鑄了中國人從《桃花源記》到田園詩歌的境界,也體現了農耕文明自然的閑適境界。
西南少數民族同樣也有著非常重視“消遣”的現象。在這里,喝酒、對歌、跳舞、捕獵、斗鳥、斗牛、過節絕不是生活中的小事。許多少數民族群眾認為,擁有充足的時間去休閑,使他們能時常處于一種安閑自在的生存狀態,這永遠是第一位的。至于物質生活,不至于餓肚子就好。甚至可以說,在他們心目中,貨幣收入并不是具有最高價值的東西。
正因為這種“消遣經濟”現象的普遍存在,使得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成為傳統民族節日最豐富、節日文化最絢麗的地點。“大節三六九,小節天天有”,紀年性、祭祀性、紀念性、農事性、社交性等節日類型應有盡有,娛神功能、娛人功能,傳承民族文化、模塑民族心理功能樣樣俱全。比如貴州,就是“民俗節日文化的勝地”。除多民族共同擁有的“牛壽節”、“吃新節”、“敬橋節”、“年節”外,還有苗族、侗族的“鼓藏節”,布依族、壯族的“三月三”、“六月六”, 彝族、毛南族的“火把節”,苗族的“姊妹節”、“跳花節”、“蘆笙節”,侗族“采桑節”、“薩瑪節”,彝族的“賽馬節”,仡佬族的“祭山節”等等,總計超過一千個。
因此,儒家也好,西南少數民族也好,其謀生的方式對自然資源和環境,是相對親和而破壞力小的。endprint
二、生態意識比較
早先的農耕生活不易,受自然、環境、生態、野獸、敵對族群等的危害,在當時生產力水平和認識水平的影響下,對影響生存的要素具有敬畏之情,并產生出強烈的生態意識。這種意識是受到所謂“原始思維”局限的。這種思維的特征,我們以為具有更多的直觀性、具體性、泛神性、互滲性等。在此思維框架下,早先的人類日常行為——如食衣住行、歲時年節、人生禮俗等——都充斥著大量的巫術、禁忌、占卜及神圣的儀式。
漢族對自然的敬畏感早先也源于“萬物有靈”的觀念。馮友蘭說,“人在原始時代,當智識之初開,多以為宇宙間食物,皆有神統治之”。“覡巫尚須為神‘制處、位、次主,則神之多可知”。[14]23《禮記·月令》亦有載:仲冬之月,“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季冬之月,“乃畢山川之祀”。[8]1383-1384
當然,這種敬天地畏鬼神的思想,后來經周代和孔子們的努力,鬼神性淡化、更多人文理性和道德倫理性。人文理性的話語主要表現為自然與人類融合為一體的“天人合一”思想,而倫理性則被后人稱為“德及禽獸”、“澤及草木”、“恩及于土”等情感及舉措。[15]1-90早期的經典《尚書·泰誓》中就有“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論述,闡述了天與人之間存在著較為緊密的聯系。[16]153,157到張載正式道明“天人合一”,其《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渾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17]183 而王陽明說得更透徹:“蓋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風雨露雷,日月星辰,禽獸草木,山川土石,與人原是一體,故五谷禽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為同此一氣,故能相通耳。”[18]286
在西南,少數民族對自然的敬畏感沒有經過儒家的理性化和倫理化,更多呈現在原初宗教與神圣習俗之中,主要借助古歌、傳說等來口耳相傳。
比如黔東南的苗族古歌《楓木》描述:楓樹心里生出妹榜妹留(蝴蝶媽媽)。榜留與水泡泡“游方”(戀愛)生下十二個蛋。由鹡宇鳥孵抱了十六個冬春,分別孵出雷公、水龍、老虎、蜈蚣和人類的祖先——姜央等十二個兄弟。這不僅是口頭傳說,更作為信仰滲透在苗族同胞的歌曲、苗繡、苗銀飾及人生習俗之中。有些地方當嬰兒長大,要把繡有蝴蝶、楓葉的襁褓埋在楓樹底下,告慰先祖:又添了一個后代。有的老奶奶離世,認定要穿繡有蝴蝶媽媽圖案的衣服才能去見祖宗。蝴蝶的形象與張載的“民胞物與”一樣,具有苗族“萬物一體、天下一家”的宏大胸懷。
無獨有偶,《侗族古歌·人類起源》中也記載了開天辟地后,四個龜婆孵蛋孵出了人類的祖先松恩和松桑,二人婚配后生下了虎、熊、蛇、龍、雷……以及會說話的章良和章美的故事。在侗族地區,有不少人家深信自己的祖宗與水牛同緣。屬于“笨臘國、臘秀想、南蕩門”,即“水牛的根骨,如象骨之高貴,脂肪之清香”,是正宗血統,高門旺戶,名聲顯揚的家族。有的還以水牛角,駕在門樓坊上,顯為榮貴,表示屬于水牛種。[19]331,355,356
彝族,認為其先祖篤慕在天帝“策舉祖”的撮合下,在“貝谷懇嘎”這個地方設立歌場,與北斗星、南斗星、北極星之三女因對歌而結為夫妻,生下六子,史稱“六祖”。《彝族古歌·人類起源》這樣唱誦他們的萬物同源:“仙生司武吐,居于高峻巖,人與天地同輩分,天驕子育人,竇米能生民。天生人煙續,什勺氏生民。人與乾坤同輩分,惹慕尼生民。天地人共處,采舍氏生民。人與天地同輩分,在麻苦恒裊,做一寨居住……”[20]237-238
從上述比較中,我們看到了西南少數民族文化同儒家都具有根深蒂固的人與天地萬物相融合相感應的觀念和理念,完全有別于西方人將自然與人類分而為二、各自獨立,自然僅僅是人類占有、征服、滿足欲望客體的主張。
三、生態行為比較
某個族群共有的日常行為往往是與謀生方式相適應、在一定思想框架下運行的。整飭的日常行為模式維系著一個族群的秩序。這些行為往往呈現在規范化的禮俗之中,如在巫術禁忌籠罩下的衣食住行、歲時年節、人生禮俗、民間藝術等。
在漢族,文字記載了大量生態習俗。比如司馬遷《史記》記載了儒家推崇的先王商湯的故事:“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論者謂體現了儒家在生產習俗中的用傳統禁忌傳達出“德及禽獸”的仁愛精神。[21]55《論語·八佾》中宰我言及古社稷種的樹“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白虎通》解釋道:“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民望見即敬之,又所以表功也。”[22]89,這些樹有一種神木之意。
類似“網開三面”的狩獵風俗也存在于西南少數民族,如黔南平塘布依族獵手,出獵前要念“團山經”,“人們相信通過施行這樣的巫術,就會把野獸圍堵在山中,便于捕獵”,而一旦有所獵獲,又必須念“放山經”,放掉其余的虎豹,“雖同一地方還有多只虎豹,也不能再捕獵第二只。”[23]165而傈僳族、獨龍族、怒族、布朗族、阿昌族等同胞,則有不獵懷孕、產崽、哺乳時節的動物的狩獵禁忌。類似“社稷神木”敬樹、惜樹的禁忌習俗,西南少數民族也有很多:云南藏族有神山圣湖崇拜,百姓認定,為神山種一棵樹可延壽五年,而損一樹則會折壽五年等。云南麗江納西族認為主管山林川藪及動物之神叫“署”,本來與人類為新兄弟。如果人類破壞了大自然,卻會受到“署”的報復。每當開年,納西族同胞要舉行“署谷”儀式,反省自己是否過度傷害生態和自然環境,如果有,則向“署”致歉。[24]
西南少數民族生態意識更實踐在人生禮俗、歲時年節、民間歌謠等習俗之中。
如西南侗族、土家族有在嬰兒降生時種“十八女兒杉”的習俗:侗族群眾每當孩子出生,家人或寨鄰要為孩子栽種一片杉林,數量一般為一百株左右,十八年間不得砍伐,直到孩子成年成親,將此樹作為兒女婚嫁資費和修建新房之用。土家人若嬰兒降生于春季,則種幾株或十幾株椿樹,叫“喜樹”;若非春季,則來年春天還得補種喜樹,以伴孩子成長。黔東南從江縣岜沙苗族則把樹當做生命的象征,每當一個嬰兒出生,家人就種一棵樹,該樹以嬰兒的名字來命名和呵護,待嬰兒成人直到死亡,就用這棵樹為他下葬,并在深葬處再種一棵樹。水族群眾則在喪葬地種楓樹以保風土,以佑后人。廣西隆井仡佬族人通過宗教節日保護神樹,其8月15有“拜樹節”,要殺牛、雞之類牲畜祭祀之。土家族則于每年臘月二十九、三十日,給房前屋后的果樹進奉年飯。瑤族同胞歌謠中有“萬樹與棕,一世不窮”,佤族諺語中則有“毀了山,就破壞了地方”等。[25]endprint
四、生態制度比較
人類要組成群落,必然會制定強制性的制度;該人群要保護生態,必然形成有關保護自然生態的制度。不過,儒家制度具有著國家的意志,而西南少數民族的制度則主要體現在寨老、理老之類精英人士主持下的鄉規民約。
儒家提倡禮法合治、德主刑輔。西周時即有“明德慎罰”思想,到孔子主張“為政以德”。董仲舒則在前人基礎上,通過陰陽學說論證“天人感應”,從而建立“陽德陰刑”的德主刑輔論,強調治國應以德政為主,刑殺為輔。[26]637-653在生態環境保護上,歷朝歷代從“節用愛物”和“生生之德”的角度制定了相關律令,要求人們從嚴遵守。
儒家經典《禮記·王制》中對生態保護作了總的要求。《禮記·月令》又對每個時令的生態保護進行了詳盡規定: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仲春之月,“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仲冬之月,“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季冬之月,“是月也,命漁師始漁”。[8]1357,1363,1365,1384
西南少數民族沒有統一的帝國政權,也就沒有相應統一的法律,但謀生的需要造就了他們對自然力和環境的絕對依賴,天地風雨、山川草木不僅是他們進行祈福避禍的對象,更是他們生存繁衍的現實需要。保護好生態,就是延續自己和家族生命的直接需要。為此,他們不再僅僅依靠內心的信念,更需要強制力的保護。
在民間,這些保護制度是通過以地緣關系為基礎的平等議事組織——“立款”(“洞款”、“會款”)、“議榔”制定出具體的“款約”、“榔規”,再通過口頭宣布、“埋巖”為證和立碑告示等方式形成習慣法,用于保護生態環境、規范社會道德、維護社會治安和對違反以上各類事件進行處罰。這些習慣法,對于該區域所有的村民,具有較高強制力約束。苗族《賈》說,“誰若做獸行,誰若當竊賊,捆他來對榔規,捉他來對場約”,“定拿他來罰榔,定拿他來游場,眾人好以為恥,大伙好以為戒。”[27]9
歷史上,少數民族早就制定了保護自然環境的習慣法:西雙版納傣文典籍《土司對百姓的訓條》規定:“童山的樹木不能砍,森林中間不能砍開樹,蓋房子在里面。”“砍掉別寨的童樹,需負擔該寨的全部祭費,若該寨死了人,按每人價格一千五百元賠償。”《青海藏區部落習慣法資料集》記載,毛埡地區土司規定,不能打獵,不準傷害有生命的東西,否則罰款。廣西金秀沿河十村茶山瑤規定每年釣魚期和攆魚期是二月村社以后至八月秋社止,其余時間不準撒網和用藥毒魚。[28]侗族村民公立于嘉慶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的錦屏縣“水口山植樹護林碑”規定:“大木如有砍盜者,罰銀三兩;周圍水口樹木,不許砍伐枝丫,如有犯者,罰銀五錢。”花溪苗族公立于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的“老關口寨鄉規碑”規定:“不準放火燒坡、亂砍樹木,如違,拿獲罰銀三兩。”立于咸豐五年(公元1855年)的興義市“綠蔭鄉規民約碑”不僅規定了具體措施,還介紹了立碑原因:“然山深必因乎木茂,而人杰必賴乎地靈。……在后龍培植樹木,禁止開挖,庶幾,龍脈豐滿,人物咸寧。倘有不遵守,開山破石,罰錢一千二百文;牧牛割草,罰錢六百文。”[29]
土家族地區,各地都制定有封山育林公約,條款具體,執行嚴格。封山區域,均立禁碑,標明四周界限。在許多碑約中,首條就說,為一方興旺,務請公眾遵守,否則:“斷子絕孫,死無葬身之地”。[30]140
在貴州彝區,習慣法將亂砍、濫伐視為犯罪,并作一系列處罰規定:縱火燒毀山林或濫砍破壞山林的,輕的賠償損失,造林償還,獻酒道歉;情節嚴重,毀林面積大,損失嚴重者,加處砍手或挖眼。毀壞宗族公有林木或神樹的,除對全族賠償、獻酒道歉外,還要處以包種新林、砍手等處罰。祭祀神樹費用由毀林者承擔,最嚴重的可將毀神樹的人殺祭神樹。[31]90
總之,西南少數民族無論在謀生、制度、習俗,還是在生態思想上,與儒家的生態文化具有很高的同質性。當然,由于儒家具有長期的文字、典籍和教育傳承,其生態文化顯得更成熟。但西南各少數民族由于擁有與大自然更為親近的生活和生產實踐,其生態文化顯得更豐富而實用。
因此,談到中華民族的生態思想,儒家與少數民族生態文化都是不可或缺的。
五、啟示與探索
在與大自然相處的歷史中,人類往往一方面依賴自然,另一方面企圖征服自然。最初,這與生產力低下,人類基本的物質生活得不到較好滿足有關。但隨后,人類變得越來越貪婪,甚至毫無節制地對大自然進行掠奪和破壞。造成了當下人類越演越烈的生態危機。
當代生態專家認為: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在人類文明的歷史長河中,曾經盛極一時的,如古埃及文明、古巴比倫文明、古地中海文明和印度恒河文明、美洲瑪雅文明等由繁榮走向衰敗直至相繼消亡,其原因雖不盡相同,但有一個共同點,即與生態環境變化相關,具體地說,就是過度砍伐森林、過度墾荒、過度放牧和盲目灌溉造成的生產力的衰竭。[32]5
在《致生態文明貴陽國際論壇2013年年會的賀信》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走向生態文明新時代,建設美麗中國,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重要內容。”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認為,儒家和西南少數民族生態文化完全可以為人類重建天人關系,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提供良好的借鑒。
通過前文闡述,在儒家和西南少數民族的生態文化和實踐中,我們可以得到人與自然良好關系重建的四點啟示:第一,自然是值得人類敬畏和效法的。沒有自然就不可能產生人類,離開自然人類無法生存。大自然不求回報的“仁愛之心”和“生生之德”即是人類應效法的最高道德。第二,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平等的。人和自然各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任何人類優于自然的思想都必須拋棄。第三,人與自然應該友好相處。自然為人服務,人也應順應自然原生的發展規律,友善相處,美美與共。第四,人與自然的發展必須是可持續的。人類應控制自己不合理的欲求,盡可能地減少對自然的破壞,確保自然的可持續發展,從而實現人的可持續發展。endprint
結合地方實際,本文就經濟社會發展中更加突出生態元素作如下幾點設想:
(一)建立西南生態文明發展試驗區,為人類生態文明建設作積極探索
2013年9月,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發表演講并回答學生問題時指出,“我們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而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2015年初,總書記在云南考察時又特別強調:“要把生態環境保護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態環境,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在生態環境保護上一定要算大賬、算長遠賬、算整體賬、算綜合賬,不能因小失大、顧此失彼、寅吃卯糧、急功近利。生態環境保護是一個長期任務,要久久為功。”[33]
作為當前自然資源原貌保存較好,甚至可以說我國僅存的一片生態凈土,西南的自然生態和民族文化的生存發展已面臨越來越大的挑戰,需要從國家層面為西南發展定好位,及時制定最嚴格的保護措施,編制生態文明發展規劃,明確保護區域,確定保護重點項目、實施步驟等,全面推進生態產業支撐體系、生態安全保障體系、綠色人居支持體系、生態文化支持體系、生態制度約束體系五大體系建設。
西南地區在全國經濟總量中所占比重相對較小,但自然生態資源非常豐富、民族原生態文化保存較好,建議國家結合西南實際,從頂層設計上改變對西南地區發展考核的指標體系,在國家已實施可持續發展實驗區、生態文明建設試點基礎上,參照世界自然遺產保護和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建設的成功經驗,為中華民族乃至全人類永續發展計,探索建立包括云貴川等在內跨行政區劃的西南生態文明發展試驗區。
(二)走創新趕超的可持續發展之路,徹底轉變粗放增長的功利思想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正確處理好經濟發展同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牢固樹立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的理念”。
西南地區應積極探索創新趕超之路,徹底拋棄依靠破壞環境、能源消耗換取經濟快速增長的功利思想,改變縣縣圈地辦工業園區的“火熱”現狀。雖然經濟發展相對滯后,但也決不能成為長三角、珠三角落后、淘汰產業的承接地,盲目跟風發展工業經濟,以工業成敗論英雄。我們當然也應該抓工業,但最好選擇在適宜地區集中發展高新技術產業,而非全面鋪開大辦園區。
從長遠來看,西南的生態優勢、民族文化優勢一樣可以成為發展優勢,甚至可以說,保持、發展好現有自然優勢才是真正的后發優勢。當前,西南地區可利用自身優勢,走生態發展、循環發展之路,積極改善基礎設施,加強鄉村環境治理,大力發展大健康產業、現代物流業、高新技術產業、莊園式生態農業、綠色經濟種植業、觀光休閑旅游業,打造中國休閑旅游避暑勝地、東亞會務中心、農耕文明和民族原生態文化體驗中心、山水田園養心中心等。
(三)樹立民族生態文化自信,倡導取用有節欲求適度的生活方式
一度以來,西南民族生態文化被外界視為落后甚至是迷信的象征。但通過前文分析,我們已經明白西南生態文化同儒家生態思想一樣,都具有極高的生存智慧和極其深刻的借鑒意義。為此,要大張旗鼓地提倡、宣傳儒家和西南民族優秀傳統生態文化,樹立民族生態文化自信,進一步增進文化自覺,促進中華民族從優秀傳統文化的覺醒與自強中走向偉大復興。
我們要通過積極的自我發動和廣泛的對外宣傳,讓優秀的傳統生態文化為更多的人所熟知和認同。讓更多的人主動參與到保護綠水青山的偉大實踐中來,讓更多的人理解并堅守取用有節、欲求適度的生活方式,讓浮躁的人心在山水田園中獲得寧靜,讓我們的家園真正成為人居環境優美、生態系統良性循環、城鄉統籌均衡發展、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典范,讓美麗中國之夢在我們身邊得以實現。
參考文獻:
[1]先鋒國家歷史雜志社主編. 國家歷史[Z].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
[2]吳國盛. 科學的歷程[M]. 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3.
[3]章太炎. 國故論衡·原儒[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4]胡適之. 大師說儒[M]. 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2008.
[5]李澤厚. 歷史本體論·己卯五說(增訂本)[M].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
[6]陳來. 古代宗教與倫理:儒家思想的根源[M].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社,1996.
[7]陳來. 儒家思想的根源及對此問題的研究·評章太炎、胡適之得失[Z]. 陳來講談錄[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8][清]阮元校刻. 十三經注疏[M]. 北京:中華書局,1980.
[9]顧久. 儒之原始及其對儒家的影響[J]. 貴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1994,(4).
[10]溫春來. 從“異域”到“舊疆”——宋至清貴州西北部地區的制度、開發與認同[M].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
[11]王明貴,王顯.《彝族源流·畢摩根源》(漢譯散文版)[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12]費孝通. 祿村農田[M]. 江村經濟(經典珍藏版)[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13][宋]朱熹. 四書章句集注[M]. 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版.
[14]馮友蘭. 中國哲學史(兩卷本上)[M]. 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
[15]喬清舉. 澤至草木恩至水土——儒家生態文化[M]. 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11.
[16]李民,王健. 尚書譯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7] [宋]張載. 正蒙·乾稱篇[Z]. 轉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兩卷本下)[M]. 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endprint
[18]于民雄注,顧久譯. 傳習錄全譯[M]. 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
[19]貴州省地方志編撰委員會編. 貴州省志·民族志[Z]. 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2002.
[20]王繼超,陳光明. 彝族古歌(上)[Z]. 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2013.
[21]喬清舉. 儒家生態思想通論[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22][清]陳立撰,吳則虞點校. 白虎通疏證[M]. 北京:中華書局,1994.
[23]周國茂. 自然與生命的意義世界[M]. 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2004.
[24]李立瓊. 從文化視角看云南少數民族的生態觀[J]. 昆明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 2007,(1).
[25]張慧平等. 淺談少數民族生態文化與森林資源管理[J]. 北京林業大學學報(社科版). 2006,(1).
[26]張世亮,鐘肇鵬,周桂鈿譯注. 春秋繁露[M]. 北京:中華書局,2012.
[27]王鳳剛. 苗族賈理·前言[Z]. 苗族賈理[M]. 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9.
[28]蘇欽. 淺談我國少數民族歷史上保護生態環境的特點及經驗[J]. 中央社會主義學報,2005,(4).
[29]盧延慶. 生態文明建設呼喚少數民族在場[N]. 中國民族報,2009-5-22(05).
[30]貴州省民族事務委員會編. 土家族文化大觀[Z]. 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2014.
[31]陳金全. 彝族仡佬族毛南族習慣法研究[M]. 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2008.
[32]王春益. 生態文明與美麗中國夢[M].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33]陳二厚等. 為了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習近平總書記關心生態文明建設紀實[N]. 光明日報,2015-3-10(01).
The Comparison of Eco-culture between Han Race, Confucianism , Minority Groups in Southwestern Areas and Priests
Gujiu Zhangbiao
(Guizhou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ureau, Guizhou Guiyang 550004)
Abstract: Beautiful Dream of China is deeply rooted with the ecosystem of civilization, while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 earth of developing the Eco-civilization. The minorities in Southwestern China is the main resource with Han Race, The Eco-culture is similar with it, the Eco-culture of minority groups are the same with Confucianism.It is quite wisdom,quite magnificent, it can be an excellent and forever borrowing for the mankind with their continu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Han Race; the minority groups in northwestern areas;Confucianism; Priests;Eco-culture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