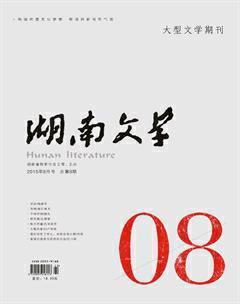付秀瑩的那一劍
吳鈞堯
文字江湖,人人都是練家子,路數與招法各異,但都求亮眼的一招。比如楚留香“彈指神功”、郭靖“降龍十八掌”、張三豐“太極拳”等。武學與文學不在一個競技場,但為了立身處世、揚名立萬的這一招,習武者得蹲馬步、練吐納,為文者必須遍覽群書,甚至手抄,一字一句透過腦、手傳譯而出,仿佛作者現身,于耳畔說話。臺灣有不少人這般苦練,大功告成者有之,沒沒于江湖者則不盡數了。
為何執于一點、迷于一招?主要是這個出招,不單是拳腳功夫,而是來自精氣神,三者融于一。以文學來看,就是明明白白告訴讀者作者是誰、用什么樣的腔調說話;落于故事者便是敘述風格與文字。我以為這像文章的兩條腿,缺乏鍛煉,任你情節再巧妙、內涵再豐富、人物再特別,都會缺乏一股韻味,而成了一款人人都在寫的文章。
有志、有識的作家都在擺脫蕓蕓之言,而能一字生風、一篇自成宇宙。作家要面臨的競爭者不單是同一輩中人,還包括已奠立聲名的前輩,于是,求一家之言的旅路,勢將越逼越險。但我們同時會看到,逼至險途,即柳暗花明,付秀瑩便在峰回路轉處,再造她的芳村天地。
我曾于二〇一四年四月,于杭州與付秀瑩匆匆一會。因為著實匆促,致十二月在臺北文學座談會再見時,我忘記見過的那人是付秀瑩,她則錯認攝影者是我。幸而,她在人間出版社出版《愛情到處流傳》,透過文字閱讀,不但不再錯認,而且,讓我大大震驚。
根據《愛情》一書的后記,以及我掌握的網絡數據,這讓人驚艷的作品竟然是付秀瑩第一篇作品。付秀瑩從中學起,便對文學感興趣,得過幾回校園比賽的獎項。二十六歲那年,她的人生大決定是離棄安穩的英文教師工作,報考文學研究生,且一試中的。在學期間她以評論家自我期許,沒料到而立之年方過,發表成名作《愛情到處流傳》。我好奇,她求學期間經歷了什么鍛煉,繼而選擇了創作而非評論?當她正襟危坐,寫下《愛》的第一句、第一行時,心里頭有無刀譜或劍訣?
臺北聚餐時,付秀瑩嘟嚷著說,她更愛的是《舊院系列》《醉太平》以及《鷓鴣天》等等,對于眾人溢美的《愛情到處流傳》倒似有了意見。這情景,猶如為人父母者都偏愛最小的子女,而老師傅門下的小師妹總集萬千寵愛。我跟她說莫偏心,《愛情到處流傳》可當作大哥、大姐,或者大師兄了,當家門衰疲,必須大哥與大姐撐起;若師傅遠途或閉關,得大師兄代師傳藝,《愛情到處流傳》火侯純熟,確有一夫當關、一劍幻萬劍的氣勢。
臺北餐會時,付秀瑩簽了小說送我。一邊是封面里頁,印有她劉海拂面,越是遮掩、越見美麗的照片;一邊是書籍扉頁,寫上我的名字、她的落款。我不禁感嘆,如此才貌佳人,竟是同行中人:我們寫了不少好故事,但總寫不好自己的名字。
近年來,常參加大陸文學交流,但見過兩回,出版繁體字小說者,著實很少。不由得讀了起來。付秀瑩成名作《愛情到處流傳》出招很緩,幾近平淡家常,“那時候,我們住在鄉下。父親在離家幾十里的鎮上教書。母親帶著我們兄妹兩個,住在村子的最東頭。這個村子,叫做芳村”。但是,付秀瑩的腔調浮出來了。不浮夸,敘述常見直白,無法言說的哀戚跟歡喜,就不費心布局了,直接說“很歡喜”“很恨”不就結了。但寫景詩意、寫人利落,文字精簡處卻疏落有致,猶如人睡足了,翻了個身,踩著地板。這一沾踩,時間跨出去、空間生出來了。
小說家都必須營造讀者從容回身的空間,指著樹說那是什么樹、指著人說那些是什么樣的人。這樣的基本構造,常讓作家調用大量修辭跟技巧,寫外在、內在,氣味、形態等,但付秀瑩卻緩吞構建芳村的人、事、地、景以及情。地景于是浮雕。空間搭建出來了,人物怎么拐彎、季節如何浮動,芳村的人物便永遠留駐芳村里。這得是一篇活的小說,才能活著一群人。
付秀瑩敘述風格是神閑氣定,從容復從容。有一種演了出好戲,不來看,是觀眾自己損失了,字句間遂自信、自在。于是付秀瑩的“說”,便非常自我的,談芳村習俗、談主角父母親、聊村人怎么促狹“聽房”等。幾個很簡單用句,小學生作文課也用的,比如“你相信嗎,世上有這樣一種女人”“我忘了說了,四叔,四嬸子的男人,早在新婚不久,就辭世了”。這是非常基本的運用,但必須使在恬淡的說書氣氛中,才能相得益彰,讓作者跟讀者站一塊,讀者讀文至此,不免莞爾,作者也有記不穩、說不準的時候,而面對潮潮舊事,誰不是這樣一次一次,自我修正?
這款技法不宜用老,幸而《愛情到處流傳》之后的篇章,它們很少出現了,倒是有一個我以為是神筆勾勒的方式,經過《愛情到處流傳》的沉淀,而能熟稔駕馭,幾乎是有意識地出現在其他篇章,比如《醉太平》,“漸漸地,就有那么一點悠然心會的意思了”。《琴瑟》,“小孩子還在哭,直著個嗓子,明顯沒有了先前的氣焰,卻還是勉力支撐著,有點示威的意思,聲音里盡是疲憊”。《紅了櫻桃》,“白嫩的皮膚,吹彈得破,動不動,臉上便飛紅了,另有一種招惹人的意思”。這意思啊,便撰寫了付氏風格,而以一種思維、一種故事腔調,流貫所有篇章。這“意思”,看似簡單,卻是主觀投入、再客觀刻畫,在修辭上,仿佛減了好幾筆,但又增色好幾分。付秀瑩的小說,便以不說的說,但說得更多。
我必須點出的是,付秀瑩的人物塑造,是有那么一點章回人物的意思了(借用一下付氏風),寫婦女生氣,常見咬碎一口銀牙、或者跺了跺腳,以前衛生習慣糟、現在美食誘惑多,能有一口銀牙者,著實太少了。另外的意見是,適當留缺,自能留給讀者跟主角,另一個柳暗花明,事事寫足了,路也就轉得少了。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我參加座談會,針對對大陸小說發表看法,曾提列“題材的細微化”“生活慢下來”“舊事物的溫度”以及“人情世故再發現”四點說明。七〇后作家已走出洶涌的大時代,而有自己的小時代。大、小不在辨識好壞,而在取擇新視角,介入小說世界,故能品嘗平凡與陳舊的美好,發覺故事就在生活周遭。付秀瑩在鄉村發現了愛情。發現平凡人家的父母親,不平靜的光陰,了無新意的莊稼跟蘆花雞,它們的沉默跟喧嘩,滿是回憶的氣味。
每想到付秀瑩的《愛情到處流傳》,常聯想著武俠奇葩古龍。他形容小李飛刀有多快、說中原一點紅那一劍有多快,常說那一劍很快,世界上再沒有更快的劍了。付秀瑩這一劍不快,但很準,再套用付氏腔調,這劍不快的,但讓人避不開,這就是把一萬招,練成一招的意思了。
付秀瑩是貌美的。若要我說,我會以“定”“靜”形容。那像是滿月之余,中庭一樹新綠,樹漾著淡淡銀光,樹也漾著它本身的底綠。于是我知道當有這么一天,當她是太陽了,她的底色、她的謙卑與樸實,不會改變。付秀瑩在臺北倒是發生一件事,而且對女人來說,是終身大事了。她在房間煮飲水不當,手臂燙傷了。幫她敷藥,是參訪團的大事,得有女同志在旁監管,才能讓略識醫理的男同志代為料理,且片刻不得停留。二〇一五年元月底,應某雜志邀約,赴北京會議,曾于東來順一塊吃火鍋,問起傷勢,但見水舞已成熱舞,下半生,都將留有這個疤了。
我感到深深抱歉,才來臺灣一回呢。她拿出保溫瓶說,這就是禍首。禍首保溫瓶仍被使用著,而沒有摔毀,或棄而不用。這讓我想起一月到北京,曾以微信聯系,飯店地點偏僻房間又小,禁不住怨了兩句,她當時來了訊,房間雖小,但還能裝得下你吧?
我剎時愧窘。使好寫字的劍,不全部來自文學的種種度量,更由一種心性掌握了。我一個不留神,便受了付秀瑩兩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