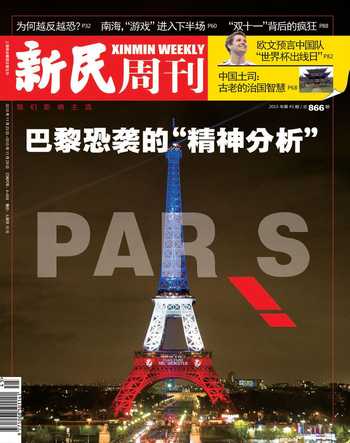韓國患了諾獎焦慮癥
詹小洪
韓國高麗民族是個爭強好勝的民族,事事不甘人后。可不是,經過幾十年的經濟高速發展,韓國早已經從發展中國家畢業。如今經濟總量居世界十三四位,涌現出了一批像三星、現代、LG這樣世界級的明星企業;歷屆奧運會上金牌沒少拿;韓流文化更是在各大洲產生了廣泛影響。翻開當地的報紙,不難看到宣稱韓國正在成為一個“發達”、“先進”、“比肩歐美日強國”的國家的報道。
然而,有一件令韓國人極為尷尬的事,韓國尚未實現諾貝爾獎零的突破。除了在2000年,韓國時任總統金大中先生與朝鮮金正日委員長成功地進行了南北民族和解的會談,大大緩和了南北韓關系,因而榮獲了該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外,迄今韓國人與被稱為諾獎之魁的文學獎、經濟學獎以及自然科學獎項無緣。
可環顧四鄰,日本先后已有21人獲諾獎,印度有人獲諾獎文學獎和經濟學獎,巴基斯坦科學家得過諾貝爾物理學獎,2012年,中國的莫言也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韓國依然是零。因此早日獲得諾貝爾獎就成了韓國國民共同的心結。每年10月各項諾獎發布的日子,韓國可以說是萬眾翹首以待。
在今年10月諾獎發布季, 韓國的諾貝爾獎的夢想再次打了水漂。中國藥學家屠呦呦獲得了諾貝爾生物學或醫學獎,日本又有兩名科學家獲得諾獎了。鄰國的成就對韓國震動特別大,韓國網絡上出現了將韓日和韓中獲獎人數進行比較的“0:21”和“0:2”等說法。韓國人正以羨慕的眼光,眼巴巴地望著中國、日本科學家攀登上世界科學最高峰。
韓國人百思不得其解,政府對科研投入力度相當大。據韓媒披露,韓國對研發投入近年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15%,居世界首位,投入的絕對值也居第七位。這么大的投入,加上舉國對諾獎的重視,在韓國人看來,韓國人中出個把諾獎得主似乎無可爭議。
韓國甚至想過一些不太切實的途徑問鼎諾獎:如為了認識諾獎委員會委員,集體訪問瑞典“攻關”;“實行舉國體制”,像奧運會國家隊加強訓練一樣,設立特殊機構,以諾獎為目標進行研究。如2008年,韓國教育科學技術部就提出一份長達189頁的《諾貝爾科學獎分析及接近戰略研究》報告,闡述了“培養韓國人諾貝爾科學獎獲得者的戰略”。
韓國媒體將上述焦灼的心情以及為獲獎采取的舉措稱為“諾貝爾獎焦慮癥”。
韓國人在反思,為什么政府該花的錢沒少花,可是現實仍然這樣殘酷,始終出不了世界級的研究成果和原創技術,乃至諾獎總不眷顧韓國科學家。韓國輿論界認為主要原因有:
政府對基礎理論研究重視不夠。韓國政府對科研投入的資金確實很多,但是研發投資的三分之二被用于應用技術的開發。韓國社會過度看重短期成果,研究人員急功近利,為了保證獲得研究經費,都致力于研究可以短期內出成績的課題。
韓國人重模仿輕創新。韓國社會蔓延一種“模仿”習性,在韓國模仿發達國家的創意或者商品的方式一直都很行得通,這成了諾貝爾科學獎獲獎路上的絆腳石。模仿風在像三星電子、現代汽車、POSCO等韓國內業界首屈一指的企業中也不例外,就有很多因為致力于模仿而大獲成功的產品。
痛定思痛,韓國政府再次振作起來要向諾獎發起新的進攻。10月22日,在青瓦臺,召開了“第27屆國家科學技術咨詢會”,樸槿惠總統在會上表示,“應積極培養有望向諾貝爾獎發起挑戰的世界頂級研究者,以優勢領域為中心,加強確保世界級水平優勢的戰略性支援”。
會上,韓國政府作出了啟動“Next-decade-100”項目的決定。即韓國推進支援1000名年輕研究人員的國家級項目,項目名稱為“Next-decade-100”。該項目計劃每年挑選100名30歲左右的研究者,給予5年內的研究經費支持。這一項目將在今后10年內持續每年選拔100名研究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