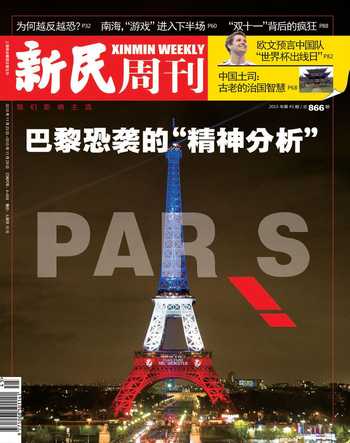“超前遏制戰略”與南海對峙
倪樂雄

中美軍方有聯合有遏制。2015年11月7日上午10時,美國佛羅里達梅波特港東南海域,中美海軍聯合演練在這里拉開序幕。中方濟南艦、益陽艦與美方參演三艦正在組成單縱隊航行。
美國對南海的思維和行動
在中美兩國首腦一來一往高潮迭起的互訪后,在雙方都給予對方極高訪問規格以及禮遇后,盡管雙方做盡了兩國關系不錯的姿態,但是,10月27日,美國海軍終于冒險駛入揚言已久的中國南海人工島礁12海里內,以罕見的直接挑戰中國領海主權的方式強硬表達了自己的意愿。
凡事先講道理,中國不是第一個在南海填海造島的國家,越南、馬來西亞和菲律賓都先于中國動手建造,另外,日本不是也在西太平洋沖之鳥礁填海造島么?那時美國既不制止、也不呼吁各方停止造島,更沒指責它們妨礙航行自由和威脅周邊國家,也不曾揚言駛入這些島礁的12海里之內。等到中國開始填海造島了,美國卻來干涉了、主持公道了、強調航行自由了、認定是威脅周邊國家安全了。顯然,美國的干涉中國填海造島的行為是赤裸裸地奉行雙重標準、故意偏袒,蠻橫壓制中國。美國并非不知道南海自古屬于中國,也知道越南曾經承認后又反悔的經歷。美國應該知道自己在南海問題上對中國的做法十分過分,但卻偏偏要這樣做。這就需要搞清美國決策者在南海爭端方面支配他們行動的思路。
觀察中美關系互動時,不難發現,美國兩次大戰的經驗教訓對他們行動的指導。美國可能、也應該從兩次世界大戰中總結出以下教訓——由于在德國和日本崛起的萌動狀態時,美國沒有及時采取強有力的遏制措施,以至兩國坐大后發動擴張性戰爭,以至在一戰時遠涉重洋赴歐洲作戰,以及在二戰時被迫開辟歐、亞兩個戰場,弄得十分被動,因此,面對一個崛起的對手,必須在崛起的萌動狀態即給予強有力的遏制。這就是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得出的經驗教訓。因為對手在羽翼未豐之際,即使自己付出再大的代價,也比對手羽毛豐滿后再動手的代價要小得多。
筆者曾判斷,只要上述姑且稱之為“超前遏制戰略”思路支配著美國的決策者,那么美國一定會在它所判斷的中國“擴張”的一開始就會采取強硬行動。在敵意支配下,美國不會理會南海人工島礁上的夜間導航等民用設施,只對中國在南海空中、海上作戰的前進基地猛地向前推進了1050公里感到憂心忡忡,只會把中國頗有誠意的“永不稱霸”、“和平崛起”、“建立新型大國關系”當作忽悠,甚至把“一帶一路”看成是當年日本提倡的“大東亞共榮圈”。這種“超前遏制戰略”指導下,美國在南海“填海造島”問題上偏袒某些東南亞國家,持雙重標準、強詞奪理壓制中國就一點也不奇怪了,所謂“國家利益高于一切”,并非美國不明白南海的是非曲折。在南海講公平、講正義、講公道、講尊重主權、講一碗水端平,那就等于顛覆美國的國家大戰略。
美戰略愿景對中國的傷害

中美海軍聯合演練拉開序幕。濟南艦信號兵升起信號旗,與“梅森”號進行信號通信演練。
如果美國一意孤行,中國將受到怎樣的傷害?美國進入中國南海人工島礁12海里內,挑戰中國主權僅僅是手段,目的是不允許中國在自己主權范圍的南海建軍事設施,其性質是迫使中國某些地區成為“非軍事化”地區。不管濫用何種理由,這種做法嚴重損害了中國的尊嚴和主權完整,并帶有赤裸裸的欺凌和侮辱成分,因而讓中國難以忍受。因而,此次南海焦點是美國“超前遏制戰略”與中國尊嚴和主權完整的尖銳沖突。
一個主權國家接受他國在自己領土上“非軍事化”的苛刻要求,往往是在戰敗的情況下被迫接受的,如海灣戰爭時,西方聯軍擊潰了薩達姆的軍隊后,美、英等國在伊拉克南部北緯33度線以南設置了“禁飛區”,不準伊拉克空軍進入。
“一·二八”淞滬抗戰時,中國第十九路軍在上海奮起抵抗侵華日軍,終因日軍在瀏河登陸、腹背受敵被迫后撤。中日雙方簽訂的《淞滬停戰協議》規定:上海劃為“非軍事區”、第十九路軍撤防、劃上海為非武裝區;中國不得在上海至蘇州、昆山一帶駐軍。國人視為奇恥大辱。
由此可見,美國在南海遏制中國的行為、以及不準許中國在自己領土上修建軍事設施的蠻橫要求,帶有侮辱中國尊嚴和侵犯主權的性質,除非戰場嚴重失利,對方處于壓倒性優勢,不然任何國家都難以接受。不戰而接受此苛刻要求是懦夫,戰敗被迫接受,勉強可以被人諒解。
中國如何尋找到平衡點

2015年2月24日,美國海軍F/A-18E戰斗機與兩日本航空自衛隊F-15J在沖繩進行空戰訓練。
美國在南海問題上對中國取咄咄逼人的姿態還有另一方面的原因,他要向亞洲國家表明:雖然在烏克蘭問題上受到俄羅斯的牽制,特別在中東亂了章法搞得一團糟,且被俄羅斯乘機滲透,但在亞洲自己仍然是“帶頭大哥”,只要姿態到位即可。同時一定程度上希望同中國一起致力于建立新型大國關系,因此戰爭沖突的選項一般不在考慮之內。人們應該清楚,擺出打架的架勢是一回事,是否愿意打架又是另一回事。畢竟“自古知兵非好戰”。
中國有著和平崛起的極大愿望,且認真地嘗試著同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系,避免重蹈歷史上大國之間的“修昔底德陷阱”。中國在當下和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里,仍然致力于國內和海外經濟的調整和布局,且處崛起的初期階段,無論從實力和時間看,收復老祖宗留下的南海失地的各種條件,尚未到瓜熟蒂落的時刻,只要維持住爭端現狀,無礙大局。不到萬不得已也不會輕易考慮戰爭沖突選項。
接下去對于中美兩國來說就是在不發生軍事沖突的前提下,如何在本國和世界面前維護各自尊嚴的問題了。美國要維持“帶頭大哥”的“尊嚴”,中國要維護主權的尊嚴。在“有驚無險”的框架里,雙方的姿態一定都是強硬的,一定會用先進的軍事裝備作道具,竭盡全力地擺出強硬架勢。目前,第一回合已顯出雙方今后的周旋模式,美方來碰底線,中方立即驅逐加警告。底線可以碰,但不能穿越。
另外,中國巡航釣魚島后的中日周旋模式,十幾年前臺海危機時候,從劍拔弩張到今天的相對風平浪靜,都可作預判的參考。尤其是臺海危機的解除,可以看成是中美在臺海問題上共同尋找平衡點的過程。這些都可以做參照,或許,此次中美對峙,也是臺海危機的翻版,是雙方在南海尋找平衡點的過程開始。
正常情況下,中美不會在南海大動干戈。自從核武器時代開始,核武國家之間只有“代理人戰爭”,還沒有直接發生過戰爭沖突,究其原因是所爭之利與核戰爭之害相差太大,比如蘇美對抗時,核戰爭雙方巨大毀滅性的代價僅僅為了爭哪種制度更好,而哪種制度下人們都能衣食無憂地活著,只是質量有差距,核冬天里人們都不能活著。所以不是人們的愿望、而是核武器強有力地約束著核國家之間的戰爭沖動,迫使沖突雙方竭盡全力地維護和平。
此外,南海危機比起“臺海危機”,對中美兩國來說都是小巫見大巫,那是分裂與反分裂沖突,性質和烈度比12海里糾紛強得多,但是中美兩國居然有驚無險地度過了,大江大海都過來了,南海“小河溝里”中美關系至少短期翻不了船。至于長期而論,中美海權戰略沖突是否最終化解、或最終在未來哪個時間攤牌,目前無解。
歷史的經驗是,處于崛起萌動期的大國必須忍辱負重、必要時“忍氣吞聲”方能贏得未來的決定性轉機。1805年,處于萌動期的普魯士蠢蠢欲動,欲乘法國拿破侖與俄國、奧地利交戰之際,配合俄、奧軍隊夾擊拿破侖的法軍,當它的使者帶著給法國的最后通牒走到半途中,拿破侖大軍已在奧斯特利茨會戰中擊潰了俄奧聯軍,普魯士使者到達拿破侖軍營時態度急轉,把履行參戰程序的最后通牒宣讀,改為向拿破侖祝賀勝利,拿破侖傲慢地奚落道:“你把祝賀的對方弄錯了吧?”普魯士使者戰戰兢兢、唯唯諾諾而退。65年后,1870年9月2日,普魯士軍隊在色當同法國軍隊交戰大獲全勝,俘虜法國拿破侖三世皇帝和他的近十萬大軍,普魯士完成統一,建立德意志帝國。法國為半個多世紀前的傲慢付出了沉重代價,普魯士當初的忍辱負重贏得了半個世紀后的輝煌。這段歷史上主客互換的故事,很值得回味。(作者為著名海權戰略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