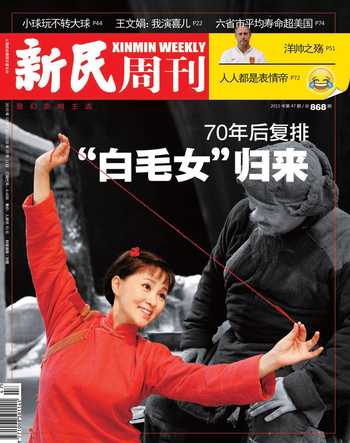張復(fù)興水鄉(xiāng)繪畫的美學(xué)品性
毛時(shí)安
寒潮來襲,于12月11日在上海圖書館開幕的《似水流年——張復(fù)興江南水鄉(xiāng)畫展》或許會(huì)給人們帶來些許暖意,展覽的80件作品充滿了陽光,浸潤了水氣,寄托了游子的情懷以及對故園的眷戀。
對張復(fù)興的作品我是不陌生的,我常在張復(fù)興創(chuàng)造的藝術(shù)世界里徘徊,思考著他的江南水鄉(xiāng)作品中獨(dú)特的美學(xué)品性。當(dāng)下,在相當(dāng)多的畫家把眼光投向水鄉(xiāng)的時(shí)候,也許是基于一種歷史主義的懷舊情緒。在那些作品中,江南的人文景觀是主角,而自然景觀只不過是人文景觀登場時(shí)的背景,充其量也只是配角。于是我們看到,納入他們創(chuàng)作視野的,總是蒼苔斑駁的老墻,沿河老屋子衰朽的背影,圖案古雅的窗欞,染著歲月蝕痕的廳堂門楣……他們不厭其煩地用極其精細(xì)寫實(shí)的筆觸,傳達(dá)著能激起每個(gè)現(xiàn)代人狂熱懷舊情緒的肌理效果。
在這些畫家熱衷于復(fù)述著老屋歷史故事的時(shí)候,張復(fù)興卻獨(dú)鐘情于江南水鄉(xiāng)自然詩篇的抒寫。他更看重更傾心于江南水鄉(xiāng)無處不在的生態(tài)和自然環(huán)境,月光下靜謐的河灘,流云下沙沙搖曳的蘆葦,叢叢綠樹婆娑的漁村,漫不經(jīng)心伸下小河的石階,被江南濕潤春風(fēng)染得柳綠桃紅的時(shí)光……他也畫烏瓦粉墻,也畫那些身姿優(yōu)美虹影般拱起的老橋,但他從來不渲染它們的細(xì)部。他把它們有機(jī)融進(jìn)大自然之中,成為自然和諧中的一部分。在他心目中,主宰江南水鄉(xiāng)的主人是水,水才是他藝術(shù)世界的真正主角。因?yàn)樗拇嬖冢械囊磺芯拔锒家劳兄及l(fā)生在水邊。水使所有的景物都變得空蒙靈動(dòng)透逸滋潤起來,也使得所有籠罩在水氣中的景物變得線條輪廓夢幻般優(yōu)美地模糊晃動(dòng)起來。
而且在技術(shù)處理上,他總是十分機(jī)智地利用留空布白,化實(shí)為虛地為水的表現(xiàn),提供著巨大的空間。從傳達(dá)這種美學(xué)旨趣出發(fā),張復(fù)興不僅利用宣紙和水墨的特性,創(chuàng)造性地運(yùn)用了一整套表現(xiàn)水的獨(dú)特技法,而且獨(dú)出機(jī)杼地創(chuàng)造了仿佛自天而降的“無根樹”和大團(tuán)塊流動(dòng)于高天的“蒙鴻云”的意象。那么,同是江南水鄉(xiāng)的作品,我們卻看到了完全不同的價(jià)值取向。早在二晉時(shí),就有哲人提出“山水以形媚道”的至理名言。在我看來,一個(gè)真正的藝術(shù)家,總是本質(zhì)上的人本主義者加自然主義者。

這里還要指出的是,江南風(fēng)景在張復(fù)興那兒不是外在的。他不必像有些畫家那樣,因?yàn)檫@題材有商業(yè)上的暴發(fā)價(jià)值而去尋找,也不必像一個(gè)對江南一無所知的人那樣僅僅出于獵奇的心理,人為地去標(biāo)新立異。作為藝術(shù),它們可以很精致,但卻常常缺乏激動(dòng)人心的內(nèi)在生命力。中國藝術(shù)美學(xué)的核心是“意境論”,意境是通過情景關(guān)系的融洽來實(shí)現(xiàn)的,“景無情不發(fā)”。
張復(fù)興是浙江紹興人,又長達(dá)十年在上海近郊青浦工作,紹興與青浦都是典型的江南水鄉(xiāng)。江南水鄉(xiāng)之于張復(fù)興已經(jīng)成為了人生積淀和生命檢驗(yàn)的基本構(gòu)成要素。畫江南,對于張復(fù)興來說,只不過是一次長期蟄伏心底的童年情結(jié)的噴發(fā),一次精神家園的靈魂重游,是一次美學(xué)上的移情。他只需把曾經(jīng)有過的生命體驗(yàn)和激情投身到那些水、橋、民居上去就可以了。所以,他總能將筆深入到水鄉(xiāng)似水柔情的本質(zhì)的深處,總能抓住最讓人靈魂顫動(dòng)的片刻和最讓人精神沉浸的場景。由于這種強(qiáng)烈的內(nèi)在生命體驗(yàn),張復(fù)興就可以不去追求外在的形似,而去做一種整體印象的抒情性再造。誠如莊子說的那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甚至可以像羅蘭·巴爾特那樣,為了想象,犧牲了形象。既然每次在宣紙上縱筆揮灑,是一次“神游”的過程,那么我們這些觀者也自然可以面對張復(fù)興的水鄉(xiāng)的世界,領(lǐng)略到一份“神游”的愉悅了。
信息
想象突圍現(xiàn)實(shí)
——龍美術(shù)館藏亞洲藝術(shù)作品展
龍美術(shù)館亞洲當(dāng)代藝術(shù)館藏作品展從11月28日起至明年2月28日,展覽將從物質(zhì)化的體驗(yàn)出發(fā),通過強(qiáng)烈的環(huán)境性與時(shí)間性感受,未完成與即興式肌理,激發(fā)觀者全新的想象。展覽第一部分將聚焦白發(fā)一雄、田中敦子等一批活躍于二戰(zhàn)期間的藝術(shù)家。他們致力于在畫布與身體間構(gòu)筑一種新的直接聯(lián)系。第二部分則將視線投向那些透過直覺和材料本身,去摸索自身與世界關(guān)聯(lián)的認(rèn)識(shí)論證明的藝術(shù)家們。呈現(xiàn)李禹煥和菅木志雄等“物派”藝術(shù)家的作品。并依據(jù)這一線索,帶來劉韡、呂振光、名和晃平等一批亞洲當(dāng)代年輕藝術(shù)家的創(chuàng)作。第三部分聚焦草間彌生、奈良美智、馬君輔通過潛意識(shí)的圖像,不定的形式,童稚及本土化的視角,即興與看似不拘的涂鴉筆法,打開一扇從想象通往現(xiàn)實(shí)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