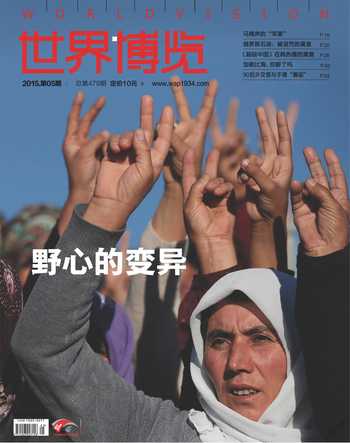俄羅斯深陷“石油陷阱”
馬堯

導語:石油這個不知道應該是頌揚還是該詛咒的黑金就這樣使一個曾經的世界超級大國淪落到以出售石油和軍火度日的國家。
提起俄羅斯這個世界上領土最遼闊的國家,人們總是情不自禁地將其與石油為主的能源聯系在一起:中日“安大線”、“安納線”之爭、俄羅斯與歐洲國家的石油貿易、美國操縱國際油價下跌打擊俄羅斯經濟……俄羅斯這頭白色的北極熊與石油這種黑色的“液體金子”越來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可以說,以石油為首的能源出口不僅是俄羅斯的“錢袋子”,而且也是俄羅斯的“大棒子”。然而,“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從蘇聯時代開始,俄羅斯民族既從石油中賺取了大量利潤,也因此吃盡苦頭。
揮霍方式使用石油財富
能源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石油則是最常用、最安全、使用成本最低的能源之一,無論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還是國家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都越來越離不開石油。可以說,石油是最重要的戰略性資源,誰控制了石油,誰就掌握了全球競爭的制高點,占據了國際關系的有利地位;誰控制了石油,誰就掌握了戰場主動權,扼住了對手的生死命脈;誰控制了石油,誰就控制了財富,有了經濟健康穩定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保證。石油是一種特殊的商品,具有不可再生、儲量有限、供需錯位三大特點。石油因為不同于大眾商品,使其成為準國際貨幣,成為油權強國控制石油貿易和定價的特殊工具。
世界石油工業歷經近150年的發展到20世紀末形成了以北美、亞太、西歐為主的世界石油消費區域構成格局和以歐佩克等為主的世界石油儲產量區域構成格局。目前北美地區是世界最大的石油消費區,亞太地區位居第二,西歐第三。這三個地區占世界石油消費總量的近80%,其石油剩余探明儲量僅占世界總量的22%。歐佩克的石油消費量不到10%,但這些國家卻占世界石油探明儲量的2/3。世界石油的消費區域構成與資源區域的構成嚴重錯位和失衡,使全球圍繞油氣資源的爭奪一直非常激烈,也使對原油進口依賴程度較高的國家一直面臨著壓力。
由于石油具有的特殊戰略價值,世界石油中心同時也成為各種政治力量爭奪的焦點。而世界石油中心的每一次轉移都導致了世界地緣政治格局的相應變化。今天,從北非的馬格里布到波斯灣,從波斯灣到里海,從里海到外高加索,再到俄羅斯的西伯利亞和遠東,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石油富集地理帶。這個巨大的地理帶蘊藏了65%的世界石油儲量和73%的天然氣儲量。在這種意義上,可以把北非——波斯灣——里海——俄羅斯稱為“世界石油供應心臟地帶”。
在蘇聯時代,石油就對這個世界最大的陸權國家產生過巨大影響。猛增的石油收入作為一筆經常性的“意外之財”,讓蘇聯領導層更愿意通過進口而不是自行挖潛和進行結構性調整,來解決國內面臨的各種經濟問題。本來應該通過改革加以解決的經濟社會問題被長時間地掩蓋了。蘇共中央將糧食缺口、消費品缺口、工業設備缺口的解決路徑和石油貿易結合在一起,完全漠視蘇聯人民的生活水平、收入水平的提高應當建立在勞動生產率而不是粗放性的資源經濟基礎上。領導人以近乎揮霍的方式使用石油財富,整個經濟的效率急劇下降。
滾滾而來的石油美元,一方面使蘇聯在對外援助、擴充軍備方面越來越慷慨,以霸權主義者的做派干涉國際事務的尺度越來越大;另一方面又使政府肆意通過補貼和進口,來扭曲糧食和消費品的生產,國民經濟越來越畸形,消費越來越嚴重。70年代初,蘇聯60%的外匯收入來自于針對西方的油氣出口。在1973年的幾個月里,原油價格從3美元快速拉升至12美元,漲幅達到400%,對于石油價格絕對不會回落的猜測,導致了蘇聯國內的相關制造業快速膨脹。而時值冷戰中期,蘇俄的核武器庫實際上大多也是建設于這個階段。石油出口的收入,成為了蘇聯賴以維持軍備建設的關鍵。然而好景不長,85年,軍備競賽如火如荼的檔口,美國誘使沙特大量增產,導致油價從30美元快速暴跌至10美元,盡管之后一度反彈回15美元,但是仍然無法拯救蘇聯財政垮臺的宿命,4年后,蘇聯解體,美國贏得冷戰。人類從此進入后冷戰時代。
石油與俄羅斯的內政外交
繼承了蘇聯主要的軍事、經濟和國際地位的俄羅斯聯邦也繼承了蘇聯的能源國地位。如今的俄羅斯是世界第二大原油生產國,年產原油5.5億噸左右,僅次于沙特阿拉伯。原油是俄羅斯的首要能源,也是重要的出口物資,年出口量約1億噸左右。原油工業在俄羅斯國民經濟中居重要地位,是重要的支柱產業部門。就目前而言,石油和軍火一道構成了俄羅斯經濟的兩大支柱。
在整個俄羅斯都在進行社會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俄羅斯的石油工業逐漸形成了多個大型垂直一體化石油公司,從根本上扭轉了石油天然氣生產行業出現的下降趨勢。在俄羅斯進行90年代“休克療法”、21世紀初的經濟恢復過程中,石油天然氣工業促進了俄羅斯財政和對外經濟形勢穩定,保證了工業生產,財稅收入和對外貿易。可謂是居功至偉。不過,更加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俄羅斯的石油天然氣行業開始在俄羅斯的外交領域發揮著比前蘇聯時期更大的作用。開始修建于上世紀70年代的俄羅斯通歐天然氣管道為歐洲諸國能源消費從煤炭向石油天然氣轉型,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從21世紀開始,這條管道對歐洲不僅意味著一條能源通道,更是俄羅斯與西方世界博弈的重要砝碼和對自己不聽話的獨聯體“小兄弟”使用的“武器”。盡管歐盟和獨聯體國家都開始有意識的擺脫對俄羅斯油氣的依賴,但是這都是很難一下子做到的。對于俄羅斯來說,原油和天然氣還有一個巨大的作用,就是它是俄羅斯有效緩沖歐盟關系的橋梁。在對克里米亞問題上,歐盟方面遲遲無法做出統一的對俄制裁態度,其實就是考慮到,不少國家天然氣、石油對俄羅斯的大比例依賴。
以石油問題為核心的能源安全問題是俄美關系中的一個潛在沖突領域。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發生后,美國提出了所謂的“能源安全”理念,主要是實現能源來源的多元化,確保能源的獲取,必要時使用武力保護能源利益以及發展替代性能源首先是原子能等。2005年,俄羅斯提出,對能源安全的理解應當有所變化,需要更多地考慮能源出口國的利益。在2006年7月“八國集團”彼得堡峰會上,俄羅斯成功地將能源安全新理念寫進了峰會文件中,確保能源從開采、運輸到分配等各個環節的安全。進入新世紀以來,能源逐漸成為俄羅斯對歐洲特別是對前蘇聯某些國家的外交武器,針對俄時常揮舞的“能源大棒”,華盛頓也是作出了各種抵制方案:從與俄羅斯的能源沖突中站在烏克蘭一邊,到激勵土庫曼斯坦建立繞過俄羅斯的石油出口體系等。
2008年,石油價格暴漲到140美元1桶,俄羅斯因此賺得盆滿缽滿,美國吃驚地發現,靠著賣軍火和石油的北極熊回來了,并且又在中東站穩了腳跟。而且俄羅斯軍力有借此復蘇的跡象,其年度軍費開支最多達到900多億美元,僅次于中美,位居世界第三。俄羅斯的海空軍甚至有恢復對美國周邊海空巡邏的跡象。這對于美國的霸權可絕不是什么好消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于是美國通過種種手段對世界石油價格進行打壓,包括動用戰備油井和石油儲備、開發頁巖氣、降低需求等手段,石油價格應聲下跌,俄羅斯因此遭受巨大損失。根據俄羅斯聯邦儲蓄銀行的計算,如果原油價格維持在90美元/桶,2015年俄羅斯財政收入將因此減少1.5%。原油價格需要維持在104美元/桶(俄羅斯人自己認為其財政運行的基礎是建立在石油每桶70美元的價格之上的),俄羅斯才能維持收支平衡。
要是這次真的暴跌回60美元,那么意味著俄羅斯將面臨巨大的財政危機,深度衰退,大規模的經常帳和財政赤字,巨額資本外逃都將成為可能。北極熊對黑金可謂是又愛又恨。
對蘇聯/俄羅斯石油暨經濟政策的思考
就世界范圍而言,石油輸出國雖然囤積了大量的財富,但實體經濟卻依然存在嚴重問題,一個正常經濟體的產業結構被部分挖空了:出口的石油換來了外匯,直接用于進口商品和服務,以支撐奢侈的消費。國內的基礎建設走向極端,要么如迪拜一樣在沙漠上建起海市蜃樓,要么如伊拉克,因為炮火的摧殘,實體經濟幾乎無法啟動。由于石油出口能獲得大量外匯,石油出口國傾向于將資源優先分配給采礦業而非工業制造領域,導致后者的發展舉步維艱,同時也使國民經濟的脆弱性增加了。
作為新興經濟體代表“金磚四國”的一員,俄羅斯對世界經濟和政治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雖然在我們三元世界的劃分中,俄羅斯目前是典型的資源輸出國。但其帝國的歷史和蘇聯時期的遺產,以及其驚人的地緣輻射能力與強大的事實力,又使得其國際影響不止如此。俄羅斯既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西方國家,更不是東方國家,作為歐亞大陸北部的新興能源帝國,俄羅斯不僅為周邊經濟體提供了關鍵的能源資源,也主動和被動地施加著自己的影響。然而,由于石油資源的大量開采使得俄羅斯深陷“能源陷阱”,俄羅斯的經濟結構顯得畸形且單一,更為嚴重的是,因蘇聯解體遭到巨大破壞的工業體系面臨由于出售石油等能源而提高的人力成本更加復興乏力。沒有強大的工業,俄羅斯永遠不可能具備與西方進行正面抗衡的實力。
石油這個不知道應該是頌揚還是該詛咒的黑金就這樣使一個曾經的世界超級大國淪落到以出售石油和軍火度日的國家。從蘇聯到俄羅斯的遭遇,可以得出幾點經驗教訓:一是強大的工業生產能力是像中美俄這樣的洲際型大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保障;二是強大的工業能力依賴于完整的工業體系。同時要注意,體系再完整的工業國,如果沒有自力更生搞工業升級的能力,也就喪失了在工業時代的戰略主動權,沒法長久地保證大國的地位。三是再強大的國家,再完美的發展戰略,也必須保證有調整戰略方向的能力與意愿,否則遇到國際局勢變動,光榮的歷史會立刻從資產變成沉重的包袱,甚至會壓垮整個國家。四是能源武器是一口雙刃劍,劍刃越鋒利,殺敵效率越高,傷自己的程度也越深。大國要用好這個武器尤其注意把握好尺度。
作為俄羅斯的近鄰,同時又是從蘇聯繼承一個完整工業體系的唯一國家,蘇聯及俄羅斯的歷史經驗教訓尤其值得中國引起重視。古人云:“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俄羅斯在石油問題上的得與失值得我們深思,畢竟那么多學費已經付出(幸運的是并非我們買單),不能讓它白白浪費。
(作者為浙江大學環境與能源政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