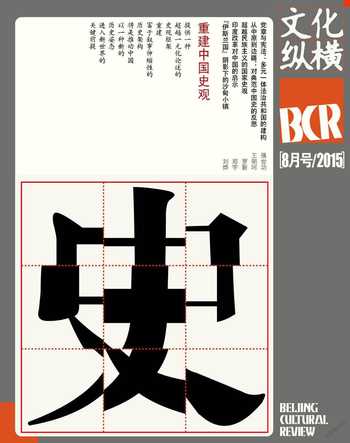緬甸的政治轉型
直接的軍人統治在當代世界已經屈指可數,它們要么讓位于選舉式民主,要么轉化為某種更具現代性的威權統治。東南亞的緬甸,也正在經歷著這一變化。2011年以來,緬甸開啟了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進程,軍人政府的外衣逐漸褪去,一個新的政治體系逐漸成型。
2015年4月,總部位于布魯塞爾的知名智庫國際危機集團(The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就緬甸即將到來的秋季大選發表選情報告,系統分析了當下緬甸政治舞臺上的主要力量及其政黨情況,并預測了可能的變局。
報告認為,現政權與新近取得合法地位的反對派——昂山素季領導的全國民主同盟——是緬甸政治的兩大對壘力量。現政權內部又可劃分為軍隊、政府以及政權黨,它們的團結遠非緊密和諧。在此之外,影響緬甸政治進程的還有若干代表少數族群的地方性勢力。它們并非全國性的政治力量,但其存在可以說是緬甸未完成的國家建設的一個縮影。
長期以來,緬甸除了軍隊外,基本沒有發展出另外一套統治工具,軍隊與國家幾乎融為一體。和許多戰后新興獨立國家一樣,緬甸在建國之初也實行了多黨制,不久后即陷入治理危機,在無休止的混亂之后,軍隊介入政治也就成為了應時之舉。在這一點上,緬甸的軍人政權并不特殊,例外只在于,軍隊集團并沒有像韓國或者印尼的同行們那樣,致力于國家的現代化經濟建設。長期以來,緬甸軍隊似乎更專注于維護自己的政治壟斷地位。
自2011年改革以來,緬甸的軍隊和政府已經在制度上正式分離(在職能和人事上仍存在著一些交叉和重疊)。理論上緬甸已經不是一個軍人執政的國家,以政府、軍方、執政黨、議會等為主體的新權力架構已經成型。新政府兼具軍人影響力和民選性兩個特點:一方面,軍人在長期執政過程中已經形成強大利益的網絡,其退出政治舞臺將是一個漸進過程;另一方面,民選也賦予新領導層以更大的外部合法性,有利于其爭取西方國家的承認,平衡其地緣政治壓力。可以說,2010年之后的改革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軍隊地位,但軍隊仍然是緬甸最有權力的政治角色。軍隊的底線是,無論2015年的選舉結果如何,它都不會放棄憲法框架下的特殊地位,例如在議會中的四分之一軍隊保留席位、對立法的實質否決權、獨立的軍事預算以及不受文官政府監督的獨立性。沒有軍隊的合作,任何一個政黨或政治力量均無法有效地行使權威,這一點也成為各派政治力量的共識。在下一階段的緬甸政治轉型中,軍隊將扮演重要的角色。緬甸國家政治的“去軍隊化”,無疑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現有體制的另外兩個支柱是吳登盛領導的政府,以及政權黨和其控制的議會。兩者隨著改革進程的深入,正逐漸取得更大的影響力,也開始謹慎地與軍隊拉開距離。它們均脫胎于軍隊體制,但在利益訴求、合法性來源以及未來的角色認同方面,卻不同于軍隊。軍隊的職能以及其在現代政治體系中缺乏合法性這一關鍵弱點,決定了它只能成為一個制衡者,采取防御姿態,在接受勢不可免的變革中將損失最小化。而如果這一波民主進程開啟者所倡導的“有秩序的民主”能夠實現,最大的受益者將是新體制的前臺角色,也就是文官政府和多數黨控制的議會。因此,總統本人樂于在眾多場合表現出傾向改革的溫和開明立場,而政權黨控制的議會,在生存之戰還遠未明朗之前,就已經本性顯露,開始尋求立法分支對行政部門的制衡,逐漸表現出不受節制的獨立性。
在2011年的議會補選中,昂山領導的反對黨大獲全勝,得以重返政治舞臺。當前,民盟已成為最大的反對黨。這并沒有改變現有的權力平衡,它仍然只占有少數席位。但補選結果是一個巨大的象征性勝利,也使得人們有理由推測,昂山素季所領導的全國民主同盟極有可能贏得秋季的大選。但這很可能只會對舊體制造成越來越大的麻煩,卻不足以致命,因為在現有的安排下,贏得選舉和組建政府并不是一回事。按照憲法,總統及其內閣的產生,需要由全體議員組成的選舉院推選,而軍隊在提名問題上有著關鍵影響力。此外,昂山本人已經被判決排除在總統候選人之外,即使她所領導的政黨贏得多數席位,也必須要妥協,最終,很可能仍然由一位來自舊體制的人士領導政府。
拋開這些技術性障礙,昂山派最大的弱點是缺乏執政經驗。她的政黨缺乏有效的政策綱領,沒有成熟的組織結構,沒有意識形態,政治目標空泛,類似發展、民主、團結、法治和聯邦主義等概念的堆砌組合并不能真正解決緬甸所面臨的任何一個實際問題。而昂山在緬甸民眾心目中所享有的近乎卡里斯瑪型的領袖崇拜,顯然也無助于其提高治理能力。
昂山的反對派嚴重地依賴中產階級以及知識分子這一小型的社會群體。在緬甸社會,他們是受過西方化現代教育的少數優越者,這無疑最有效地將其與大多數民眾隔絕開,盡管在反軍人執政的共同戰斗中他們站在一起。而從歷史上看,來自中產階級的進步主義改革者大多沒有能力構筑一個整合嚴密的政治結構。埃及的穆爾西政權是最近的一例,烏克蘭“橙色革命”之后一度給人以希望的尤先科政府也是一個典型。可以料定,昂山的反對派不會是這一規律的例外。
基于對主要政治行動集團策略和可能布局的分析,國際危機集團報告認為秋季選舉多半不會產生格局性變化。最關鍵的理由是,各方對于軍隊的實力和意圖均不存在嚴重誤判。
從遠景看,緬甸的轉型之路究竟會如何?澳大利亞莫道克大學(Murdoch University)的Richard Robison 教授在《東亞論壇》發表的一篇論文提供了一種有益的分析。
他比較了若干可能為緬甸所參考的轉型案例。近鄰越南和柬埔寨是一個有吸引力的選項。兩國都是高效的一黨制民主國家,國家有力地控制社會、政治和經濟生活。然而緬甸政權卻缺乏這一模式的前提:一個高度發展的政黨機器。緬甸若從一個基礎狹隘的軍人統治轉向選舉民主,除了賴賬和武力鎮壓(1990年上演過一次),幾乎沒有其他手段去控制選舉進程。
印度尼西亞提供了另一個選項。蘇哈托的威權統治在1998年金融危機的打擊下頃刻陷入瓦解,隨后印尼進入快速的轉型通道。在經歷代價相對較小的陣痛后(亞齊的分離主義),一個開放、分權的新體系得以建立。
緬甸和印尼都曾是軍人統治國家,都面臨著建立一個新政治和經濟體系的任務。最大的區別在于,印尼軍人統治僅僅在1965年政變和大屠殺之后的幾年內,才達到類似緬甸那樣的程度。從1970年代早期開始,蘇哈托領導了一場靜悄悄的變革,完成了從一個基礎狹隘的軍人鎮壓體制向具有更大參與度的威權體制的轉向。蘇哈托不再簡單地鎮壓,而是尋求公眾支持,甚至動員民眾。其最成功的發明就是專業集團黨的構造。這是一個精心組合的體系,包括有控制的選舉、層級式的國家庇護和政商聯盟,以及政權黨支配的議會。
這個高度復雜化的結構遠非軍隊所能控制。蘇哈托給軍隊準備了特殊地位,卻使其在政治體系中邊緣化。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印尼軍隊在1998年的政治巨變中只扮演了旁觀者的角色。
當下,昂山反對派的根本性弱點意味著,軍隊和現政權還可能有第二次機會。此時,有兩個關鍵因素:一是現政權黨能否有效動員大眾支持;二是能否在整合現有利益集團的同時,將一套分贓和裙帶體系擴展至精心選定的若干新社會階層。就第一條而言,所謂大眾支持,通常就是民粹主義的動員和呼吁,而最有效的動員就是民族主義。考慮到這一背景,近年來緬甸國內族群、宗教沖突日益加劇,甚至連佛教徒都加入到宗教殺戮的戰場,人們也就毫不感到奇怪了。
(文/程東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