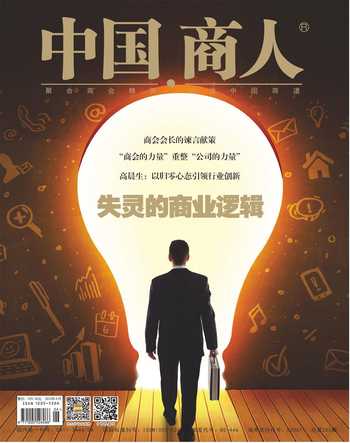新思維刷新商會服務力
汪朝江

經數年探索后,北京福建茶業商會升格為北京茶業企業商會。這不單純是平臺提升和名稱的改變,而是一個商會發展的“新格局”……
經數年探索后,北京福建茶業商會升格為北京茶業企業商會。這不單純是平臺提升和名稱的改變,而是一個商會發展的“新格局”。
“新格局”需要秘書處具備“全面刷新”的能力,不是提升服務能力就可以,也不是更加精進就夠了。如何把握商會發展新形勢與會員核心需求,以創新思維重塑我們的工作方式,這是秘書處面臨的挑戰。
“新格局”三大挑戰
此前我們服務的對象是以閩商為主體,秘書處團隊也是一個區域性行業商會的配置。
商會升格后,服務群體擴大至在京各省區茶商與茶企,這需要我們有一種全國性的眼光來了解我們的會員群體,重組我們的服務,提升我們的服務能力。這是我們面臨的第一個挑戰,從區域性行業商會,到服務全國各地在京茶商與茶企的行業商會,我們的視野和思維需要隨之升級。
第二個挑戰是工作量。以前我們主要熟悉閩商群體的需求、性格和文化就可以了,現在這個任務放大了30多倍,我們需要逐步熟悉34個省級以上行政區企業家群體的行為模式與群體需求。因為茶葉主產區雖然有限,但是茶葉銷區是覆蓋至各個省區,以及世界各地的。我們不熟悉各地商業群體的游戲規則和文化性格,雙方的溝通可能都不在一個頻道上,又如何深入了解他們的需求呢?
第三個挑戰帶有共性。無論行業商會還是各個地域商會,經過五六年快速發展后,都會進入一個平臺期。如何越過這個平臺期,在做好常態化服務的基礎上,為會員提供更高品質的創新服務,這是我們要經過的一個坎。
每個部門都是“小秘書處”
我們秘書處十多人的團隊中,沒有一個來自茶學專業的,這可能有利于我們從消費者角度去理解茶,但是反過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劣勢。
北京福建茶葉商會成立時,我們遇到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商會正是在危機中走過快速發展的6年,當時我們的一切服務都是從零開始的。
2014年,當整個行業陷入低迷狀態時,北京茶葉企業商會成立。我不知道這兩者之間是否有什么聯系,但仍然需要以空杯心態,重新梳理、規劃出一種真正適宜新常態經濟環境下商會發展的模式。
因而,從認識提升、能力提升到團隊最終執行力的提升,需要我們從行業高度去理解和提供會員企業需要的服務,會員企業則從市場趨勢理解消費者需要的服務,這是一脈相承的。
未來,我們秘書處圍繞各部門核心任務和職能,將逐步實現平臺化,向事業部的方向去發展:
比如會員部拓展部,核心是優秀會員企業的發展、聯絡,會員企業的人才引進、培訓服務等等,在此基礎上它可以把行業內的培訓等細分業務做精做深,并對接一些相關的機構資源,向事業部方向發展。這樣的平臺,可以整合一個為會員企業提供專業培訓服務的企業集群;
還有我們的宣傳信息部,它的核心任務是商會品牌形象的宣傳與推廣。未來,它是否可以在《茶商》內刊基礎上,發展為一個整合了傳統及新媒體資源的雜志社,通過自身造血功能,形成商業方面的運作模式。
同樣,在金融服務這一塊,我們也可以引進些專業合作機構。甚至我們秘書處可以組織自己的咨詢機構,廣泛開展對外合作,為會員提供優質的金融服務。
通過這樣的梳理,通過真正的部門負責制,各個部門都應該是一個小秘書處,每一個部門主任都應該是一個秘書長。每個部門都有自己核心的服務,創新的能力,沿著部門——平臺——事業部的發展路線去積極發揮。
這種變革給會員企業帶來的感受應該是,未來每個部門的職能都梳理得更加清晰,會員企業的需求也經過細分,都有對應的機構去服務他。
發揮專業委會的自組織作用
北京茶業企業商會成立后,秘書處在人才引進和配置方面也相應地有一些變化。我們新增加了幾個副秘書長,這些副秘書長將分別對應一個圈層群體。
比如,《茶商》雜志社成立后會有編委會,孫永偉就可以在這個編委會中擔任一個比較特殊的職務。未來我們可能會成立電商委員會、巖茶委員,胡松和趙露在商會是副秘書長,在電商委會和巖茶委員中則可能擔任秘書長。
我們商會秘書處對全國各地優秀會員企業的發展是縱向的整合,各個專業委員會則是圍繞從產區、銷區各個產業鏈關鍵環節的橫向圈層整合。未來秘書處每個部門,各個專業委員會都會引進一個專業的機構。這種合作機構一定是戰略合作者,也可以是條件成熟時由我們商會內部自主組建的專業服務機構。
這樣,商會是搭建一個大平臺,每個部門搭建各自的小平臺,小平臺集結更多合作伙伴后逐步平臺化,形成服務職能清晰的事業部。
未來我們商會的每一個部門,甚至每一個人的核心工作其實非常簡單,他不一定在每個方面都是專業的,但一定能夠引進專業機構為會員企業和廣大茶商及時提供平臺化、專業化的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