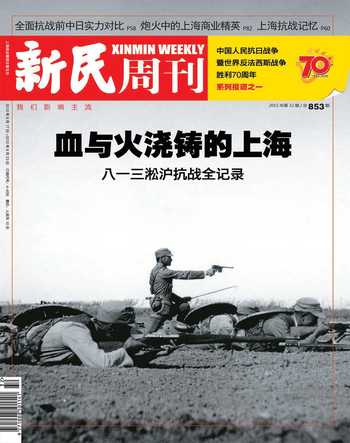悲愴的生命線
劉建春 陳慈林

1937年8月28日下午4點,日軍轟炸上海火車站。
20世紀中前期的鐵路,幾乎是唯一的大運量、長距離、全天候快速運輸工具,是國家的生命線。戰爭時期,鐵路的戰略意義愈加凸顯,往前線可以運送部隊、武器彈藥和后勤物資,往后方可以轉移物資和人員。抗戰期間,鐵路作為戰時交通運輸工具,是戰場,也是“諾亞方舟”。
對中國來說,為了保護戰爭中的生命線,有時候卻需要毀壞生命線。如此無奈的選擇,是何等悲愴的事件。
鐵路,戰時大動脈
1934年,德國軍事顧問塞克特就進言蔣介石:“發展具有戰略性的交通系統,在日本入侵時,可以迅速地輸送部隊至危急地區,實為當前首要任務。”
鐵路自從傳入中國,一直以緩慢的速度發展。自1876年吳淞鐵路建成通車后的近20年時間,一共只修建了400多公里。就是在南京國民政府所謂的“黃金十年”的前期,1935年之前的8年半時間內僅修建鐵路1763公里,平均每年僅修建207公里。
1935年11月,中國國民黨在“五大”之后對日政策逐漸強硬。1936年底,國民政府制定國防交通建設計劃,使交通建設得到了比較高速的發展。從1936年到1937年抗戰爆發的一年半中,共建成鐵路2030公里,平均每年達1353公里。這是1927年至1935年8年間年建筑速度的6.5倍。
抗戰期間,鐵路作為戰時交通運輸工具,發揮了巨大作用。鐵路擔負著向各戰場輸送軍隊及軍需品,搶運機器、設備和技術人員到后方,保證外援物資的輸入等繁重任務。
貫通不久的平漢、粵漢和廣九鐵路成為抗戰初期中國重要的陸上通道。當時中國軍隊80%的補給靠這條鐵路北運。中國從國外購買的全部輕重武器、彈藥、器材由香港進口后,再由這條鐵路運往東南戰場。從“七七”事變到廣州失陷的15個月中,這條鐵路共運送部隊200余萬人、軍用物資70余萬噸。行車最密時,全線列車達140列,成為維持中國抗戰的主要交通線。
浙贛、滬杭甬、京滬、蘇嘉和津浦鐵路的貫通,對東部地區的國防意義十分重大。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開始之后,南京到上海的京滬杭鐵路成為軍用列車專線。淞滬會戰3個月,共開列車1346趟,運兵50個師、輜重5萬噸。該鐵路除了前運軍用物資外,還向大后方搬遷工廠、學校的人員和物資達數百趟列車。
廣州、武漢失守之后,寧波、溫州是唯一與鐵路連接的港口,西南的銻、鎢、桐油、茶葉等農、礦產品由該兩處出口,以換取國外的軍用品。從1938年初到1939年3月的15個月中,浙贛鐵路計開軍列1700趟,運送部隊150萬人。
從“七七”事變到武漢淪陷的15個月中,是鐵路運輸最繁忙的時期,軍事運輸幾乎全部依賴鐵路。武漢失守后,交通運輸重心才不得不由鐵路向公路和水路轉移。
茅以升造橋與炸橋
錢塘江大橋位于杭州六和塔旁邊的錢塘江上。1935年之前,南岸的杭江鐵路和北岸的滬杭甬鐵路是不連通的。為加強華南、華東的聯系,南京國民政府決定把杭江鐵路滬杭甬鐵路跨越錢塘江連接起來,擴展為浙贛鐵路,為此亟需修建錢塘江大橋。國民政府任命茅以升為工程處處長,羅英為總工程師,李學海等橋梁工程專家為工程師,負責大橋的勘測設計。
錢塘江大橋上為公路,下為鐵路,全長1390米,1935年4月正式動工。1937年淞滬會戰打響后,工程建設人員更是夜以繼日工作,終于于當年9月26日建成通車。
通車后,大橋從早到晚被行人和車輛擠得水泄不通。當人們從橋上走過的時候,沒有人知道,他們腳下的14號橋墩中,已經預留了可以埋設500公斤炸藥的方形大洞,足以將大橋炸毀。因為建橋時已經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大戰前夕,茅以升預感到,也許建成后不久,他就不得不親手將橋炸掉。
當時淞滬會戰正酣,大橋立即擔負起鐵路、公路軍運任務。京滬、滬杭甬、蘇嘉鐵路上的機車、車輛和各種器材,快速運轉到浙贛、粵漢、湘桂等線上使用。同時還疏散了數以百萬計的中國居民。
1937年11月的一天,一位神秘的客人造訪了茅以升的錢塘江大橋工程處,他是南京工兵學校的教官,受國民政府指派,向茅以升傳達了炸橋密令。他對茅以升說,杭州即將淪陷,錢塘江大橋決不能資敵,他還告訴茅以升,440公斤炸藥已直接從南京運來了。
1937年12月22日,大橋通車不到3個月,為抗戰需要,錢塘江大橋被炸毀,茅以升親手啟動了爆炸裝置。目睹大橋被炸,茅以升如同親手掐死自己的親生兒子一樣悲痛,他憤然作詩:“斗地風云突變色,炸橋揮淚斷通途,五行缺火真來火,不復原橋不丈夫。”其中,“五行缺火”指的是錢塘江橋的偏旁分別是金、土、水、木,獨缺一個“火”字,“火”字一到橋被炸毀。
他還在1937年12月31日的日記中寫道:“12月23日,敵軍迫近杭州,本橋為我方自動爆炸,第十四號橋墩被毀,五孔鋼梁落水。橋雖被炸,然抗戰必勝,此橋必獲重修,立此誓言,以待將來。”橋被炸的第二天,杭州就淪陷于日軍。
歷史學家在評論這段歷史時說:“日軍實施南京大屠殺后,南侵鎮江、無錫、蕪湖等地,所到之處瘋狂實行‘三光’政策,殺我同胞無數。唯侵占杭州后,發現幾乎已是一座空城,是所有城市中被殺軍民最少的。此錢塘江大橋莫大之功也。”
悲壯的蘇嘉鐵路
“和路軌并行的,是銀灰色的一泓,不怎么闊,鑲著蘆葦的邊兒。青蛙間歇地閣閣地叫。河邊一簇一簇的小樹輕輕搖擺。”這就是78年前,茅盾先生筆下的蘇嘉鐵路。只讀這一段文字,還以為是和平時期一家人乘坐火車出游,事實上,這是1937年10月的一天,茅盾先生帶著兒女告別申城,乘上了逃難的列車。為躲避日機轟炸,列車半夜從上海西站駛出,進入蘇嘉鐵路時已是后半夜,窗外是昏黑而無際的原野,列車馱著逃難的人,在黑夜里轟隆隆地前進。不僅車廂內擠滿黑壓壓的一片,甚至連車頂上也坐滿了人。
蘇嘉鐵路是歷史上存在了7年多的一條鐵路,北起京滬鐵路蘇州站,與運河、蘇嘉公路并行南下,途經相門、吳江、八坼、平望、盛澤、王江涇六站而抵滬杭甬鐵路嘉興站,全長74公里。
這條鐵路是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1936年7月建成的,為何要建造這條鐵路?事情還得從1932年說起,當年1月28日,日軍突襲上海,淞滬抗戰爆發。淞滬抗戰失敗后,國民政府被迫與日寇簽訂《淞滬停戰協定》,其中規定中國軍隊不得在安亭鎮至長江邊的滸浦口以東駐軍,軍隊的調動也不能經過上海,而日軍卻能在上海市郊駐軍。上海是當時中國最重要的城市,是京滬和滬杭甬鐵路這兩條主動脈的交會處。這樣一來,兩條動脈被切斷,南北之間國防和軍事活動無法正常進行。面對日寇的囂張氣焰,首都南京面臨著直接的威脅。為抵御日寇進一步的侵略,使南京與杭州之間的交通暢通無阻,國民政府開始籌劃建設蘇嘉鐵路,并把它作為京滬杭國防工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1935年2月,蘇嘉鐵路正式破土動工。它全長約74公里,寬度42米至200米不等,共征地約6800畝,每畝價格最高才50元,國難當頭之際,蘇州和嘉興人民為支援抗戰,作出了巨大犧牲。沿線農民又承擔了大量的土方工程,由于路基全為填土,基高1米至4.5米,沒有先進的機械設備,所有施工只能靠肩挑人抬。

左:錢塘江大橋鋼梁準備安裝。供圖/陳慈林右:今天的錢塘江大橋。
1936年7月15日7時20分,蘇嘉鐵路第一趟列車正式駛離吳縣站(今蘇州站),駛向嘉興,沿途不時有成群結隊的百姓駐足觀看。出了蘇州火車站,沿運河南下,第一站就是相門站,著名記者馮英子先生那天從蘇州的相門站上車,大概花了三個多小時,趕到嘉興參加了通車典禮。
蘇嘉鐵路通車后,不僅使南北間的軍事活動得以正常進行,防御設施得以貫通,也擴大了經濟交流,為人們出行帶來了方便,鐵路沿線以及長三角地區的交通條件大為改觀。蘇州以西、嘉興以南之間的客、貨運輸不再繞道上海,運輸距離縮短了110.7公里,節省了3小時旅行時間。在淞滬會戰的3個多月中,蘇嘉鐵路作為戰時的交通大動脈,為保衛大上海輸送大量的戰備物資,注入了不計其數的新鮮血液。
1943年,敗局已定的日本,其國內軍用物資原材料極度匱乏,蘇嘉鐵路被日軍拆除運回日本。至今,人們在蘇嘉之間的水鄉田埂旁,還能依稀看到蘇嘉鐵路路基的形狀。
新四軍夜襲滸墅關車站
從上海乘坐滬寧高鐵往南京方向前行,過了蘇州站,下一站就是蘇州新區站。就在蘇州新區站數百米外,有一座現已不辦理客運的老火車站——滸墅關站。滬寧鐵路是1906年修到滸墅關的,車站就建在鎮東側離開京杭大運河大概一公里外的地方。
1937年淞滬會戰之后,蘇州很快淪陷,滸墅關成了日軍調兵和轉運后勤物資的重要節點。扼守水陸交通要道的滸墅關,離蘇州城和無錫城都比較近,周圍的黃埭、望亭、楓橋等地均為日偽軍據點,在十幾公里范圍內拱衛著滸墅關火車站。假如受到攻擊,無論從蘇州或無錫方向來增援部隊都方便。新四軍著名的將領葉飛在1939年夏天成了駐守滸墅關火車站日軍的終結者。一直到今天,夜襲滸墅關火車站在小鎮幾乎還是家喻戶曉。
事情要從1939年夏天說起。那天夜晚,在無錫郊外的田野上,葉飛司令員一聲令下,江抗戰士們出發了。當時正值江南梅雨時節,白天的一陣梅雨后,田埂道路泥濘。渡過蠡水后,東橋鎮已在眼前,去滸墅關,東橋鎮是必經之路。為使日偽無法得悉情報,偵察排率先行動,解除了東橋偽警的武裝,剪斷了電話線,夜襲總指揮部就設在東橋鎮上。
自幼生長在滸墅關的愛國青年鄒根木,早已在東橋和滸墅關交界處的大通橋等候,為部隊帶路。憑著對當地一草一木地形高低的熟悉,他很快帶領部隊摸黑前進到了火車站附近的牌樓村。
江抗支隊三個連的戰斗任務是:一連向火車站南蘇州古城方向監視蘇州方向來敵,三連向北監視無錫方向來敵,二連在吳立夏連長率領下,直搗日軍隊長駐所,指導員吳立批則率隊越過封鎖溝后消滅巡邏哨兵突入營房。
三路隊伍分兵到達車站時,正是半夜子時。主攻的是二連,指導員吳立批帶著二排,悄悄地跟著5個巡邏日本兵進了火車站。連長吳立夏則帶領一排摸到了東車站的日軍營房,迅即把3間屋子包圍起來。
吳立夏向東西房間各投進一枚手榴彈,戰士們跟著投進20余枚,正巧擊中汽油桶和彈藥箱,發出巨大爆炸聲,燃起熊熊烈火。吳立批帶領二排包圍了火車站西邊的日軍營房,他們跟著巡邏兵摸進營房大門。一排在東邊打響后,二排戰士迅即向屋里投擲手榴彈,頓時房屋成為一片火海。戰斗于半個小時后結束,此戰殲滅日軍一個排20余人。
6月25日凌晨,日軍從蘇州城內出動200多人,乘坐裝甲車趕來滸墅關增援。進到東橋時,新四軍早已渡河撤走。日軍在蠡河渡口猶豫了半個多小時,怕中伏擊,不敢貿然渡河,悻悻而歸。
由于滸墅關火車站被焚毀,路軌被破壞,滬寧鐵路被迫停運3天。夜襲滸墅關火車站戰斗勝利的消息不脛而走,上海《大美晚報》、《譯報》、《新聞報》等競相刊載,美國女記者史沫特萊還將這次戰斗寫成戰地通訊刊于《密勒氏評論報》上。
如今,滸墅關老火車站還有一塊“夜襲滸墅關”紀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