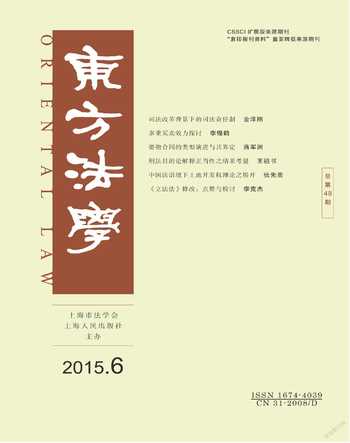訴訟時效適用對象之體系化解讀及立法完善
楊巍
內容摘要:訴訟時效適用對象是指直接受訴訟時效限制的救濟權,而非最終受保護的原權利。因中德兩國分別采“債權——民事責任”兩分法模式與“債務與責任結合”模式,導致兩國在請求權適用范圍、債權請求權與侵權請求權的定位等方面存在顯著差異。在我國現行法體系下,訴訟時效適用對象不應被解讀為原權利屬性的債權請求權,而應為民事責任請求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民法總則專家建議稿”(以下簡稱“建議稿”)第180、181條關于訴訟時效適用對象的規定應以此為基礎作出修改。
關鍵詞:訴訟時效?適用對象?請求權?民事責任請求權
一、問題的提出
受德國及我國臺灣地區影響,我國學界普遍認為訴訟時效適用對象是請求權,但一方面現行法對訴訟時效適用對象的表述并不一致,另一方面由于請求權概念在中德兩國不同立法體系下具有不同意涵,因而對作為訴訟時效適用對象的請求權亦應作出符合現行法體系的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以下簡稱《民法通則》)第135條規定,訴訟時效的適用對象是向人民法院請求保護民事權利的請求權,而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事案件適用訴訟時效制度若干問題的規定》(法釋〔2008〕11號,以下簡稱《訴訟時效規定》)第1條規定,訴訟時效的適用對象是債權請求權。雖然這兩條均規定訴訟時效適用對象是請求權,但兩者性質迥異:其一,前者規定的請求權是為了保護民事權利而行使的請求權,即在某種民事權利受到侵害時而主張的救濟權;后者規定的債權請求權是原權利而非救濟權,其核心內容是債權人依債的本旨向債務人主張的給付請求權而不涉及權利受侵害或權利保護的情形。其二,前者規定的請求權必須借助法院等公力救濟機關才能得以實現,在我國現行法框架下,該請求權主要是民事責任請求權;后者規定的債權請求權發生在平等地位的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而尚不涉及公力救濟。“建議稿”第181條第1款規定:“義務人可以對債權請求權提出訴訟時效抗辯……”。該款系繼承《訴訟時效規定》第1條之規定,而與《民法通則》第135條之規定不同。建議稿規定在我國現行法體系下是否妥當,并與相關規則是否具有兼容性,尚需斟酌。
一個必須澄清的前提問題是:“訴訟時效適用對象”的涵義究竟為何?該問題看似簡單,但實則被學者有意無意地采取不同的解讀而造成學理及實務上的諸多困擾。概言之,“訴訟時效適用對象”有以下兩種可能的理解:
1)原權利A受侵害——→救濟權B,B受訴訟時效限制,訴訟時效適用對象是A。
2)原權利A受侵害——→救濟權B,B受訴訟時效限制,訴訟時效適用對象是B。
按照理解1,原權利A受到侵害時,〔1 〕產生救濟權B, 〔2 〕訴訟時效的適用對象是原權利A。依此理解,訴訟時效適用對象不是訴訟時效直接限制的對象,而是通過訴訟時效最終保護的原權利。“訴訟時效適用對象主要是債權”、“人身法律關系、物權關系均應適用訴訟時效制度” 〔3 〕等觀點即是以理解(1)為基礎。而按照理解(2),訴訟時效適用對象是救濟權B,而非原權利A。依此理解,訴訟時效直接限制的權利才是訴訟時效的適用對象。“訴訟時效的適用對象是救濟權請求權”、〔4 〕“財產權不應適用訴訟時效” 〔5 〕等觀點便是以理解(2)為基礎。
筆者認為,應采理解(2)為宜,即訴訟時效適用對象應為直接受訴訟時效限制的救濟權。理由如下:其一,從歷史產生原因來看,訴訟時效制度發端于羅馬裁判官法的直接原因是權利人在裁判官任期內提起訴訟才能獲得救濟。〔6 〕該制度的初始價值是對權利人獲得公力救濟劃定時間范圍,該制度系針對權利人的救濟權而設。其二,從制度價值來看,訴訟時效具有的多重價值均與權利人尋求公力救濟密切相關。國內外主流意見認為,時效法意在鼓勵原告不要眠于權利之上,而應該在可能的情況下盡快地提起訴訟;〔7 〕時效法便于盡可能保證證據的收集,等等。〔8 〕該制度價值著眼于對權利的救濟而非權利的正常行使。其三,從文義與體系解釋來看,《民法通則》第135條規定訴訟時效針對的對象是為了保護民事權利而“請求”的權利,即請求權。由于行使該請求權的目的是“為了保護民事權利”,因而該請求權具有救濟權性質。例如物權、人格權本身并不適用訴訟時效,但當這些支配權受侵害時,受害人為保護其權利而通過訴訟向加害人主張的侵權責任請求權,即為訴訟時效適用對象。如果把訴訟時效適用對象解釋為該條中被保護的“民事權利”,將得出物權等支配權為訴訟時效適用對象的結論,此與學界通說相悖。其四,司法實務主流意見亦采取該觀點。例如在最高法院公報案例“農業發展銀行青海分行營業部訴青海農牧總公司擔保合同糾紛案” 〔9 〕和“張艷娟訴江蘇萬華工貿發展有限公司、萬華、吳亮亮、毛建偉股東權利糾紛案” 〔10 〕中,在訴訟時效適用對象為訴訟爭點的情形下,主審法院均認為訴訟時效適用對象為救濟權而非原權利。因此,在我國現有學理體系和司法實務語境下,訴訟時效適用對象即指直接受訴訟時效限制的救濟權性質的請求權。
二、在我國現行法體系下,訴訟時效適用對象不是債權請求權
1.中德兩國之請求權存在的差異性
第一,從概念的產生及功能來看,德國法的請求權概念系由羅馬法中訴的概念發展而來,其經歷了從程序權利到實體權利的演變過程。在德國,實體法上的請求權概念是由溫德沙伊德從羅馬法和普通法中的“訴”的概念中發展出來的。〔11 〕溫氏認為,在法庭起訴的權利或訴權,只是請求權的結果,而非原因;請求權在法庭的可訴請性(訴權),是請求權的一個側面,而非構成請求權的東西。請求權概念不包括可訴請性(訴權)的因素。這樣,通過剝離羅馬法上的訴所內含的訴權或可訴請性的因素,溫氏提出了純粹實體法上的請求權概念:請求權是指“法律上有權提出的請求,也即請求的權利,某人向他人要求一些東西的權利”。〔12 〕《德國民法典》的起草者接受了溫氏的觀點,在民法典中將請求權規定為實體權利,其基本功能為連接實體權利和訴權的橋梁。在中國,因請求權為舶來概念,其在立法和學理上初始即被定位為實體權利,而未經歷其在德國的演變過程。在《民法通則》頒布之前,請求權就被認為是一種實體權利,其法律意義是民事法律關系的內容之一。〔13 〕《民法通則》只界定了債權概念,而未規定請求權概念,但學理上均認為請求權為實體權利。〔14 〕而且被認為構成實體權利與訴權之橋梁的并非請求權,而是民事責任制度。〔15 〕
第二,從適用范圍來看,德國法的請求權是總則概念,該概念適用于民法典各部分而不僅限于債法領域。《德國民法典》第194條第1款規定了請求權的概念。“向他人請求作為或不作為的權利(請求權)”,該條位于總則編“消滅時效” 〔16 〕一章。在德國,請求權可以由于債權債務關系、物權關系、親屬關系或繼承關系而產生。〔17 〕根據請求權產生的原因,可以將其分為債法上的、物上的、婚姻家庭法上的以及繼承法上的請求權。〔18 〕債法領域之外的物權請求權、人格權請求權等為非獨立請求權,此類請求權是某些支配權的權能,其作用是當支配權受侵害時使其恢復權利的圓滿狀態。在中國,請求權主要被運用于債法領域。在《物權法》頒布之前,是否對應規定物權請求權存在極大爭議。其后《物權法》雖然規定了物權請求權,但對物權請求權的性質、物權請求權與侵權請求權的關系等問題在學理上仍未得到妥善解決。〔19 〕而對于人格權請求權、知識產權請求權等,也存在較大爭議。筆者無意梳理和總結這些爭議,僅指出對于此類屬于救濟權性質的恢復權利圓滿狀態的請求權,現行法僅規定了物權請求權,其他請求權仍屬于法律上未明確規定、學理上存在爭議的狀態。
第三,對債權和民事責任的不同立法模式,導致債權請求權在中德兩國具有不同的涵義和性質。在德國債法領域,請求權與債權是可以相互替代的概念,兩者適用同樣的規則。德國通說認為,在請求權與債權之間不存在實質上的區別。有關債權的規定,因此可以準用于請求權。〔20 〕在債法范圍內,請求權也被稱為債權。請求權與債權從結構上看是一回事,并且兩者也常常作為同義詞使用。〔21 〕造成此現象的主要原因是,《德國民法典》采取“債務與責任結合”的立法模式,沒有獨立的民事責任制度,對債權提供公力救濟的紐帶由債權所包含的救濟權能來完成。例如《德國民法典》第276條和第277條所稱“責任”實際上是指“債務”,只是為了避免重復使用“負擔債務”才采“責任”概念。〔22 〕因此,德國法的債權請求權包含了給付請求權、訴請公力救濟權的雙重涵義。《民法通則》采取“債權——民事責任”兩分法的立法模式:第五章“民事權利”第二節“債權”第84條第2款規定了債權的概念;而違約責任則被獨立地規定于第六章“民事責任”第二節“違反合同的民事責任”第111條。在《民法通則》體系下,債權請求權為原權利性質,而債權之救濟權能被剝離出來單獨規定為民事責任請求權以實現對債權的救濟。在學理上,我國學界亦嚴格區分債務與責任,民事責任被認為是民事主體違反民事義務所承擔的法律后果。民事責任請求權并非債權的一項內容或權能,而是當債務人不履行或不適當履行債務時由債權人主張的一項獨立權利。〔23 〕因此,在我國民法語境下,債權屬于原權利的范疇,其內容主要包括給付請求權能、處分權能等,而不包括救濟權能;債權請求權與違約責任請求權為相互獨立的權利,兩者為原權利與救濟權的對應關系。
第四,對侵權之債與侵權責任的不同立法定位,導致侵權請求權在中德兩國具有不同的涵義和性質。德國法中,侵權行為是債的發生原因之一,因實施侵權行為而給他人造成損害,行為人對受害人負擔損害賠償義務,在受害人與行為人之間存在的是債務關系。〔24 〕由于采取“債務與責任結合”立法模式,德國法將損害賠償有時認定為義務,有時認定為責任,對義務與責任,特別是對債與責任未作嚴格區分。〔25 〕德國法中的侵權請求權既是一種債的關系,也是一種責任關系,其具有原權利和救濟權的雙重屬性。我國現行法則與之不同,《民法通則》“債權”一節沒有將侵權行為規定為債的發生原因,而是在第六章“民事責任”中專設第三節“侵權的民事責任”。立法機關對《侵權責任法》的定位是“民事權利保護法”、“民事權利救濟法”,〔26 〕該法的名稱亦未采用“侵權行為法”或“侵權之債法”。該立法定位堅持了《民法通則》將侵權請求權界定為獨立的民事責任請求權而非債權請求權的作法,因此在我國現行法語境下,侵權請求權即指侵權責任請求權,其在性質上屬于典型的救濟權,而不具有原權利屬性。
綜上所述,中德兩國請求權的差異性如下表所示:
2.在我國現行法體系下,訴訟時效適用對象不能解讀為債權請求權
由于德國法未采獨立的民事責任制度,違約請求權系債權的救濟權能而非獨立權利,且堅持將侵權行為作為債的發生原因而非獨立的民事責任的發生原因,因此德國法的請求權包含了原權利和救濟權的雙重內涵。這導致在德國法語境下,“訴訟時效適用于債權”與“訴訟時效適用于請求權(債權的救濟權能)”均可成立。而我國現行法嚴格區分債務與責任,將債權的救濟權能從債權本身剝離出來設置獨立的民事責任制度,且未采大陸法系將侵權行為作為債的發生原因的傳統作法,而是將侵權請求權界定為獨立的民事責任請求權。因此在我國現行法語境下,債權僅具原權利屬性,而對其提供救濟的民事責任請求權為獨立權利而非債權之權能,這導致在我國現行法體系下,訴訟時效適用對象不能解讀為債權請求權。
在我國學界,很多學者認為給付請求權或履行請求權是訴訟時效適用對象。〔27 〕有意思的是,他們同時認為違約責任請求權也是訴訟時效適用對象。該觀點是自相矛盾的。其一,從權利的性質來看,根據前文分析,債權在我國現行法體系下僅具原權利性質即主要指給付請求權。訴訟時效的適用對象系直接受訴訟時效限制的救濟權而非其最終保護的原權利,故而債權或給付請求權不應被界定為訴訟時效適用對象。其二,從權利的運行狀態來看,給付請求權履行期尚未界至時,債權人還不能要求債務人履行債務,救濟權處于尚未產生或尚未啟動的狀態。給付請求權履行期界至,但履行期尚未屆滿的這一段時間內,債務人應當現實地履行債務,但由于履行期的最后期限還未屆滿,債權人此時也還不能啟動救濟權。給付請求權履行期屆滿債務人仍未履行債務,表明債權人的給付請求權因債務人的不履行而受到侵害,債權人此時可以啟動救濟權即違約責任請求權以保護其給付請求權,而訴訟時效直接限制的對象即為違約責任請求權。其三,從概念體系的協調性來看,如果認為給付請求權和違約責任請求權均為訴訟時效適用對象,則會推導出物權等支配權和(該支配權受侵害產生的)侵權責任請求權也均為訴訟時效適用對象的結論,這無疑將導致現有概念體系的混亂。
《民法通則》第135條將訴訟時效適用對象界定為“向人民法院請求保護民事權利的請求權”而非“債權請求權”,該規定貫徹了債權與民事責任分離的立法模式,使訴訟時效與民事責任兩種制度能夠有效地銜接。但《訴訟時效規定》第1條則未能體現我國與德國在民事責任制度上的差異性,仍然按照德國法語境將訴訟時效適用對象界定為債權請求權,系明顯的立法失誤。“建議稿”第181條第1款延續了《訴訟時效規定》的錯誤,改變了《民法通則》對訴訟時效適用對象的規定,顯非妥當。
三、在我國現行法體系下,訴訟時效適用對象應解讀為民事責任請求權
第一,在現行法體系下,民事責任請求權是權利人請求保護各類民事權利的基本救濟權。《民法通則》將債權與民事責任分設章節規定,此立法模式使債權作為原權利與民事責任請求權作為救濟權相互分離。其后頒布的《合同法》(第七章“違約責任”)與《侵權責任法》則使這種分離更加明顯和確定。對此立法模式的理論解釋是:民事責任與民事義務(債務)在性質、功能、拘束力等方面均存在差別。〔28 〕侵犯民事權利與違反民事義務相對應,民法對民事權利的保護和對義務人責任的追究構成一個問題的兩個側面,故將民事權利保護與民事責任分開規定。〔29 〕在該立法模式語境下,作為訴訟時效適用對象的“請求權”應解讀為作為各類原權利之基本救濟權的“民事責任請求權”。
第二,將訴訟時效適用對象界定為民事責任請求權,才能與抗辯權發生主義的效力模式相適應。訴訟時效效力與訴訟時效適用對象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前者解決的問題是,訴訟時效期間屆滿后賦予義務人何種權利去對抗權利人的救濟權;后者解決的問題是訴訟時效期間屆滿后訴訟時效抗辯權直接對抗的對象是哪些權利。《訴訟時效規定》第1條規定了抗辯權發生主義,即訴訟時效期間屆滿的直接后果是由義務人取得抗辯權。依據該司法解釋及《民法通則》規定,義務人行使時效抗辯權主要對抗的是權利人在各類場合下要求其承擔違約責任和侵權責任的請求權,因此,這兩種民事責任請求權也成為最主要的訴訟時效適用對象。
第三,我國立法及學說現狀決定了物權請求權、人身權請求權等具有救濟權性質的非獨立請求權不應作為訴訟時效適用對象。在現行法體系下,具有救濟權性質的請求權有兩種:一是民事責任請求權;二是作為原權利權能之一的恢復權利圓滿狀態的請求權,例如物權請求權、人身權請求權等。對于物權請求權是否適用訴訟時效,各國立法不一,我國學界爭議甚大。對于人身權請求權是否適用訴訟時效,域外立法一般持否定態度,〔30 〕我國學界亦普遍認為人身權請求權不應適用訴訟時效。惟應注意的是,此處的人身權請求權是指作為人身權救濟權能、旨在恢復人身權圓滿狀態的請求權,而非指侵害人身權產生的損害賠償請求權。這并非因為后者具有財產給付內容,而是因為后者屬于典型的民事責任請求權而非人身權的權能。
第四,現行法有關規定蘊含了將訴訟時效適用對象界定為民事責任請求權的精神。其一,依《民法通則》第135條規定,訴訟時效期間針對的對象是為了保護民事權利而“請求”的權利,即救濟權性質的請求權,最基本的此類請求權即為民事責任請求權。前文已有詳述。其二,依《民法通則》第136條規定,1年訴訟時效期間適用的場合是人身傷害侵權(第1項)、產品責任(第2項)和兩種違約情形(第3、4項),這四種情形均非債權人正常行使債權,而是發生侵權或違約需要尋求救濟的場合。該條表明1年訴訟時效期間的適用對象是侵權責任請求權和違約責任請求權。其三,依《民法通則》第137條規定,訴訟時效期間起算點是“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時”,該條包含了訴訟時效適用于救濟權的精神。因為在權利未受侵害時,作為原權利的絕對權或債權被正常行使,行使該原權利的時間應受物權存續期間、債務履行期限等期間限制,而不適用訴訟時效;而當絕對權受侵害產生侵權責任請求權、債務不履行產生違約責任請求權時,為限制權利人在一定時間內行使救濟權,該侵權責任請求權和違約責任請求權適用訴訟時效并依據一定標準開始起算。這表明訴訟時效期間直接針對的對象是作為救濟權的民事責任請求權,而非絕對權、債權等原權利。《訴訟時效規定》繼承了這種精神,其第6條規定未約定履行期限的合同債務履行期限與訴訟時效期間是相互銜接關系。前者針對作為原權利的給付請求權,后者針對因債務人違約而產生的違約責任請求權。特殊情形是,債務履行期限未屆滿之前債務人明示預期違約的,由于此時已產生違約責任請求權,則該請求權自應適用訴訟時效并開始起算。
第五,將訴訟時效適用對象界定為民事責任請求權,在理論上和實務上具有實益。理論意義有:其一,使訴訟時效適用對象的界定與訴訟時效制度價值相一致,準確體現訴訟時效作為一種救濟權限制制度的本質。其二,使訴訟時效適用對象的界定與抗辯權發生主義的效力模式相一致,在理論上明確訴訟時效抗辯權所對抗的對象為民事責任請求權。其三,有利于在現行法民事責任制度框架下,厘清債權與民事責任、原權利與救濟權的關系。其四,準確解讀請求權在現行法框架下的涵義,澄清在德國法語境下對請求權概念的誤讀,對我國現行法語境下的請求權概念進行準確地理論定位。實務意義有:其一,明確債務履行期限與訴訟時效期間的銜接關系。在未約定履行期限合同和分期付款合同等特殊情形下,合理界定訴訟時效期間的起算點。例如在“艾娟訴三水區家福五金搪瓷制品廠買賣合同案”中,主審法院認為:“雙方沒有約定質量保證金的返還時間,在原告沒有主張權利或被告未拒絕履行義務的情況下,不能認定原告知道自己權利受到侵害,故原告訴訟請求沒有超過訴訟時效。” 〔31 〕該案雖然發生在《訴訟時效規定》頒布之前,但其處理與該司法解釋第6條規定相符,即履行期限適用于債權(原權利)、訴訟時效期間適用于違約責任請求權(救濟權)。其二,明確無效合同中有關請求權是否適用訴訟時效的問題。例如在“廣西北生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與北海市威豪房地產開發公司、廣西壯族自治區畜產進出口北海公司土地使用權轉讓合同糾紛案”中,主審法院認為:“合同效力的認定,實質是國家公權力對民事行為進行的干預……當事人請求確認合同無效,不應受訴訟時效期間的限制,而合同經確認無效后,當事人關于返還財產及賠償損失的請求,應當適用法律關于訴訟時效的規定。” 〔32 〕該判決隱含的觀點是:當事人請求確認合同無效的“請求權”并非平等主體之間要求承擔民事責任的請求權,因而不能適用訴訟時效;而合同被確認無效后當事人向對方主張的返還財產及賠償損失等請求,屬于當事人之間主張的民事責任請求權,應適用訴訟時效。《訴訟時效規定》第7條第2款亦堅持了該精神。其三,有助于解決保證期間、抵押期間的性質及其與訴訟時效關系等爭議問題。此類期間的適用對象為原權利(保證債權、抵押權),其性質并非訴訟時效期間,但由于這些原權利為主債權的從權利,故此類期間應受主債權訴訟時效的影響并遵循從隨主的規則。例如在“孫蘭芬訴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汝南縣支行抵押權糾紛案”中,主審法院認為:“《物權法》第202條規定的抵押權行使期限實為抵押權的存續期限。抵押權作為擔保物權,不適用訴訟時效制度,但因抵押權人未在主債權訴訟時效期間內行使而消滅。” 〔33 〕其四,對于共有物分割請求權和其他一些與物權有關的請求權,因其不具備民事責任請求權之性質而確定其不適用訴訟時效。例如在“羅芙蓉、羅福玉訴王昌雅等法定繼承糾紛案”中,主審法院認為:“在遺產分割前的共有關系存續期間,任何共有人隨時都可以提出分割共有物的請求,該請求權不適用訴訟時效。” 〔34 〕在“鄭仕興訴林松漢、汕頭市森達塑膠廠有限公司財產所有權糾紛案”中,主審法院認為:“被告辯稱原告關于房屋面積不足的主張超過法律規定時效,缺乏法律依據,不予采納。” 〔35 〕
四、“建議稿”第180、181條存在的問題及修改意見
第一,從立法技術而言,第180條應予刪除。其一,該條的本意是對訴訟時效屆滿的效力作出規定,但因第181條第1款直接繼承《訴訟時效規定》第1條規定,該條已經包含了抗辯權發生主義的內容。故第180條是對第181條第1款內容的同義重復,而無必要獨立存在。其二,第180條系直接仿照《德國民法典》第214條第1款 〔36 〕而設,但其表述又與后者有異。《德國民法典》第214條第1款的表述是“債務人有權拒絕履行給付”,明確將時效屆滿的效力限定于債權債務關系;而“建議稿”第180條則表述為“義務人得就權利人行使權利的主張提出抗辯”,其對權利人的范圍和權利性質未作任何限定,徒生歧義。其三,退一步而言,即使有必要對訴訟時效屆滿的效力設專條規定,也應當將該條與第183條第2款(自愿履行不得要求返還)、第3款(屆滿后義務人同意履行及提供擔保)等內容置于一處規定,而不應置于第181條之前。
第二,第180、181條均將享有訴訟時效抗辯權的主體界定為“義務人”,而《訴訟時效規定》則表述為“當事人”,相較而言后者更為合理。依文義解釋,“義務人”是指債權債務關系中的債務人,而“當事人”則包括債務人及其他當事人。從域外法來看,享有時效抗辯權的主體并非僅限于債務人。例如在法國,債務人以及對于時效完成有利益的其他任何人,均可主張時效抗辯;〔37 〕在日本,判例及學說將可援引時效的主體范圍限定于依時效直接取得權利或者免除義務者。〔38 〕從我國現行法來看,能夠主張訴訟時效抗辯權的主體除債務人外,還包括其繼承人、保證人等。〔39 〕
第三,第181條將訴訟時效適用對象表述為“債權請求權”,改變了《民法通則》規定訴訟時效適用對象為救濟權的立法模式,系未能體認“請求權”和“債權請求權”在我國現行法體系下的準確含義,屬立法失誤,應予糾正。具體理由前文已有詳述,此處不贅。
第四,第181條第1款沒有明文列舉人格權請求權和身份權請求權不適用訴訟時效。對于此類請求權,域外立法通常設專條規定排除其適用訴訟時效,以彰顯人身權與財產權之差異性,我國學界對此亦普遍持肯定意見。〔40 〕現行法規定的某些基于身份關系產生的請求權例如夫妻同居請求權(《婚姻法》第4條)、親屬間的扶養請求權(《婚姻法》第21、第25-30條)、親子認領請求權(《婚姻法解釋(三)》第2條)等,被學理及實務均認為不適用訴訟時效。〔41 〕對于人格權請求權,雖然現行法缺乏明確規定,學理上對其性質及功能也尚存爭議,但主流意見亦認為其不應適用訴訟時效。然而,第181條第1款列舉的不適用訴訟時效的具體情形僅簡單繼承了《訴訟時效規定》第1條的內容,而未明確列舉這兩種請求權,而且兜底條款“其他依法不適用訴訟時效規定的債權請求權”也無法包含這兩種請求權,因為這兩種請求權的性質為支配權恢復圓滿狀態的權能而非債權請求權。
第五,第181條第2款未列舉賠禮道歉和消除影響、恢復名譽兩種侵權責任形式不適用訴訟時效。賠禮道歉和消除影響、恢復名譽這兩種侵權責任形式主要適用于人格權和知識產權受侵害的場合。由于現行法沒有明確規定人格權請求權和知識產權請求權,這兩種侵權責任形式雖然規定于《侵權責任法》,但其實際上擔負著這些絕對權受到侵害后為恢復權利圓滿狀態而產生的絕對權請求權的功能。一般認為,這兩種侵權責任請求權不應適用訴訟時效,因為這些請求權是保護絕對權圓滿狀態的必要手段性權利,如果法院因訴訟時效期間屆滿對其不予保護,則有損人的民事主體資格和生存發展并有違倫理道德、使絕對權成為空洞的權利。〔42 〕第181條第1款既未規定人身權請求權不適用訴訟時效,第2款又未規定賠禮道歉和消除影響、恢復名譽不適用訴訟時效,顯非妥當。附帶指出,第181條第2款規定停止侵害等三種侵權責任請求權不適用訴訟時效,而這三種請求權的性質在現行法體系下是民事責任形式而非債權請求權,第2款規定恰恰證明本文之觀點,即訴訟時效適用對象是民事責任請求權而非債權請求權。
第六,第181條第3款規定返還財產請求權適用訴訟時效是不妥當的,應予刪除。對于返還原物請求權是否適用訴訟時效,各國立法不一,我國存在極大爭議,筆者無意作全面梳理分析,僅就第181條第3款本身的內容加以分析評價。其一,雖然《訴訟時效規定》第7條第2款規定合同被撤銷后的返還財產請求權適用訴訟時效,但依據最高法院的解釋,該條規定的返還財產請求權僅指不能返還原物的情形下“折價補償”的請求權。例如財產是有體物但已不存在(如已被消費)、不能返還(如已被第三人合法取得)或者沒有必要返還(如雙方同意不返還)等,這些情形均為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而返還原物請求權則不適用訴訟時效。第181條第3款未對返還財產請求權作任何限定,將返還原物之物權請求權亦包括在內,擴大了適用訴訟時效的返還財產請求權的范圍,缺乏現有立法支撐。其二,第181條第3款規定返還財產請求權適用訴訟時效的條件是“存在保護不特定第三人信賴利益必要時”,該規定是完全開放式的而非限定具體情形。在承認返還原物請求權適用訴訟時效的我國臺灣地區,司法實務將物權請求權適用訴訟時效的具體范圍嚴格限定于未登記不動產及動產所生物權請求權的場合。〔43 〕而第181條第3款的規定,實際上僅表明了基本立法精神,而并未明確劃定具體適用范圍和適用條件,此規定勢必產生諸多分歧和困擾。其三,德國民法典在將普通時效期間縮短為3年的前提下,規定返還原物請求權適用30年時效期間。〔44 〕其立法理由是該請求權旨在實現各種物權,如果時效過短則難以保障實現各種原權利的目的。〔45 〕而在我國仍然堅持普通時效期間2年或3年的背景下,顯然無法達到德國民法典對返還原物請求權適用訴訟時效的效果。
基于以上分析,“建議稿”第180、181條應當修改為:
第××條:第1款:當事人可以對民事責任請求權提出訴訟時效抗辯,但對于下列民事責任請求權提出訴訟時效抗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支付存款本金以及利息請求權;(二)兌付國債、金融債券以及向不特定對象發行的企業債券本息請求權;(三)基于投資關系產生的繳付出資請求權;(四)其他依法不適用訴訟時效規定的民事責任請求權。第2款: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賠禮道歉和消除影響、恢復名譽的民事責任形式不適用訴訟時效。第3款:親屬法上旨在設立、變更、終止身份關系的請求權,不適用訴訟時效,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