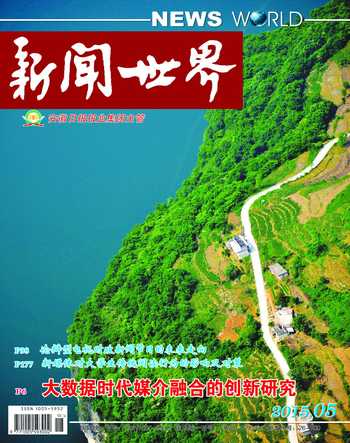案件報道如何提升新聞價值
劉亞群
[摘要]案件報道是新聞報道的“富礦”,但近年來,案件報道呈現出了明顯的程式化傾向。如何突破這種陳舊模式,本文提出了對案件新聞進行“事件化”報道的思路。文中以具體案件為例,從契合案件發生時的背景、挖掘案件發生的真正原因、把握案件的個性化細節等方面著手,給出了具體操作辦法。
[關鍵詞]程式化 事件化 新聞價值
一、當前案件類報道的程式化窘境
案件報道一直受到媒體青睞,眾多媒體都將案件報道作為“重頭戲”。但在新聞實踐中,案件報道日漸陷入程式化的窘境。所謂的程式化,就是在案件報道中,長期使用固有的寫作模式與套路,使得受眾對純粹案件新聞的興趣銳減。
案件報道呈現程式化,有客觀與主觀方面的多種因素——
其一,搶發新聞,不深入采訪。隨著網絡媒體的興起,新聞時效性的爭奪日趨白熱化。記者在獲取相關案件的信息后,便按照固定的套路簡單處理,“第一時間”將新聞發出,而不再進行深入采訪。
其二,滿足于淺層信息,不深度挖掘。隨著政法部門對信息公開的重視,公安、檢察、法院、司法行政等部門常常向媒體主動披露相關案件信息,并給記者提供通稿,部分記者出于懶惰心理,滿足于相關辦案方提供的淺層信息,不愿再對案件深度挖掘。
其三,法律知識的制約,使得采訪淺嘗輒止。每起案件均涉及到相關的法律法規,要想把案件寫成有深度、有含量的新聞報道,須建立在對相關法律法規知識的掌握和理解之上。一些記者受法律知識局限,加之又不愿學習了解與所涉案件相關的法律法規、查詢相關資料,采訪難以深入,便只能局限于固有的模式與套路,很難寫出有新聞價值的案件報道。
二、“事件化”報道提升新聞價值
案件報道亟待突破固有模式,探索一種全新的形態。對案件新聞進行“事件化”報道,不失為提升案件報道新聞價值的有益探索。
所謂事件,一般是指歷史上或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不平常的大事;而案件,則是有關訴訟和違法的事件。顯然,案件只是事件中具有突出矛盾特征的一部分,它距離大多數人相對較遠,只與訴訟參與者及涉案人群的切身利益相關。社會公眾對事件和案件的關注度,有著較大的差別。
數年前,合肥某科研所的退休研究員胡先生以名譽權被侵犯為由,把夸大宣傳其能力和榮譽的科研所醫院告上法庭,媒體廣為關注。諸多報道中,省直一家媒體記者獨具視角的報道抓住了受眾的眼球。胡先生與科研所醫院的訴訟,涉案范圍、訴訟標的和影響力都比較小,若僅僅報道案件庭審過程及判決結果,它最多只是一條讓讀者感到“有趣、意想不到的”社會新聞,不會留下深刻印象,更不具新聞價值。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位已退休的研究員,居然與他所注冊的并“善意褒揚”自己的醫院對簿公堂,其背后的不為人知的故事,不是一張平面的起訴書、答辯狀或判決書可以概括得了的。如果記者只依賴法律文書來采寫新聞、或采用法院提供的判決結果的通稿,即便做到了客觀真實,也不過是一張“平面圖”而已,遠不能滿足讀者觸摸新聞事件內核的心理需求。
胡先生訴科研所醫院侵犯名譽權一案,緣于院方發布的醫療廣告。省直一家新聞媒體記者深入采訪獲知,科研所醫院為吸引更多患者前來就醫,把只在該院掛名注冊而實際并未在此行醫、曾獲得省科技進步一等獎的胡先生作為“招牌”,以各種方式夸大事實對外發布廣告。在廣告宣傳中,胡先生的科研經歷、能力及其所獲得的榮譽均被院方延展、拔高。
現實生活中,夸大其詞、子虛烏有的虛假醫療廣告危害嚴重,廣大人民群眾對發布虛假醫療廣告行為深惡痛絕,也歷來為各級政府要求治理和相關執法部門打擊的重點。為此,記者將原本只有部分人群關注的“尋常”的民事案件,與全民關注的“整治虛假醫療廣告、保障人民身體健康”的大事緊密融合,從庭審的小視角拓展開來,對這一案件進行了立體的、全方位的“事件化”報道,激發了讀者的興奮點、關注度,其顯現的新聞價值不言而喻。
三、如何將案件新聞“事件化”
實際上,將案件新聞進行“事件化”報道,其實質仍然是要將新聞的分量做足、做出更能滿足讀者需求的深度報道來。具體操作中應把握以下幾點:
1、把案件放置到一定的背景里審視
跳出案件看案件,契合案件發生時的背景,表現出具有戲劇性、曲折性的事件本質,案件報道才具新聞價值。
2007年發生在廣州的沸沸揚揚的“許霆案”,人們至今仍時常談及。絕大部分媒體在報道這一案件時,并沒有或者說不僅僅局限于案件本身,而是將案件置于銀行自動柜員機一度屢遭侵財犯罪的背景下,分析許霆從其僅有171元余額的信用卡中連續170多次取走17萬多元的行為,屬于“不當得利”還是“秘密竊取”,為公眾釋疑。2007年12月,廣州市中級法院以盜竊罪判處許霆無期徒刑;許霆提出上訴后,廣州市中級法院不久作出“以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的重審判決;許霆再度上訴,廣東省高級法院對該案公開開庭審理后作出終審判決,駁回許霆的上訴,維持“以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原判。根據“許霆案”一審、重審和終審的判決結果,眾多媒體在報道中充分引用法律條文、過往判例和法律專家的觀點,讓讀者通過有效閱讀作出了自己的判斷。
2、從案件發生發展中挖掘出真正原因
案件的形成存在種種因素,且處于一種潛在的動態變化中,其產生的沖突及帶來的影響,社會最為關注。
武漢市中級法院于2008年3月對一起飛行員辭職糾紛案公開開庭審理,終審判決辭職飛行員向原所在航空公司賠償179萬余元。在報道案件庭審過程中,有記者深入采訪發現,兩年時間里,僅武漢地區就發生3起、超過10名飛行員跳槽到其他航空公司的事件。據介紹,我國每年培養飛行員的總數為600名到800名,遠不能滿足快速發展的航空事業之需。飛行員的稀缺,是造成同行“挖墻腳”的根源。新入市的民營航空公司為保障正常運營,不得不出高薪挖同行的“墻腳”,有的飛行員跳槽產生的賠償費用,也由民營航空公司墊付。由此,飛行員跳槽事件在多地接二連三上演。社會各界在關注案件庭審的同時,對因飛行員稀缺而引發的飛行員頻繁跳槽事件更為關注:這樣“跳來跳去”又面臨高額賠償,會不會影響飛行員的情緒進而影響飛行安全?將這一案件如此予以“事件化”的深度報道,回應受眾關切,其新聞價值必然提升。
3、在案件中發現個性化具有表現力的細節
看似靜態的案件新聞其實起伏不斷,記者有心,便可讓有新聞價值的鮮活“故事”浮出水面。
曾有“安徽第一村”之稱的合肥市包河區隆崗村原書記受賄案開庭審理時,前去采訪的多數記者在開庭一段時間后便離開法庭,返回所在單位等待案件判決結果的通稿。而其中一名記者卻自始至終端坐在法庭內旁聽,認真觀察庭審中出現的變化,并通過庭外與案件當事人交流溝通,把握住了一個具有個性特征的細節,撰寫出《自稱“獻計”獲獎29萬》一稿,受到媒體同行和讀者好評。在采訪報道具有新聞價值的案件過程中,記者應用心參與,與案件新聞自身的變化、發展同步,“制造”出具有表現力的與眾不同的新聞作品。
當然,對案件新聞進行“事件化”報道,不能一概而論。對于那些懸念迭生、偵查技術含量很高的案件來說,讀者還是更希望獲得原汁原味的案例通訊;那些不具典型意義、缺少解剖價值的案件,也難以進行“事件化”報道。筆者認為,將案件新聞“事件化”是對提升其新聞價值的探索,前提是案件本身必須具有一定的新聞價值;否則的話,把一杯白開水全倒出來,它仍然不過是一杯淡而無味的白開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