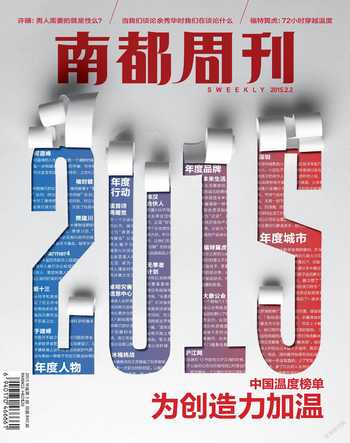樊建川:傻兒、妖精和館奴
安小慶

一名前地產商人,成為中國最大的民間博物館群創(chuàng)建者,搶救國家歷史與國民記憶的收藏家。通過收集數(shù)百萬件地震、抗戰(zhàn)、“文革”藏品,樊建川找到了自己的歸處,也給時代注入了溫度。“館奴”樊建川的經歷顯示了,商人這個群體,正成為中國最有效率的民間公益力量。
三年前,尚在世的成都百歲文化名人車輻在坐輪椅看完建川博物館群后,非常激動,指著樊建川說:“你是妖精!”
四川人口中的“妖精”指人天賦異稟,行事怪異,實有贊美之意。車輻說樊建川是“妖精”,是說從未見過像他這樣奇怪的房地產商人,半生搏命冒險賺的錢,傾筐拿去投入做只賠不賺的博物館。
在此之前,樊建川在收藏界和成都商圈中有一個更廣為人知的外號:樊傻兒。“傻兒就是傻瓜的意思,腦子有病”。
“樊傻兒”的人生有過三次重大選擇:一是不當重慶三醫(yī)大的教師,到宜賓市政策研究所當干事;二是辭去宜賓市副市長下海,到外企打工、自己做房地產;三是做收藏和博物館。這三次他都被視作“不合時宜的傻子”。
2013年,樊建川出了一本新書,他給自己取了一個新名字:“館奴”。作為中國民間最大博物館群的建造者和運營者,他說“我要做一個歷史證據(jù)和細節(jié)的收藏者”。證據(jù)關乎真實,細節(jié)關乎溫度。目前,他的博物館聚落已經有館藏文物800余萬件,國家一級文物達到329件,分館近30個,目前已經開放25個。
時光倒退到50幾年前,幼兒園大班的樊建川收藏了自己人生中第一件藏品,一份幼兒園老師評語,上面寫著“害羞,不愛說話......希望以后好好培養(yǎng)勇敢的精神,遇到困難不哭。”
1957年,樊建川生于四川宜賓。他的青少年時代在“文革”和上山下鄉(xiāng)中度過。他記得自己有明確的收藏意識是在“文革”剛開始的時候。那時候他想弄明白父親為什么被批斗,凡是牽扯到父親的傳單和小報,他都會收起來。也從那時候起,樊建川養(yǎng)成了在垃圾堆里翻東西的習慣。
“文革”末期他考上軍校,從軍校畢業(yè)后到重慶三醫(yī)大任教。因為不甘心在學校平淡終老,他選擇轉業(yè)到宜賓當公務員,不過撿破爛的習慣變本加厲。那是樊建川最愉快的時代,他“豐收”了十萬余張宣傳畫。有一次為了收集老鏡子,他甚至租了一輛皮卡裝上大喇叭,拉了一車的新鏡子到村里邊開邊廣播:“現(xiàn)在四川有個特傻特傻的傻瓜,用新鏡子換你們的老鏡子,還補點錢。”這樣一下子收來了5萬面鏡子,后來成了他文革博物館系列中的“鏡鑒館”的展品。
1993年已經是宜賓副市長的樊建川決定辭職下海,他覺得自己嘴巴太快不適合官場,另外收入太低不適合搞收藏。1993年,他和朋友出資辦起了房地產開發(fā)公司。修房子賣房子賺的錢能夠讓他更加自由和狂熱地到處“收破爛”。
“別人收藏梅蘭竹菊、春花秋月”,樊建川總結自己“收藏的多是些火爆的東西”。比如目前還不適宜展出的大量“文革”遺書。有一份1970年代的遺書,上面有很多黃色的痕跡,樊建川看完了才發(fā)現(xiàn)那是尸水印記。
看這些東西,他會產生一種探索的歡愉。因為“我感到每件文物都在跟我說話”。這些歷史的證據(jù)和細節(jié),令樊建川上癮和沉醉。
1999年9月博物館成立時,關于他只是在安仁打著博物館幌子開發(fā)房地產的說法一直流傳至今。其間,他興建后來被稱為正面戰(zhàn)場館的國民黨抗戰(zhàn)館,又遭遇諸多揣測和說法。
經歷豐富、頭腦過人的樊建川懂得尺度和界線,這是他和他的民間博物館聚落能夠走到今天的基礎。但他并不為此沾沾自喜,反而在盡量制造和安插一些令人“不安”的零件和細節(jié)。
比如知青館前的雕塑—10座在云南葬身于火海的女知青墓碑,被鑲嵌在赤色花崗巖中。不少人跟樊建川說,調子太灰不合適。但樊建川說,“放在門口,是想讓每個進博物館的人都能跟她們打個招呼也好。”
“中國人健忘,對歷史有罕見的稀釋和過濾能力。我能做的就是用更多的展品說話,把歷史留在那兒,讓后人吃驚。”

他自認自己是個合格的商人,但不是優(yōu)秀的商人。為了博物館群,他賣掉了成都的辦公樓,幾乎把十幾年房地產賺的錢都投進去。作為國內的規(guī)模最大的私立博物館群館主,樊建川的員工500多人,每天開館的運營成本已近10萬,在2010年才做到收支平衡。
樊建川一年要買40萬件文物。目前僅“文革”時期的文物就有:手寫資料二三十萬噸、書信三四十萬封,日記兩萬本、宣傳畫十幾萬張......這些都是有待整理和構建的“文革”國民記憶庫。
樊建川自信,當下沒有哪個機構和個人的收藏能超過他。啟功曾讓人捎話給樊建川,“抗戰(zhàn)博物館可以建,‘文革’博物館叫他別建了,是災難不能建,建了要惹禍上身的”。后來樊建川又托人帶話給老人:“‘文革’博物館,現(xiàn)在建不成,三十年后我也要建。”
樊建川今年已經58歲了,想到家族中好幾位父輩都早逝,這幾年他開始有一種極其強烈的“死期將至的緊迫感”。2007年12月6日,樊建川在成都公證了一份遺贈,去世之后,他的建川博物館聚落將歸屬于政府。六年后,他又寫了一個捐贈補充。“主要是怕不在我手上之后,博物館的性質會變。我的話是對一百年后、三百年后、五百年后、一千年后的政府說的。”
2015年9月3日,將是抗戰(zhàn)勝利70周年紀念日,建川博物館將開放新落成日本侵華罪行館。此外,在去年一場火災中燒毀的“三寸金蓮館”也在今年1月15日重新開放。他嫌目前的博物館數(shù)量還不夠,又給自己設立了一個新目標:建到100個博物館,但時間已然緊迫。閑暇時他錄了一張歌碟,里面十幾首都是紅色年代的老歌,每首歌前都有他的宜賓話獨白。
“我想,一個戰(zhàn)士死在戰(zhàn)場上,就是他的歸宿,我樊建川,如果死在建設博物館的道路上,可能是我最高興的事。”
樊建川出專輯是為自己“完蛋”的時候用的,“在我的追思會上,就放這里面的歌。”他覺得參加追思會的人聽這些歌和獨白,“肯定會覺得很親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