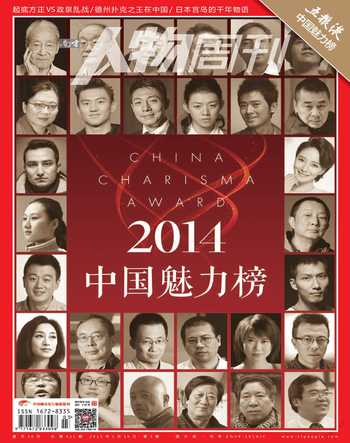大象公會的祛魅方法論
杜強
?

陌陌在納斯達克上市時,黃章晉與羅永浩在時代廣場合影
黃章晉在拉新人入伙大象公會時,喜歡打一個比方,“我們是拿著今天的地圖穿越到過去的哥倫布,未來有著無限多光明的可能,只要能活下來。”
2013年4月,黃章晉辭去《鳳凰周刊》執(zhí)行主編一職,轉身投入新媒體的航海時代,創(chuàng)建“大象公會”。7個月后,大象公會發(fā)出第一篇文章《同性戀鑒別儀的故事》,現(xiàn)在,僅在微信公號平臺就擁有四十多萬粉絲。它給自己的定位是:知識,見識,見聞,最好的飯桌談資。在大象公會誕生之前,恐怕找不到任何一個類似風格的媒體。黃章晉說,“我們就是標準。”
早在2008年,黃章晉便有創(chuàng)辦雜志的想法,“做雜志形態(tài),要厚,內(nèi)容是長文章。”但是創(chuàng)辦一份雜志牽扯到刊號、管理費、發(fā)行、廣告和盈利等諸多現(xiàn)實煩惱,這個創(chuàng)業(yè)想法一直拖了5年。
在此期間,羅永浩找黃章晉談過幾次,想讓他做牛博網(wǎng)主編,黃章晉拒絕了,“那些文章沒有意思,如果我來做一個媒體,百分之九十的作者都要換掉。”黃章晉理想中的團隊是,擁有探索世界的無窮好奇心,對一切抱有祛魅的心態(tài),杜絕空發(fā)議論。
直到2013年10月,一個5人團隊才基本成型。在網(wǎng)站和APP搭建之前,大象公會的第一篇文章就貼上了微信公號,“起碼讓人知道我們開始做了,得讓大家熟悉你的調(diào)性。”
大象公會文章風格鮮明,尤其是文字背后的思維方法,在茫茫文海中很有辨識度。黃章晉擁有13年媒體經(jīng)驗,作為掌舵人,從選題、編輯、成稿到推送時機,他都要參與把關。他在采訪中提到,“大象公會是一個公司化產(chǎn)品,就是標準化的生產(chǎn),即使把作者和媒體名字抹掉,別人一看就知道是哪里產(chǎn)的。”
《為什么習近平選擇慶豐包子鋪?》、《美國人的牙齒為什么最漂亮》、《中國香煙的政治經(jīng)濟學》,內(nèi)容無所不包,往往從“熟知而非真知”的現(xiàn)象開始,抽絲剝繭,引人入勝。如劉瑜所說,“雜亂無章的主題背后,卻似乎隱藏著同一種生活態(tài)度:對日常世界保持永不疲倦的驚奇。”
大象公會的文章標題里最多的關鍵詞是“為什么”。“中國人的數(shù)學為什么好,為什么不好?”“為什么東莞會成為性都?”甚至還有“為什么公章是圓的”。僅問題本身就讓讀者撓頭,但黃章晉覺得,它們都是真問題,“從已經(jīng)熟悉的世界里挖出各種各樣有意思的疑問。”
提問考驗好奇心,回答則需要思維方法。“方法論是慢慢形成的。提出一個現(xiàn)象,概念要先定義清楚,是描述式或是舉例式,總結出一些特征,再進行分析和梳理。”大象公會的文章往往應用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在表象背后挖掘社會性、制度性原因,比如,川菜湖南菜流行是因為近些年來人口流動的趨勢,人口輸入地的粵菜、杭幫菜就沒有大行其道。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慶豐包子鋪就餐后,大象公會推送了題為《為什么習近平選擇慶豐包子鋪?》的文章,從政治學、傳播學領域解釋習近平的選擇,還提到“炒肝”與滿語及飲食風俗的淵源。這是典型的大象公會特色。
2013年10月,大象公社推出了第一本圖書《來到地球第一天》,劉瑜在推薦序中說,“大象公會所做的事情,是社科人文知識的‘科普’。所謂‘科普’,就是用理性破除迷信,用邏輯代替神秘主義,用論據(jù)代替‘我覺得’。”
從2007年開始,黃章晉這套方法論就慢慢成熟。他策劃了一系列國際報道,“就像打仗,傳統(tǒng)的方法是個人的經(jīng)驗、指揮靈感,但我們傾向于系統(tǒng)地分析任務,事先會有長時間的討論,提綱就有一兩萬字,告訴別人的同時也有自我解惑的過程。”
對于文章中的祛魅態(tài)度,也有讀者反感,尤其探究龍圖騰的起源為豬的文章,著實傷害了一些人的感情。黃章晉不太在乎,“反正是沒心沒肺的人。”在他看來,“熟悉的事情被解構,你會感到痛苦,要花費非常多的精力重新定義它。”
其實大象公會對讀者也有自己的設定,“他們不會在成年后自動封閉了對世界的探求欲望和好奇心,他們是從精神上和心靈上不那么中國的中國人。”
為了黏住用戶、迎合讀者的閱讀習慣,大象公會的文章長度在三千字左右。這是內(nèi)部測試的結果,也是黃章晉妥協(xié)的結果。“一千多字只是簡單介紹幾句,但長于三千字的就不愿意讀了。”雖然約稿是主要稿源,但再創(chuàng)作的程度很高。黃章晉對于稿件有著近乎苛刻的要求,他會把采訪細節(jié)全部去掉,很少直接引用,數(shù)小時的采訪經(jīng)過編輯流程有時只剩下一兩句話。“沒有形容詞、沒有副詞、沒有‘我’,信息量超高,所有稿子都是如此。”
一開始,大象公會將自己定義為小眾讀物,而現(xiàn)在它已經(jīng)擁有了40萬讀者。看來,既有的認知被顛覆也會是一種樂趣。
不管是在傳統(tǒng)媒體或是在新媒體叢林里行走,黃章晉一直提醒自己要把握尺度。原先團隊計劃做一個秦城監(jiān)獄的選題,重現(xiàn)內(nèi)部構造,還原審判流程,“包括怎么受審,坐幾個人,每個人坐的位置,一天的生活是怎么樣的。并且聯(lián)系到當事人,手繪監(jiān)獄內(nèi)部圖。但最后還是放棄了。”
大象最終要走向何方,尤其是價值內(nèi)容如何盈利,外界既關注又疑惑。出版的第一本圖書算是探索的一種,黃章晉猜測,《來到地球第一天》也許會顛覆出版業(yè)的舊模式,“出版社不知道讀者在哪里,但是我們有40萬讀者,而且趣味性是一致的。”黃章晉坦言,大象公會將來如何盈利并長久運轉下去,自己也還沒有想好,但眼下,他并不急著讓“大象公會”的品牌變現(xiàn)。“一個媒體要被別人認可是要花時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