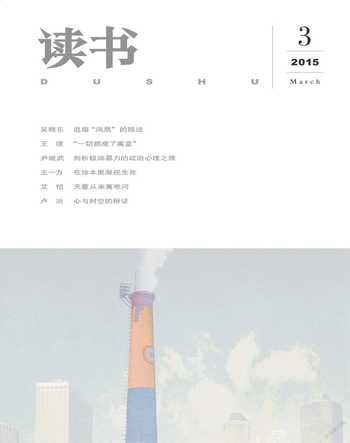心與時空的辯證
盧冶
賀桂梅《西日本時間》一書的獨特性,我以為是不想被任何意識形態(包括自己的)所控制,這是思想者潔癖式的警惕。這種警惕在書中被發揮得爐火純青,幾乎形成了一種新的敘述范例。
在學界,賀桂梅以清晰地處理難纏問題著稱。在中國現當代文化研究的場域中,面對從“五四”到八十年代繁復的歷史命題,她條分縷析的能力令人嘆為觀止。相對在寫散文時,一個問題就出現了:水至清則無魚。她的行文沒有任何迂回遮掩之處,而那些即物即景的觀察又往往引向綿密的學理分析,或令普通讀者退避三舍。
而正因為避免了經驗過快地向知識過渡,在本書的“理論”之內,血流仍然通暢,而作者本人也在假期和田野調查的雙重意識中穿梭自如。她是最稱職的傻瓜游客,會因迷路而有小小的驚慌,也會為一兩個行人的善意就對整個城市起了好感。她對日語和日本文化并無特殊興趣,而從琵琶湖到“王隱堂”,那些精心規劃的旅游景點卻同時滿足了她一般性的驚喜和私人性的鄉愁。在飄飛的櫻花中,像周圍的人群一樣微醺之際,她開始尋找那不經意間操控了人們感情的“幕后之手”。比如說,“日本旅游工業布局對游客的引導和規范”。
知覺的第一個特點是選擇性。人們選擇觀看什么,是被塑造出來的。現代旅游好像一連串的快照,把片斷的印象串接為連續的歷史感。這種認識論式的反省并不僅僅源于作者的職業性警惕。在不舍晝夜的宇治川之側,在街巷叢中靜臥的平等院,在琵琶湖畔的彥根古城,以及日本佛教兩大母山—密宗的高野山和天臺宗的比叡山中,確實存在某些東西,“如此深、如此當真”地滿足和刺激著旅游者關于歷史、文化、生活與精神層面的種種欲求。
旅游文化產業運作出來的日本風味,在十七世紀就已經開始了。長達二百六十余年的江戶時代,天皇大權旁落,遠置京都,將軍在江戶(東京)掌握實權,小小藩國遍布全國,在此“幕藩制”之下,實際上形成了三種類型的朝圣之旅—藩國朝將軍、將軍朝天皇、佛教圣徒朝山—也織就了一張全國旅游的大網,串聯起島國人民的日常起居和精神生活。浮世繪師葛飾北齋和安藤廣重畫筆下,《東海道五十三次》、《江戶百景》這些洋溢著諧趣與清新之氣的風景版畫,在當時就已經成為各個驛站旅館的廣告招牌。直到西方的勁風吹過,這些東方情調更出口外銷,掀起了大洋彼岸一場又一場的藝術革命。
如果說,十七、十八世紀的日本旅游是“全球化”在東方開啟的標志之一,在今天則可能是這一“世界進程”快交卷時的產物。人類越是“現代”,古典與傳統越是層出不窮。誠如賀桂梅所說,懷舊其實是一種后現代的發明。在她喜愛的導演山田洋次的電影里,舊日時光和小人物的職業尊嚴形成了一個回憶的庇護所,哀傷溫暖,甜而不膩,深深地滿足了文化窺視者的懷舊興味,如此,她才切身領會到理論家之言:“文化”是人為構造的裝置和演出,而“人”則總是這種表演的產物。
這種發明和表演,其實并不簡單。全球化的世界,處處是擺好的景觀與趨同的騙局,然而,北京前門大柵欄嶄新的紅墻綠漆總是讓游客輕易看穿商業的戲碼,日本的嵐山古寺卻可以不露聲色地將“歷史之物”端在托盤里,輕輕地掃除模仿與重建的痕跡。靠講述一個故事就維持了生態平衡,這是日本旅游文化的精彩之處。事實上,這個歷史相對短暫的國家總能帶給外來者一種古老悠長的真實質感,而這種質感在號稱千年文明古國的中國,已經非常罕見了。
如果我們把賀桂梅的訪日觀感放到近代以來的世界“學者”譜系中去考察,“日本”的這一特質,可能會更加明顯。從十九世紀末“扎根”日本的希臘教師小泉八云,到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的歷史學家湯恩比、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和后結構主義大師羅蘭·巴特那多少帶著人種論和東方主義色彩的訪日之旅,加之清末以降周作人、戴季陶、陶晶孫和林文月、陳平原們的縱向時間線,即便處境迥然,動機不同,方法各異,東西方學者對這個國家文化特性的考察結論卻是相近的:活的神話,活的童年,活的傳統。
日本是一個“符號帝國”(巴特語),踏入其中的人們,會油然產生借文字、韻律、符號來主控世界的沖動。它是童年和幸福感的儲存庫(熱拉爾·馬瑟語),總是喚起故鄉的記憶,不論是中國人的還是歐洲人的。小泉八云曾在這里重溫愛琴海的灰暗和陽光交織的日子,而屬于賀桂梅的二零一一年,從宿舍的門窗直對著的神戶塔方向,傳來了海水的喧嘩聲,就像普魯斯特的瑪德萊娜小點心,把長江中下游遙遠的少年記憶一波波地傳送過來。
作為最先現代化的亞洲國家,日本最熱衷于儲藏過去。就單位面積而言,它也是世界上博物館最多的國家。“博物館”是殖民地模式的產物:二百年前,大英博物館收集了世界各地的文明圖騰和數不盡的動植物,足不出戶就把世界握在手中。通常,入駐博物館被觀看,意味著你的文明已經死去:參觀者進館開燈,接受一種拆禮盒式的驚喜,其余的時候,展品一片死寂。
日本人有所不同:他們隨時準備把過去拿到現在食用。這種冬眠動物一樣的行為,在周作人于“五四”前夕就介紹到中國的柳田國男的民俗學中已見端倪。而正如美國人瑪里琳·艾維在《消逝的話語:現代性、幻象和日本》里所說,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是日本開始正式打造精神上的“文化博物館”時代。賀桂梅則發現,無論觀者在還是不在,那些日本古董上依附的“寂”的美學,好像隨時都是醒著的。
全球化是無神論的游戲,日本卻隨處有著被宗教賦形的痕跡。誠然,從學理的角度,現代社會在對“自由”、“平等”、“科學”的崇信中,神學的光澤其實從未消隱。然而,走在高野山奧之道那漫長的墓碑之路上,目睹空海御影堂里昏黃的燈籠陣,所謂“生者與死者之間半明半暗的地帶”的體悟,絕非理論的演繹所能替代:那是呼吸之間即時感知的“死亡之魅”,思之令人悚然。
究竟是什么造成了這種“活著的”日本性?《西日本時間》的許多篇章,就在尋找這種感覺的由來。
感性體驗和知識之間的遲滯,是許多學者終生難以跨過的障礙,除了“先入為主”,他們往往會犯一個基本的錯誤,就是錯把屬于空間的東西當成了時間的,或者相反。然而一旦認識到這一“時空的辯證法”,又可從心所欲,任運而行。整理時空正是賀桂梅的長項:所謂“西日本的時間”,其實是不同空間的串聯。
事有表理,情有兩面,各國皆然。然而,日本的二重性與我們不同。在中國,所有的差異都是整體中的部分,而日本,每一個差異都以完整而自足的姿態出現。在賀桂梅的觀感中,以京都、大阪、神戶為首的“關西地區”,與以東京為首的“關東”不同,是“古典日本”的靈魂所在。而關西日本,又是千差萬別。乃至于小小的神戶也有“表里”和“上下”,每一項都顯示著空間的相對獨立。日本僧人行腳穿梭于高野山的八十八所寺廟,將內在的精神蛻變外化為一個又一個不連續的空間場景,這是常見的日本式表達。同樣,充滿了人間煙火氣息的東大寺大佛,與遠處“凈土宗”參道上密層詭秘的石燈籠、背后神道教神社的孤獨和莊嚴,彼此疏離又彼此映射,這一切都表明,歷史的模型并非只有西方式的線性進取和中國式的圓形循環,“俄羅斯套娃”的重重相扣也始終存在,而它的典型形態卻不在俄國,而在日本。
日本的美學、文化和哲學特質,就棲息在“時間的空間化”這個奇妙的視景中。日本人的美學,是不均衡。法國人馬瑟發現,日本的奇數文化對于厭倦對稱的現代人總有奇效,它喜歡列舉而非概括:天皇、古剎、凈土信仰、酒肉和尚、和服、葬禮、童謠民歌、深山里的大鍋飯,以及令人浮想聯翩的“其他種種”,用無序和豐富對抗秩序和分類。這同樣是賀桂梅的發現。名目眾多的“差異”歸置在“日本”大筐下,親臨現場,卻覺得意外的和諧。連農歷節氣都開始淡忘的我們,已經很難想象用哪一個王朝的紀年來排置生活的細節。而現代日本“卻仍舊保留著天皇紀年,將文物的內在邏輯當成當代生活來演示”。同樣,日本人“將飛鳥大佛和入鹿的首塚作為最重要的兩處景點并置一處,似乎并不覺得在佛法的慈悲和殘酷的殺戮之間有太多的矛盾”。在松尾芭蕉的俳句里,脫去野性和回歸自然這樣矛盾的句子奇妙地組合在一起。在本愿寺,巨大的圓木柱撐起堂前走廊,涼風陣送,游人的悠閑與古寺的莊肅形成有意味的對比,與芭蕉的俳句同樣顯示了這一點:日本人對于自然的態度,恰恰是人工性的。
“空間時間化”的基底,在于生死觀:日本的文化空間,總會給死者留下一席之地。正因此,在化野寺外、嵐山古道中,那些圍著鮮艷紅色小布裙的地藏菩薩小石像,才會如此靜謐而凜然。
由此引申開去,這樣的假設或不為過:春天的櫻花游,秋天的紅葉祭,日本人常規的自然之旅不僅來自美的陶醉,也來自凈化恐懼的需要。從用品的消耗、生死的轉換到“日本沉沒”的想象,所有破碎的、失去的、冗余的、未知的,在日本,都有召喚、治愈、預言和編織的場所。于此,賀桂梅發現了一種視角轉換的辯證法。比如熱鬧的商業城市大阪,其精神世界的根底卻是天王寺,只有從這里出發,才能找到大阪人的幽默、精明、熱情的關西腔之下的隱秘與困擾,以及這繁華城市的“人間性”。
如此隨文入觀,我們可以領略到賀桂梅進行空間描繪的能力。在某些時候,她的文字質感有些像王安憶,那種真正復原性的空間感和對物象的記憶能力,在學者和作家中都鮮見。然而這是現象學的分析,它始終關乎著“如是”。但賀桂梅的思維根骨,乃在于社會學的“所以如是”。
并不像她的許多同行,將學術觀點和“私人情懷”在“論文”和“散文”中分而治之,賀桂梅寫論文和散文出于同樣的目的,那就是不遺余力地認識生活和世界。袪魅是她的思想核心,也是啟蒙和理性主義的極致形態。
仁者愛山,智者愛水。賀桂梅是處于穩定狀態的活火山。她分析問題總是就事論事,很少銃上“文采”,但這種分析中的熱情卻是有起源和傳承的:那是啟蒙者的人間世,在八十年代后期,它被轉化成各種不同的形態。作為一個直率而純粹的人文主義者,賀桂梅對神戶的好感,始終來自它保存和聯結那些“符合人性”之物的能力和方式。這是一個安靜而不頹廢的內向型的城市,但居住于中的舒服卻引起了她的理論思考:神戶的悠緩,究竟是一種城市性格,還是經濟遲緩的表征?一般中國游客的“海外旅行”,總是陷入清潔和骯臟的對比性唏噓中,賀桂梅的想法卻是,作為一個很難避免“入侵”的成熟旅游城市,京都究竟是如何整治環境的?
凡此種種顯示了作者社會學式的思維,以及對推理力量的依賴。她的歷史觀同樣頗具啟蒙性:理解過去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不論是在怎樣的地域時空,也不論在何種文體里。
像她推崇的美國人米爾斯所擁有的“社會學的想象力”一樣,賀桂梅能夠辨別感受與知識的邊界,也具有隨時隨地讓它們相互轉化的能力。在伊勢神宮外的商業街,她試圖用宗教人類學來詮釋“眼前活生生的流動的人群”;她關注神戶的富裕華人,因為他們可能會提示另一種觀察“中日經濟交往史”的路徑。然而,這些理論思考的原點正在于物與人相接觸的瞬間:在號稱“京都后廚”的錦市場,被那些琵琶湖的魚和醬菜包圍著,她想到,今天當地人的所食所用,與他們的祖先也許相去不遠—不斷地從物到心,又從心到物,如此回旋往復,由是產生的幻境,或許就是歷史本身。
中國是本書最內在的參照系:在作者的觀感中,奈良比京都更接近中國,而伊勢神宮的地位,亦如同中國的孔廟或黃帝陵—最終的時間與空間感,仍然來自我們所深深認同的那個身份。從 《“新啟蒙”知識檔案》到《思想中國》,何謂現代,何謂中國,這一縱一橫,構成了賀桂梅的學術譜系。而“神國”土地上的“中國人”心情,才是《西日本時間》所通向的地方。
生死問題是一切哲學的根底,作為中國學者,賀桂梅對日本最集中的關注點,卻是政治。從政治的角度來看待日本“時間的空間性”,又是另一番景象。從幽玄美學、武士道到皇軍精神,從歷史戀物癖到愛土愛鄉愛國再到新民族主義,“這中間有許多跳躍的環節”,卻被善于“制造套娃”的日本人出人意料地關聯在一起。
對于中國人來說,戰后的日本不是一個,正如柏林墻割裂下的德國其實有四個。“這個‘一億中產’的日本與那個帝國主義的日本,這個物質豐裕的慢節奏的發達國家與那個充滿攻擊性的非常態國家,甚至包括那些坐在我課堂上的好教養的學生與那些在網絡上大聲叫罵的右翼網民……”這之間的分裂常常使作者需要緊張地尋找一種表述方式,才可以平衡感官經驗和理性意識之間的矛盾。
不難理解,對于啟蒙思想者賀桂梅來說,通往日本的鏈接之一是張承志。這位在九十年代仍然堅持理想主義的孤獨斗士,在《敬重與惜別—致日本》中對“忠臣藏”的描寫,讓賀桂梅體會到“歷史的血肉感”。而正像張承志在想到“中日歷史”之際便“沒有了欣賞日本古典的余裕”一樣,中日關系也會影響到她旅游的心情。她關注大阪市市長橋下徹的改革、對市民的許諾,也注意到他與右翼民族主義的關系。在伊勢神宮,她自覺站在日本人“古典”和“秘密”的核心,而這種感覺卻讓她更加清晰地體察到自己“是中國人”。
這里或許有著真正的分歧之點。在中日戰爭爆發之前,周作人在散文《管窺之四》中宣稱關上了他的“日本研究小店”。除了時局已不允許任何形式的“溝通和理解”之外,更深層的理由是,他發現了中國和日本“真的不同”。對于口味清淡的周氏來說,這是很重的話了。這種“不同”,就寄放在祭神的儀式之中。與中國人熱鬧的迎送場面相對的是,日本人所抬的神輿里,供奉的東西是如此抽象,有時是劍,有時是鏡子,有時則就是“空”。大半個世紀后,賀桂梅在伊勢神宮的現場再次感到:所謂“想象的共同體”,有時會比現實的一切更深地銘刻在我們的身體里。
無論在事物還是語言中,都沒有筆直的路線。即使在思念兒子的假期里寫一點雜感游記,也沒有什么能減輕分析、描寫和抒情中隱含的道德責任。賀桂梅尊重日本,無論是作為研究對象還是作為旅居的場所。然而感情和題材并不能總是并駕齊驅。那些韌勁十足的“學術”段落不僅僅是出于學者的職業倫理,而是因為,“西日本”的時間里,全球化的迷思無分國界,而比此更重要的是,日本是她生命中的過客,但中國不是。
在這個時代尋找傳統與家國似乎總是徒然之旅,交到左手的,右手就拿走了。可這并不意味著沒有能會通的心情。在《飛鳥的佛、石與“大和”之山》中,她寫道:在中國鑒真和尚東渡傳法駐錫的唐招提寺園內,有一個很小的池塘,池水因為不流動,顯得有些臟污和澀滯。但它的名字居然叫“滄海”。“那是佛家內心的海吧。”在另一個地方,她說,“如果人在寂寞中并不落入被他人遺忘的恐懼,而因此領會到自己和世間萬物、無數的人一樣,生活在一個雖不常常有情但也并非不可改變的世界上,看見它的輪廓與邊界,同時也看見自己有限與卑微的力量,關于生活、生存的理解或許才能更為深刻吧”。—“寂”的美學不僅在日本,在賀桂梅心中也同樣存在,只是發生了轉換。國族的分歧、歷史的重量被她納入到“心”的體認之內,構造出的,是別一種“世界”的景觀。
(《西日本時間》,賀桂梅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二零一四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