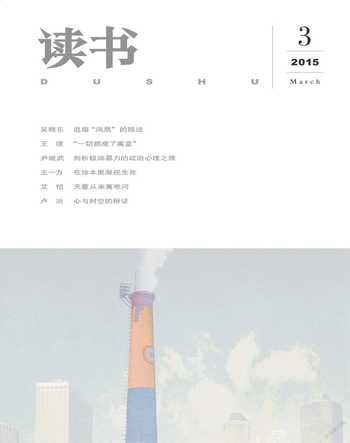文章·文體·文運
魏泉
王風的《世運推移與文章興替》做到了以一種難得的干凈、整飭而又明晰的文風,曲徑通幽,從傳統“小學”的語言文字所涉范疇著眼,由“文字”而“文章”、而“文體”、而“文運”,構建出一個龐大而又細密的文學史景觀,堪稱是近代文學研究的補天之作。
這本書由若干篇論文組成,其寫作時間前后跨了將近二十年,不止是十年磨一劍。其中《為什么要有“近代文學”》一文,代表了作者對中國文學史研究的通盤看法。通過對“文學”、“新文學”和“現代文學”等基本概念的追根溯源、條分縷析,王風令人信服地指出了中國“近代文學”研究所面臨的理論困境與同時所蘊含的廣闊空間:
在經過“資源重組”的古代文學和具有“自足傳統”的現代文學之間,有這么一個所謂近代文學,難以被“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的敘述框架兼容,僅從這一點看,它有成為獨立學術分支的理由。但另一方面,由于“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的敘述策略相距甚遠,“近代文學”處于兩個遠比自身強大得多的學術傳統之間,既無法對二者的關系作出合理解釋,更不可能從這一領域的思考出發,影響并改變相鄰學科的學術路向,這是近代文學研究長期無法取得根本性進展的直接原因。
近代文學作為中國文學史一個至關重要的時期,給研究者提供的廣度是足夠的,舊有文體的整合、新興書面語的崛起,以及文學史的建構,乃至“文學”被作為概念和觀念,無不出現在那時,而同時存在的多種可能性作為埋沒的資源,可以為我們反思現實提供依據。這些特質使得近代文學完全有可能與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區別開來,說得更明確點,有成為獨立學術分支的基礎,而一旦出現獨有的研究思路,上引下聯,將影響我們對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的看法。
王風所謂“獨有的研究思路”,迥異于以往各種宏大敘事的研究格局,也不同于任何形式的流派研究或文本細讀,而是轉而追溯細致、多元、富有深度的“局部空間”,試圖尋找能夠重新思考“中國文學”,并足以質疑整部文學史的出發點。
這樣一個非常獨特又極具挑戰性的思路,大致導源于他對劉師培、章太炎、王國維等人文學觀的形成與轉變的研究。《劉師培文學觀的學術資源與論爭背景》是這部論文集中最早問世的一篇。此文從辨析劉師培與章太炎關于“文言”、“質言”的學術論爭入手,上溯十九世紀在漢宋、駢散之爭背景下阮元的立論,中經劉師培與章太炎從“小學”入手,構建各自龐大而嚴密的不同文學史觀,最后落實在周氏兄弟關于魏晉文章、新文學源流的論述,論述之清晰,眼光之獨到,顯示出深厚的學術功力。
縱觀本書,可以發現作者極為注重書寫語言問題。書寫語言并非語言學領域工作的重心,而同時也為文學研究領域所忽視,但其實極為重要。因而他留意到清末民初的“國語運動”。所謂“國語運動”,據王風所言有廣狹兩種界定:廣義的國語運動可以從晚清拼音化運動算起,一直延續到二十年代國語羅馬字、三十年代大眾語和拉丁化甚至更晚。此以黎錦熙的 《國語運動史綱》 為代表。狹義所指,則從“國語研究會”始,至國語羅馬字運動之前,由當時教育部中人士發動,并組織廣泛的同盟,有一系列明確的目標,到二十年代初獲得全面成功。
“國語研究會”成立之時,正是《新青年》以《文學改良芻議》和《文學革命論》發起“文學革命”的一九一七年。二者之間的關系,在王風筆下,從最初的各行其是,到開始發生聯系,到以標舉“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為標志,二者合流。在雙方的配合下,才有了后來白話對文言的全面替代:
二十年代初,國語運動的成功,為白話文爭得至關重要的初步的合法地位,使它成為正式書寫語言的候選人;然后由新文學不斷豐富鍛造,到共和國時代,終于依靠政權力量徹底取代了文言。(《文學革命與國語運動之關系》)
論文不僅能發人所未發,將這個過程敘述得清晰完整,勝義紛呈,而且還頗覺跌宕起伏。艱辛的考證被融入環環相扣的描述、引征和點評,其強大的邏輯性和強烈的真實感,將一個相當艱深的學術問題論述得引人入勝。
與“國語運動”相關聯,作者還上溯晚清拼音化運動和白話文運動,在紛繁復雜如一團亂麻般的晚清歷史語境中,王風以一種難得的冷靜和細密抽絲剝繭,因難見巧,以“辨名正詞”的“正名”功夫,將晚清拼音化運動、白話文運動的來龍去脈及與國語運動的關系,梳理得清晰而又確鑿。正如他自己說的:“事實只有經過描述才能成為歷史,而描述必須依賴一定的邏輯。”這個邏輯,由獨特的研究思路和詳實的史料征引所決定。雖然你很清楚這也只是建構歷史的一家之言,但是不能否認的是,在一個“局部空間”中,他把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理清楚了。這種建構能力以及不足兩萬字的論文背后海量的資料閱讀(且不論所涉領域的深度),使得讀者除了洗耳恭聽之外,無論是想要對話,還是攻錯,都相當地困難。
王風的論文寫作,極其另類。兩萬字以內的長文,沒有小標題,多數也不設章節,圍繞問題,從頭至尾,一氣貫注,全以文章內在的邏輯推進,冥搜孤往,排難決疑。“文氣”之強,為論文寫作所罕見。這種寫作形式的難度和挑戰性有目共睹,王風不選擇趨易避難,而是迎難而上,背后應是他強大的自信和“做第一流”的自我期許。
循此獨特的研究思路和寫作模式,王風由拼音、國語、文字問題推展到文體研究,其《近代報刊評論與五四文學性論說文》一章,遠溯近代報刊之初,從王韜、鄭觀應,到梁啟超、嚴復、章太炎,到陳冷血、包天笑、章士釗,再到《新青年》時期的周氏兄弟,令人信服地推證了從梁啟超的“自由書”到魯迅的“隨感錄”,論說性報刊文體在近現代之間的轉折與演化:
近代報刊文體興起以來,論說文經歷了相當復雜的過程,先是,傳統的著作之文被移到報章上,亦即王韜、鄭觀應時期;至甲午戰后,梁啟超崛起,他的論說文汲取資源至廣,將著作之文演化為報章之文,余力所及,為“自由書”,這種“短論”將“論說”個人化了,但終于并未產生影響,更沒有成為現代散文的資源—此為“論”之演變。與此同時,由于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日益多元化和分野,“短評”開始作為依附于新聞的評論興起,逐漸發展出獨立的“時評”和“閑評”兩種體式—亦即“評”之系列。到“隨感錄”時期,魯迅扭轉了此類文體中新聞與評論的關系,確立了議論的主體性,由此在報章論說文的廣泛背景下開始催生先被稱為“雜感”,后被稱為“雜文”的現代論說文體。(《近代報刊評論與五四文學性論說文》)
對于文體演變的考察分析,不僅議論新穎,且有非常難得的分寸感和深透的洞察力。這種分寸感和洞察力在《周氏兄弟早期著譯與漢語現代書寫語言》一文的論證中,有更加令人振聾發聵的發揮。
這篇超過三萬字的長篇論文,說是作者積十年之功而成應該不夸張。慢則慢矣,但是慢工出細活兒。此文說得上是在現代文學的“顯學”—“魯迅研究”領域(也還要包括周作人研究)做出了推進。
該文從書寫形式入手,對于“段落”、“標點”與“句讀”在性質和功用上貌同實異的分析頗能啟人心智。但即便如此,標點符號與句讀的使用,究竟是如何與周氏兄弟掛上了鉤,并進而對已經汗牛充棟的魯迅研究有所深化呢?這就是王風的拿手好戲了。從二十世紀之初的林譯、梁(啟超)譯及陳冷血的“冷血體”對周作人早期小說創作嘗試《好花枝》的影響一路道來,通過不厭其煩的文本舉證,得出了以下結論:
有關分段和標點這些書寫形式的問題對現在的閱讀者來說,早已習焉不察。但在晚清的漢語書寫語言變革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無論如何估價都不過分。此類變化在文言和白話系統內部都在發生,總體而言尤以文言為甚,或者可將之稱為近代文言。這當然與口語沒有關系,完全是書寫的問題,所以不妨將其看成“文法”的變化。可以這樣認為,就“詞法”和“句法”的層面,出現了一些新的“文法”。而真正全體的變化在于整個篇章層面—姑且稱為“章法”,出現了新的文章樣式,這是由段落標點這些書寫形式的引入所造成的。周氏兄弟的文本也是這一歷史環境中書寫大革命的產物。
在此基礎上,王風將周氏兄弟以“異域文術新宗,自此始入華土”為訴求的《域外小說集》做了顯微鏡下的細讀,就標點符號的引入對譯和魯迅“直譯”的翻譯理念,如何在這本譯著中做到“移徙具足”,“迻譯亦期弗失文情”,列舉了大量例證,說來話長,但最后的結論很明確:
魯迅的譯作,實際上是將西文的“章法”引入—亦即“對譯”到漢語文本之中。句法的變化,甚至所謂 “歐化”的全面實現端賴于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域外小說集》確實可以被認為是漢語書寫語言革命的標志性產物,盡管那是文言。
在周氏兄弟的早期小說翻譯和文言小說的創作實踐中,對于“引號”的使用及前后變化引起王風的特別關注,他有驚人的發現:
漢語古典文本,無論文言還是白話,實際上是無法從形式上區分直接引語和間接引語,因為沒有引號這個形式因素來固定口說部分,從文法上也無法分別。無論是“曰”是“道”,其所引導,只能從語言史的角度判斷其口語成分,一般的閱讀更多是從經驗或者同一文本內部的區別加以區分。唐宋以來文白分野之后,文言已經完全不反映口語,文言文本中直書口語是有的,但那只是偶爾的狀況。如今對文言句子直接加引號,從形式上看是直接引語,但所引卻是現實中甚至歷史上從未可能由口頭表達的語言。由《懷舊》的文本揣測,魯迅在這篇小說開筆時似乎并未預料到后面會寫法大變,只是進入有關“長毛”的情節時發現不得不如此。結果新的表達需求必須新的書寫形式的支持,而新的書寫形式的實現又帶來了語體上的巨大矛盾,所顯示的恰是文言在新形式中無法生存的結果,簡直預告了文言的必須死滅。
在這已經夠讓人目瞪口呆的結論面前,王風猶不自足,進一步考究“逗號和句號”的重要性:
句號和逗號是最常用的兩種標點符號,但其實最晚被引入漢語書寫中,就因為漢語文本原就有施以句讀的歷史。句讀和句號逗號都有斷句的功能,雖然斷句方式并不相同,但表面上看似乎差別不大,不過句號逗號的配合使用有時可以反映某種文法關系,為句讀所不備……
句號和逗號的引入,終于全面實現了書寫形式的移入,使《域外小說集》所說的“移徙具足”,或者說令國人頗不習慣的“歐化”的漢語書寫得以全面實現:
在周氏兄弟手里,對漢語書寫語言的改造在文言時期就已經進行,因而進入白話時期,這種改造被照搬過來,或者可以說,改造過了的文言被“轉寫”成白話。與其他同時代人不同,比如胡適,很大程度上延續晚清白話報的實踐,那來自于“俗話”;比如劉半農,此前的小說創作其資源也可上溯古典白話。而周氏兄弟,則是來自于自身的文言實踐,也就是說,他們并不從口語,也不從古典小說獲取白話資源。他們的白話與文言一樣,并無言語和傳統的憑依,挑戰的是書寫的可能性,因而完全是“陌生”的。
作為新文學創作的開端,魯迅的《狂人日記》奇特的書寫語言相信給每個讀者都留下了鮮明的印象,而何以如此,王風此文是我所見到的最別出心裁而又有說服力的解答。
盡管如此,關于周氏兄弟的研究在我看來,還不算是此書最精彩的部分。從劉師培、章太炎,到林紓、嚴復,到胡適、錢玄同、周氏兄弟,凡所論及,都說得上精彩可觀。但我覺得王風做得最好的,還是王國維。
王風曾在《追憶王國維》一書的“后記”(收入本書的《新時代的舊人物》一章),圍繞王國維之死是“殉清”還是“殉文化”展開論述,言必有征,條理秩然,視野開闊而又析事精微。尤其難得的是,在冷靜雅潔的文字背后,有種不可掩抑的如詩意般的情感,十五年前讀來蕩氣回腸;此番重讀,仍多感喟,覺其分寸之精準、體貼之入微及行文之雋雅,依然是難以企及的學者之文。而完成此文的十年之后,王風卻能再進一步,拿出王國維研究的新作《王國維學術變遷的知識譜系、文體和語體問題》,對王國維學術變遷的細密考察,仍以“辨名正詞”的“小學”功夫入手,追溯王國維學術入手處與東洋之教育的關系,從醉心于叔本華、康德哲學,關注教育,接受西洋之分科邏輯,到移情于文學,標舉“古雅”,倡言“境界說”,以至對宋元戲曲的大規模研究,及后期的轉向國學研究,王風都有從語詞、文體和語體方面的精彩紛呈的論證和發覆,并能進一步斷言:
所以通觀其一生治學,哲學則以西學重理中國思想,文學則在西學的觀念下以中國本有的范疇進行研究,史學則全由中國自身學術傳統而發揚光大之。
王國維數度學術轉向也正說明他與中國傳統學者的追求有所不同,傳統上中國學者于所謂無學不窺外,自我期許的是諸學會通,循環相證。遠之不論,即以同時之大學者章太炎而言,《國故論衡》論語言文字之學、論文學、論諸子學,意在結構完整的自我學術構架。反觀王國維,數度轉向,而每每掉頭不顧,可見早期由教育入手所形成的“學科”或“科學”的觀念還是終身留下了烙印。
站在這樣一個讓人望而生畏的高度去評價王國維、章太炎的學術變遷與知識譜系,顯然僅有勇氣是不夠的,學養、才華、性情、文采、功力,甚至時間,都是缺一不可。王風的王國維研究,以一種難得的分寸感摹寫出了王國維學術人生真實而又高明的境界。他自己于其中浸淫體味多年,一定也是受益匪淺的吧。
(《世運推移與文章興替》,王風著,北京大學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