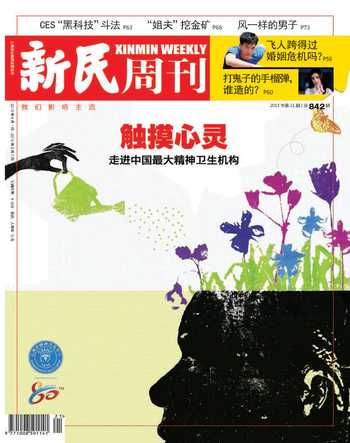你必須做一個心理體檢
黃祺
上海市心理咨詢與治療中心有30個門診室,從患者需求出發,中心開設了睡眠障礙、焦慮、抑郁障礙、強迫癥、老年心理、兒童心理等專病特色門診。
馬斯諾,美國著名的心理學家,他提出的馬斯諾需求理論,把人的需求分成五個層次,以金字塔的形狀排列。五個需求中處于最底層的兩個是生理需要和安全的需要,在這兩個需求之上,是情感和歸屬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需要,后三者,都屬于精神和心理的范疇。
也就是說,人作為地球上最高智能的生物,除了滿足生理的需求以外,我們還有更多的要求,所謂的“幸福”,不僅僅是衣食無憂,更有心理的愉悅和健康。
邁入21世紀的中國,經濟發展讓大多數人越過溫飽之憂,站到了需求金字塔的上端,公眾對心理健康越來越重視。同時,隨著社會轉型與城市化,中國人也開始體會到前所未有的心理壓力。
心理的晴雨,該如何應對?現在,很多上海市民知道,有了心理問題,可以到零陵路604號上海市心理咨詢與治療中心。為了滿足公眾對心理咨詢的需要,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加強了心理相關學科的建設,圍繞心理咨詢和治療開設了多種渠道的服務模式。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的心理咨詢與治療中心,已經成為行業領跑者和心理咨詢與心理治療的人才培養基地。
與軀體的不適相比,心理的亞健康更難被發現,需要專業人員的判斷和糾正。當體檢成為人們生活的必需,心理的體檢,也理應受到更多的關注。
心靈感冒無需回避
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在人生的某些階段出現心理行為問題,它被形容為心靈的感冒,只要及時糾正,并不影響生活,但如果沒有得到及時的發現和糾正,則很可能變成更加嚴重的心理或者精神疾病。
為了了解上海市居民的心身健康狀況,上海市曾在開展大規模的流行病學調查,2010年發布《上海市民心身健康調查》結果。
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何燕玲醫生介紹說,這次調查得到4個重要的結果。首先,上海市每5個市民中就有1個終身有過至少1種心理行為問題;每8個市民中有1個正存在某種心理行為問題。其中男性的酒精依賴和酒精濫用問題特別突出,而女性的焦慮和抑郁問題患病率高于男性。
第二,心理和軀體密切相關,增加彼此的患病風險。有某種心理行為問題的人有慢性軀體疾病的比例要高于沒有心理行為問題的人;反之,有過慢性軀體疾病者,患各種精神疾病的風險是沒有任何慢性軀體疾病者的2倍多。
第三,患有精神疾病增加患者及其家庭的負擔。第四,有心理行為問題者很少求助于專業心理援助。市民中只有將近五分之一的人曾通過互聯網、熱線、自助團體、親朋好友和自行購藥等非專業途徑了解或求助有關情緒問題、飲酒、服藥、吸毒等問題。

調查顯示,上海市心理行為問題和精神疾病的現患率處于國際中等水平,精神疾病的終身患病率雖然目前仍低于多數發達國家,但上升趨勢明顯。
缺少心理健康常識以及對心理行為問題的避諱,是阻礙有心理行為問題的人及時求助的最主要原因。何燕玲醫生介紹,另一次關于上海市民精神衛生知識知曉度的調查顯示,盡管近年來心理健康知識得到一定的普及,市民對疾病案例的識別和認識有提高,但也有不足,對精神疾病的歧視和偏見依然嚴重。
心理咨詢火熱背后
心理行為問題與社會壓力有關,上世紀80年代,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的一批老專家和院領導,已經意識到為市民提供心理健康服務的重要性,這個時期,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開設了心理門診,是國內最早的一批心理門診之一。
不過,由于公眾對心理健康的認識不足,到心理門診就診的人不多,門診開在精神衛生中心原門診樓的一角,每周只設兩個半天的開診時間。現任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臨床心理科主任的張海音醫生還記得,對于當時的患者來說,走進心理科診室,是一件非常艱難的事。張海音曾接診一位患者,患者告訴他:我已經在門口猶豫2個月了,今天才總算走進來。
盡管就診患者不多,但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非常重視心理科的發展,1980年代,受當時上海市衛生局委托,醫院承辦了心理醫生的專業培訓班,為心理科工作儲備專業人才。1990年,上海第一條心理健康咨詢熱線開通,由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的專業人員接聽電話。
到了上世紀90年代,社會上形成心理熱,學校里開始設置心理輔導老師,各種心理咨詢工作室出現在市場上。同時,衛生系統要求三甲綜合性醫院必須設置心理門診,中國心理學科進入快速發展的階段。
為了滿足公眾對心理健康服務的需求,1998年,上海市心理咨詢與治療中心投入使用,心理咨詢與治療中心設置在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旁的一座獨立的建筑中,是中國第一家獨立設置的心理咨詢與治療中心。
中心投入運營之初,門診量不多,平均每天接診大約60人,但此后增長迅速,每年門診量增長30%,近幾年的增長率也在10-15%,目前每天接診700多人。走進上海市心理咨詢與治療中心,給人留下的印象是不太像醫院,中心環境寬敞明亮,診室私密性比普通醫院更強,候診者安靜地在走廊里等待。
門診量的增加,反映了人們對心理疾病認識的改變。張海音醫生告訴記者,他曾看到有老總讓助理陪著來就診,這說明大家已經不認為看心理門診是羞恥,而是一種正常的需要。現在,上海市心理咨詢與治療中心有30個門診室,從患者需求出發,中心開設了睡眠障礙、焦慮、抑郁障礙、強迫癥、老年心理、兒童心理等專病特色門診。另外,中心可以提供國際主流的各種心理治療方式。
心理咨詢對專業人員的要求非常高,作為國家衛計委三大心理治療師培訓基地之一,上海市心理咨詢與治療中心對心理醫生的專業能力要求很高,他們都是具有精神科醫生資質和從醫經驗的醫生,經過心理學科培訓后才可以為患者開展心理咨詢和治療。張海音醫生告訴記者,心理科門診與其他軀體疾病的門診不同,診斷和治療的耗時長,一次心理治療一般需要50分鐘,醫生非常辛苦。
心理咨詢行業的“火熱”,也帶來了咨詢機構的良莠不齊。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黨委書記謝斌介紹,新修訂的《上海市精神衛生條例》對心理咨詢機構的資質和登記、監管提出了明確的要求,在此之前,社會上的各種所謂心理咨詢機構,都是以其他咨詢業務的名義登記。在這些機構中,咨詢師的資質難以保證,業務質量也難以監管和控制。謝斌提醒說,今后市民一定要到正規的心理咨詢機構求詢,以獲得專業的心理咨詢和治療。

去年國內上映了一部名為《催眠大師》的影片,電影中,心理咨詢行業被描述為一種時尚、高端、神秘的職業。這樣的印象,也正是吸引很多人成為心理咨詢師的重要原因。目前,國內市場化的心理咨詢行業數量很多,但良莠不齊,心理咨詢機構的注冊、咨詢師的考試、頒證等環節比較混亂,一直飽受詬病。有業內人士介紹,日本在將近30年的歷史里一共才考出1.2萬多名心理咨詢師,而我國從2002年開始,僅上海8年中就已經頒出了5萬多張“心理咨詢師證書”。
張海音告訴記者,心理咨詢行業對人員的專業素質要求很高,如果患者到不具備資質的咨詢師處咨詢,很可能適得其反,問題沒解決,反而產生不必要的焦慮。市場上一些不正規的咨詢機構,也會給咨詢者做量表測驗,但測驗結果的解讀需要非常專業的能力,解讀不準確,會大大影響心理治療的效果。
身邊的心情“大白”
心理的變化復雜而微妙,我們都希望,如果出現心理問題,身邊能有一位心理健康家庭醫生隨時提供評價和指導。不久前在中國熱映的電影《超能陸戰隊》中,電影主人公大白就是這樣一個家庭醫生的形象,大白隨時能夠覺察到人的情緒變化,及時地提出建議和指導,幫助解決心理問題。
醫生們也在尋找方法實現這樣的愿望。2014年8月,一款名為“心情溫度計”的APP正式上線,這款APP的研發團隊是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的精神科醫生。
移動醫療是近幾年醫療領域的熱門話題,隨著互聯網技術的成熟和移動智能終端的普及,很多過去只能在醫療機構內完成的服務,可以通過移動終端達成,“心情溫度計”也是這樣一個新興的移動醫療服務工具。
開發團隊的吳志國醫生介紹說,“心情溫度計”提供了5套專業量表(PHQ-9、GAD-7、HCL-32、MDQ和6項生活質量問卷),專注于常見的病理性抑郁和焦慮情緒的自測,用戶自我測評后,軟件會依據不同的選項統計自我評測的分值,并將各項目的分值以及該量表的總分值匯總到后臺服務器,由服務器記錄歷史數據并提供相應的數據反饋。最后,被解讀的數據以溫度計的形式反饋給用戶,讓用戶獲知當前精神狀況的評估結果。
吳志國醫生強調說,“心情溫度計”不是診斷,而是一個自測工具,目的是促進就醫。我國成人總的精神疾病月患病率為17.5%,其中各類抑郁障礙和焦慮障礙患病率分別超過4%和5%,但超過96%的患病群體從未尋求專業的精神衛生醫療服務。加之廣大居民對精神衛生知識的低知曉率和低接受度,因此眾多精神心理問題/疾病被“隱藏”在了社區中而無法被專業服務覆蓋。
從全球范圍來看,諸多因素限制了精神衛生服務的可獲得性。除了精神衛生資源短缺及分配不均衡等重要因素外,時間、地域、交通條件、病恥感、病患個體偏好等因素也極大阻礙了服務需求者們去尋求“面對面”的精神衛生服務,這些問題在包括中國在內的中低收入國家尤為突出。
“為此,臨床工作者和研究者們正在探索利用現代化信息和通訊技術手段來改善精神衛生服務的可及性,由此發展出電子化精神衛生(e-mental health)的概念和創新服務模式。”吳志國醫生說,“心情溫度計”的開發,正是基于以上的社會背景。
除了自測,“心情溫度計”還提供心理健康的相關知識,對公眾進行健康教育。
當然,“心情溫度計”未來還可以有更加豐富的功能。吳志國醫生介紹,由于抑郁和焦慮障礙等精神疾病的整個診療過程,包括初始識別、評估、診斷、干預等一系列流程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其間產生的大量有益于個體診療和醫學發展的信息,經由傳統醫學“面對面”的疾病數據采集和病情記錄的方式已不能充分和有效滿足如此大量的醫學隨訪需求。而“心情溫度計”可以記錄用戶自測的數據動態變化,制作成曲線圖,這些資料直接提供給用戶自己的主治醫生,這樣,醫生就可以得到豐富的參考數據,對診斷和治療都有很大的幫助。
我們都期待身邊有一個心情“大白”,隨時為我們做一次心理體檢,移動技術與醫學的結合,已經為我們實現了這樣一個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