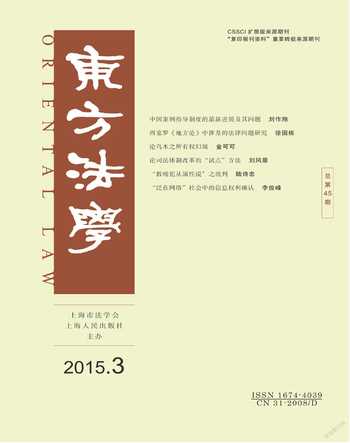追索在荷“肉身坐佛”之私法路徑
葛江虬
內容摘要:欲由私法路徑追索在荷“肉身坐佛”,首先應當明確肉身坐佛屬人類遺骸文物,追索行為系主張文物所有權的返還。根據本案背景,荷蘭法院對本案具有管轄權,準據法為荷蘭法。本案中并無適用國際公約或文物特別立法的余地,具體規則應適用《荷蘭民法典》中的規定。根據《荷蘭民法典》第3編第86條、第115條等相關條文,我國福建陽春村村民作為所有權人,應通過證明現占有人對出賣人不享有所有權存在合理懷疑,以阻卻善意取得的構成;并于佛像被盜次日起20年期間屆滿前,通過啟動司法程序以中斷導致訴權喪失的消滅時效。在該過程中,提供全面且有效的證據是追索的關鍵所在。
關鍵詞:被盜文物 準據法 善意取得 取得時效 荷蘭法
引〓〓言
近日,一尊在匈牙利自然科學博物館展出的中國佛像引起了世人的關注。在該佛像的現占有人將這尊佛像送到專家處整修時,人們在這尊佛像的內部發現了一具僧人遺骸。〔1 〕在中國,這種佛像被稱為“肉身菩薩”,亦有“肉身佛”、“即身佛”、“入定佛”等稱謂。〔2 〕然而,這尊“肉身坐佛”如此令人矚目,并不僅僅是因為其制成過程。更重要的是,這尊佛像被認為系我國福建省三明市大田縣吳山鄉陽春村所供奉的“章公六全祖師”佛像——后者于1995年12月15日被盜,至今下落不明。在我國媒體記者發現此事并進行追蹤報道后,〔3 〕“如何幫助陽春村村民追回供奉時長已綿延千年的祖先遺骸”這一命題,成為了各方關注的焦點。在不少媒體的新聞稿中,一些記者提出了關于追索肉身坐佛的見解,也有一些文物法與國際法專家接受了采訪,從法律角度提出了不少建議。〔4 〕
遺憾的是,新聞報道畢竟篇幅有限,對于追索肉身坐佛所涉及的法律問題而言,很難進行深入、全面、準確的探討。如果真的要啟動追索程序,那么現有文章對相關問題的梳理與分析,仍可謂遠遠不夠——甚至在個別文章中,還存在著一些具有誤導性質的內容。若因此貽誤時機,后果嚴重,茲事體大,從私法角度進行系統梳理殊有必要。除近日新聞所能提供的事實要素外,我國學界對于有關如何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相關問題,已經有了不少研究成果,〔5 〕其中不少介紹與觀點為本文的寫作提供了堅實的理論根基。
雖然究竟采取何種方式追索肉身坐佛仍未有定論,但“合乎法理”的主張及其指導下的具體行動方略,無疑將提高追索的成功幾率。無論其他追索方式是否可行,跨國訴訟總是當事人的選擇之一。考慮到本案當事人的主體身份皆屬于私法關系主體,〔6 〕出于私法角度的考察將具有重大價值。
基于上述考量,以下筆者將通過試圖回答下述問題,來具體說明追索肉身坐佛的私法路徑:(1)肉身坐佛的法律性質是什么?和追索行為有何關聯?(2)如果要通過民事訴訟追索肉身坐佛,那么何地法院擁有管轄權?何地法律得以適用?換言之,我們應在何種語境下展開對本案的分析?(3)在該語境下,哪些立法應予適用?(4)在這些立法中,有哪些實體規則值得注意?(5)具體的追索工作應如何展開?
一、“肉身坐佛”的性質與爭議類型
本案涉及的第一個問題,是對系爭標的物——肉身坐佛——應當如何認識。之所以需要對此進行討論,是因為各國對于不同類型的私法爭議,往往都規定有不同的國際私法規則,而該規則又是確定管轄權與準據法的依據,屬于探討“追索之私法路徑”所不可回避的前置命題。因此,后續一切基于私法層面的討論,都將圍繞本案的爭議類型展開。
在目前的大部分文獻中,“肉身坐佛”基本都被賦予了兩種性質:“文物”與“人類遺骸”。〔7 〕那么這兩種特性究竟具有哪些涵義?兩者之間是否存在某種包含關系?其定性與后續的追索行為又有何種聯系?
就“文物”(或“文化財產”)的概念而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曾在其《1970年關于采取措施禁止并防止文化財產非法進出口和所有權非法轉讓公約》(以下簡稱“1970年公約”) 〔8 〕第1條作出說明,“文化財產”系指“每個國家、根據宗教的或世俗的理由,明確指定為具有重要考古、史前史、歷史、文學、藝術或科學價值的財產”。與此同時,1970年公約第1條還提供了一份類型化的清單。而于1995年所通過的《國際私法協會關于被盜或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約》(以下簡稱“1995年公約”),〔9 〕則于其第2條定義了“文物”的概念——“系指因宗教或者世俗的原因,具有考古、史前史、歷史、文學、藝術或者科學方面的重要性,并屬于本公約附件所列分類之一的物品”。該公約的附錄同樣提供了一份清單,用以說明文物的類型。由于這兩大公約是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非法販運文化財產”項目下所提及的重要法律文書,其價值不容小覷。遺憾的是,兩大公約對于“文物”或“文化財產”的定義基本大同小異,而除了“具有人種學意義的文物”被規定在類型化清單中以外,與人類遺骸直接相關聯的內容,則沒有被公約所涉及。
在公約表述的基礎上,國外的文物法專家亦嘗試過對“文物”進行進一步的精確定義。根據文物法專家克斯廷·奧登達爾教授(Kerstin Odendahl)的觀點,文物系指為人力所創造、改造或組合,或者能夠表征人類文明發展的,并由歷史、藝術、科學、建筑、考古或其他任何不同的維度,所能夠賦予其文化價值的有形動產或不動產。文物可以是一件單獨的物品,可以是物品的組合,也可以由系列藏品所組成。〔10 〕根據其他學者的解讀,該定義認為,文物應符合兩個標準:人類中心屬性以及文化價值。其中,“人類中心屬性”主要是指文物須為人力所制成,即使其形成非人力之功,也必須能夠表征人類文明的發展,后者尤以考古學上的發現為典型;而“文化價值”則指向社會所賦予物品本身的特殊涵義。〔11 〕由此,就人類遺骸而言,若該遺骸具有表征人類文明發展的意義,且被社會所賦予了特殊涵義,那么該遺骸就能夠被認定為文物——典型例子如本身屬于人類骸骨的嘎巴拉碗(Kapala)、埃及木乃伊與毛利刺青頭顱(Toi Moko),這三者都被認為屬于文物。
由于直接關切人類遺骸的追索與返還的法律規則非常罕見,確定遺骸的文物性質,至少可以保證遺骸能夠受到基于文物法,包括作為一般規范的財產法的保護。不過,人類遺骸作為文物,亦有不同于其他文物的特征。這一點可以在諸多國際層面的正式文書中發現。
《凡爾賽條約》第246條第2款被認為是人類史上第一個明確提及人類遺骸歸還、且具有國際約束力的法律條文——即于該條約生效的六個月之內,德國必須把姆克瓦瓦蘇丹(Sultan Mkwawa)的頭骨移交給英國政府。在此之后,1989年由世界考古學大會所通過的《朱紅同意書》(the Vermillion Accord on Human Remains)被認為是歷史上第一個在國際層面處理人類遺骸問題的正式文件。根據該同意書第1條,無論其血統、種族、宗教、國籍、習慣與傳統,對于人類遺骸的尊重應普遍適用。該文件第3條明確提到,在可能、合理及合法的前提下,應尊重逝者所在當地社會以及逝者親屬、監護人的意愿。第5條則談及,對于已經成為化石、骨架或是木乃伊的人類遺骸的安置,應通過磋商達成,在此過程中應尊重逝者所在當地社會關于如何安置祖先遺骨的合法考量,以及基于科學與教育的合法考量。〔12 〕雖然在實踐中,大部分遺骸作為展品在陳列前往往并未取得當地社會與逝者親屬的同意,這一點《朱紅同意書》未作涉及。〔13 〕但是至少該同意書確認了一條重要的原則,即遺骸所屬逝者的親屬、所在社會的合法考量都應當得到足夠尊重——即便是以科學性及專業性為主要出發點的世界考古學大會,也同樣是這樣認為的。這樣的立場在后續的國際文書中也得到了重申,甚至強化。比如,1993年“第一屆土著人民文化與知識財產權國際大會”所通過的《關于土著人民文化和知識財產權的馬塔圖阿宣言》第2.12條明確指出:“所有由博物館及其他機構所持有的土著人遺骸與隨葬品,必須依合乎當地文化的方式歸還于它們的原籍”。〔14 〕而國際博物館協會(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以下簡稱“ICOM”)在2004年修訂的《ICOM博物館倫理準則》,其第4.4條同樣提到:“對于所屬社會要求將其成員的人類遺骸,或其他具有神圣意義的物品撤下公開展覽的請求,應當被迅速、保持尊重且敏感地處理。對于歸還此類物品的請求,也應秉持這樣的原則進行處理。博物館規章中應包含如何處理此類請求的具體流程”。〔15 〕此外,2007年《聯合國土著人民權利宣言》第12條第1款最后一句明確提及,土著人民有權要求把遺骨歸還原籍,且該條文第2款更是進一步說明,各國應通過與有關的土著人民共同制定的公平、透明和有效的機制,設法讓土著人民能夠使用或取得國家持有的禮儀用具和遺骨,并(或)將其送回原籍。〔16 〕
雖然這些正式文件缺乏法律上的約束力,也沒能提供任何一種可供執行的、具有法律之力保障的實體權利,不過,其于法律與政治活動中的影響力卻不能忽視。通過對這些文件的整理,不難發現,聯合國公約尚且不提,那些專業性組織——甚至是往往在利益上與歸還遺骸存在沖突的考古學家及博物館團體——也都認可歸還遺骸的重大倫理意義。在這些涉及人類骸骨的國際文書中,往往關于人類骸骨的條文和其他文物的條文是分立的,且其歸還沒有任何妥協余地。〔17 〕相較于其他文物,我們明顯可以看出,對于人類骸骨的歸還被賦予了更重要的地位,因此主張歸還遺骸的合理性也更堅實。〔18 〕
基于上述介紹與分析,本次追索所涉及的“肉身坐佛”系人為產物,且具有高度的宗教與科學價值,被認為屬于文物應該不存在疑問。〔19 〕唯須注意的是,該“肉身坐佛”同時具有“人類骸骨”的性質,就其歸還意義而言甚至高于其他文物種類。就追索而言,“文物”的定性決定了我們從私法路徑出發,應考量與財產法、物權法有關的法律架構,主張文物所有權的返還,是追索行動的中心。而“人類遺骸”的定性,則確定了追索行為背后堅實的合法性根據。〔20 〕
二、管轄權與準據法
由私法路徑探討追索肉身佛像的問題,確定該路徑應起始于財產法或物權法只是第一步。接下來需要回答的問題是關于管轄權與準據法——假設我們要通過啟動司法程序的方式追索肉身坐佛,那么哪國法院有權受理案件?第二個問題是,依據該法院所在地的沖突規范,哪國法得以適用?
就管轄權而言,實踐中并不存在太多爭議。國際文物訴訟由提起訴訟時文物所在地的法院管轄,已經成為了各國普遍遵循的規則。〔21 〕在當前語境下,荷蘭法院對本案具有管轄權——即追索肉身坐佛須向荷蘭法院提出主張,這一點并無問題。
相較之下,關于準據法的確定,國際上則有不同做法——這也是現有中文文獻所討論得較多的問題之一。首先,各國處理涉外物權糾紛時,普遍適用的沖突規范被認為是采納了“物之所在地原則”。不過,到底什么是“所在地”,中文文獻中卻存在不同理解——是系爭文物的流向地?〔22 〕還是所有權據稱轉移時的法律事實發生地?〔23 〕在不少案件中,基于這兩種思路選擇的準據法可能會有不同。比如,在我國學者曾介紹過的“文克沃斯訴佳士得、曼森及伍茲公司案”中,竊賊從原告位于英格蘭的居所竊取文物,運送到意大利賣給了一位善意購買人,隨后該善意購買人又將文物送回英格蘭進行拍賣。此處,如果準據法確定采用“流向地”規則,則文物地處英格蘭,應適用英格蘭法;若采用“移轉地”規則,則引起所有權移轉的交易發生于意大利,應適用意大利法。事實上,在確定準據法的過程中,英格蘭法院采納的是后者立場,作為“物之所在地原則”的應用結論。〔24 〕除明確說明采“物之所在地原則”的國家外,即便是另外一些采納“最密切聯系原則”以確定準據法的國家,動產交易的發生地也是衡量“最密切聯系”的首要因素,結論與采用“物之所在地原則”往往沒有區別。
不過,“物之所在地原則”在近年來也受到了一些批評。該原則被認為會鼓勵竊賊將偷盜而來的文化物品,在確保善意取得人獲得有效所有權的民法法系國家進行交易,再通過適用該國法律以漂白買受人的所有權。考慮到具有重要意義的文物爭議所帶來的國際影響,近年有的國家司法實踐以及學者開始主張采納“被盜地法”(或“來源國法”)、“文物原所有人住所地法”。〔25 〕不過,出于“被盜地法或原所有人住所地法忽略了善意購買人的利益”、“文物流失多年的情況下與上述地點聯系已不再緊密”、“文物資源國法往往沒有文物市場國法完備”等原因,〔26 〕國際文物訴訟中適用“物之所在地法”,仍然是主流。
回到本案——由于本次事件具有管轄權的是荷蘭法院,而管轄權的確定又是適用準據法的前提,那么究竟采納“物之所在地原則”、“最密切聯系原則”還是“來源國法”,則應當考察荷蘭有關國際私法的確定準據法問題的相關規定。〔27 〕
荷蘭國際私法對于確定準據法的沖突規范被規定在《荷蘭民法典》 〔28 〕第10編。其中,第10:127條第1款確立了適用于財產法的一般規定——采“物之所在地法”。第4款則規定了需要被納入考量的若干因素,如該物屬動產還是不動產,該物是否可轉讓、是否有權利能夠被創設——需要滿足哪些要件,等等。第10:131條就從無權處分人處取得財產的準據法作出了特別規定:即該物處于哪國領土時,該權利可以依法被獲得,那么該國法便得以適用。
在荷蘭法學界,該規則被認為是對荷蘭最高法院在1988年所作出的一則經典判例(以下簡稱“被盜名畫案”)的成文法化。在該案中,一幅名為“Klooster in een Landschap”的畫作于1945年在德國失竊。時光荏苒,1990年一名買家持該畫作前往阿姆斯特丹的一家拍賣行進行估值。該畫作的原所有人發現后,主張對該畫作享有所有權,且該買家不享有所有權。買家則主張,他已經通過適用荷蘭法上關于時效的規定,而獲得了畫作的所有權。荷蘭最高法院認為,在文物追索案件中,往往因年代久遠或文物本身幾易其手,要在文物不斷流轉的過程中找到每一次可能引起所有權移轉的法律事實發生的地點以及其對應的準據法,幾乎不可能。因此,無論畫作在長達45年的時光中如何流轉,如果最后占有人可能通過荷蘭法上的規定獲得所有權,那么荷蘭法就為該案件的準據法。〔29 〕
申言之,由于荷蘭關于消滅時效的實體規則并不考慮文物在離開原所有權人之后的每一次具體流轉,而是直接從“非原所有權人的其他人以文物占有人姿態行動時”開始計算,故此時在文物流轉過程中的每一次引起所有權變動的法律事實,對于判斷最后一名占有人能否獲得所有權來說,均已喪失意義,因此它們所對應的每一個“物之所在地”,也變得毫無價值,只有最后可能導致現占有人獲得所有權的“所在地法”——荷蘭法——煢煢孑立。故而確定準據法的結論也只剩下了一個。
這種在沖突規范可能導致不確定結論的情況下,直接用國內法實體規則幫助確定準據法的思路,非常值得我們關注。不過這種獨樹一幟的操作背后,其本質還是在于文物所有權糾紛往往產生于原所有人與現占有人,決定這兩方利益主體誰能夠得到法律之力保護的關鍵,還是在于導致現占有人可能取得所有權的最后一件法律事實——無論是一般情況下的交易行為,還是本案中因為規范內容而得以適用的消滅時效,兩者在本質上并無差別。雖然乍看之下確有本末倒置——“實體規則先于沖突規范被納入考量”——的嫌疑,但是背后的法律精神卻是一致的。因此,該案所確立的規則被納入了《荷蘭民法典》中。
就肉身坐佛的追索來說,荷蘭藏家若以交易為核心法律事實主張取得所有權,則交易地為荷蘭,應據“物之所在地原則”適用荷蘭法;他也可以主張曾在上述“被盜名畫案”中大顯身手的時效規則,此時適用的仍然是荷蘭法。因此,筆者下文中對于具體規則的考察,將圍繞荷蘭法展開。
三、荷蘭法框架下的立法適用
確定了準據法為荷蘭法后,筆者需要關注的問題是:荷蘭法框架下,應當關注哪些立法?具體而言,有否適用國際公約的可能?歐盟層面有無相關指令已被荷蘭國內法轉化?就荷蘭國內法而言,除了《荷蘭民法典》以外,有否有相關文物的單行立法可以適用?
就第一個問題來說,根據《荷蘭王國憲法》第五章第二節的規定,國際公約在荷蘭一經公布,便可直接適用,且其效力相對荷蘭國內法具有優先性。〔30 〕這樣的規定為適用國際公約提供了一種可能性。具體到追索文物的領域,我國學者對于國際條約法與國際習慣法的發展,已經作出過不少介紹。〔31 〕如前所述,1970年公約與1995年公約與本文最是相關。其中1970年公約所確立的規則,主要適用于國家以公法主體參與文物返還的情形,而1995年公約確立的規則,則主要適用于以私法行為為特征的返還行為中,返還關系既可能發生于國家與國家之間,也可能發生于國家與私人之間、私人與私人之間。〔32 〕就具體內容來說,1995年公約則比1970年公約提供了更為詳細的規則,尤其是對于被盜文物的善意取得作出了規定。〔33 〕考慮到我國大部分涉及追索被盜文物的論文,已經對兩個公約的內容進行了不少深入介紹,〔34 〕筆者在此不作進一步展開。
遺憾的是,上述兩大公約均受“不拘束第三國”原則及“不溯及既往”原則的影響,在實踐中作用非常有限。〔35 〕對于“不拘束第三國”來說,由于在利益衡量上更傾向保護文物資源國,因此西方不少文物市場國拒絕簽署公約。〔36 〕就“不溯及既往”而言,僅我國就有不少文物,由于流失年代久遠,在國際公約沒有溯及力的現實情況下,基本很難通過公約途徑進行追索。〔37 〕
對于本案所涉及的肉身坐佛來說,剛好上述兩個問題都有表現——荷蘭與中國一樣,是1970年公約的締約國,但荷蘭加入公約的時間是2009年7月。〔38 〕基于“不溯及既往”原則,公約條文及其轉化后的法律規定,對約二十年前進入荷蘭的肉身坐佛并不具有約束力。〔39 〕就1995年公約來說,雖然荷蘭政府早在1996年6月就簽署了公約,但荷蘭議會至今沒有批準該公約,〔40 〕該公約在荷蘭尚未生效,自然也不具有法律上的約束力。〔41 〕
針對第二個問題,在歐盟層面確實有一部指令,以促進歐盟成員國財產法的協調化為目的,同樣涉及了文物歸還這一具體命題——即《關于歸還從成員國非法運離文物的指令》(以下簡稱“《歸還文物指令》”)。〔42 〕雖然該指令在內容上包括了不少令人感興趣的條文,〔43 〕然而,在該指令的語境中,文物受保護的前提必須是在其自歐盟成員國領土被非法移出之前或之后,根據成員國內國法或行政程序,被列為“具有藝術、歷史或考古價值的國家寶藏”。〔44 〕這是因為,該指令的立法權限來源于《歐盟運行條約》第36條。根據該條文,即使條約第34、35條確立了“歐盟成員國對于彼此之間的進出口不能作出數量限制”的立場,但這在保護具有藝術、歷史或考古價值的國家寶藏時并不適用。如此一來,本案的肉身坐佛既非由歐盟成員國出口,迄今為止恐怕也沒有歐盟成員國將其列入“國寶級文物”范疇,故《歸還文物指令》與其轉化后的荷蘭國內法條文也無法適用。
就荷蘭國內法來說,專門保護文物的單行立法主要是1984年生效的《文化遺產保護法》。但是,這部旨在防止具有重大歷史及科學意義的荷蘭文化遺產從荷蘭流失的法律,〔45 〕顯然不能為我國陽春村村民追索肉身佛提供直接幫助。
在排除了公約、指令及單行立法的可適用性之后,唯一剩下的,只有《荷蘭民法典》上的一般規定了。以下,筆者將結合《荷蘭民法典》上的條文,對荷蘭藏家業已獲得所有權的主張的兩大根據——善意取得制度與時效法——進行逐個介紹與評述。
四、具體規范之一:善意取得制度
通過私法路徑追索文物,即意味著依《荷蘭民法典》第5編“物權”第2條對于所有權人的保護,向現持有佛像的荷蘭藏家主張返還佛像,并獲得法院的支持。〔46 〕而可能面臨的抗辯,則是荷蘭藏家依據荷蘭法上的制度,主張其已經獲得了肉身坐佛的所有權。因此,否定荷蘭藏家“已經合法取得所有權”的法律狀態,成為了私法路徑的重中之重。在這樣的語境下,我們需要關注的問題是,荷蘭民法上有哪些規范可能為藏家所援引,主張其已經擁有了對肉身坐佛的所有權?欲對抗這些主張,這些規范應如何為我們所用?
如前所述,無論是學界研究也好,公約立法也罷,追索被盜文物的核心法律問題,往往是圍繞著“現占有人能否依善意取得規則獲得所有權”這一命題展開。在本案語境下,這同樣是藏家可能倚仗的重要實體規則。
《荷蘭民法典》第3編“財產、財產權與財產性利益法”第86條第1款是為荷蘭民法對于善意取得制度的一般規定。根據該條文,“在一項依據本法第90、91或93條,以動產、非登記財產或票據權利為標的的轉讓中,盡管出讓人欠缺處分權,但如果該轉讓存在對價,且受讓人為善意,則該轉讓為有效”。該條所涉及的第3編第90、91、93條主要是關于交付問題,例如第3:90條第1款規定的內容,即為“交易未登記且置于出讓人控制下的動產所需之交付,為轉移其占有于受讓人”。而何為“善意”,《荷蘭民法典》第3:11條給出的定義是:“任何法律效果中所要求的‘善意’,不僅指當事人實際上并不知曉與其善意有關的事實或權利,也包括在這些情形中他所應當知曉的內容。如果存在合理懷疑,那么即使該當事人無法進行調查,他也將被評價為‘應當知曉’”。
第3:86條第3款則說明了盜贓物是否適用善意取得的問題:一項動產的所有權人,若其喪失占有是由于該動產遭竊盜,則有權在被竊之日起的三年內重新主張其所有權。不過對于第3款的規定,亦存在一些限制,即于兩種情況中,善意受讓人取得所有權并不受“三年等待期”的限制。其中,第二種主要是關于金錢及票據交易,與本案有關的是第一種情形,即:該動產的受讓人屬自然人,且非該領域中的專業人士、亦非以此為業;而交易中出讓人的工作則是在營業場所 〔47 〕與公眾就類似物品進行交易——除拍賣人以外——并能夠證明出讓人的交易行為屬其正常業務范疇。與此同時,該條文規定的“三年等待期”,可類推適用本法第316、318、319條關于時效中斷的規定。
除了直接規定善意取得制度實體內容的第3:86條以外,《荷蘭民法典》還有兩則條文專門規定善意取得制度的適用范圍。其中第3:86a條不僅確定了第3:86條規定的善意取得制度不能被援引對抗歐盟成員國、或其他依《歸還文物指令》追索文物的國家。當然,這以該文物屬于指令所界定的文物范疇,且該文物被證明屬非法出口的前提上。第3:86a條第2款則明確,第3:86條不能被援引對抗,主張其占有脫離的動產為《文化遺產保護法》所指定保護的所有人,也不能對抗主張其動產為《文化遺產保護法》第14a條所禁止運離荷蘭之物的所有人。關于補償的規定則被規定在第3:86a條第3款,即就第3:86a條第1款(基于《歸還文物指令》)所規定的情形而言,法院應當考慮具體情勢,在占有人已盡審慎義務的情況下,準許給予占有人的合理補償;就第2款(基于文化遺產保護法)的情形來說,除非是適用本法第86條第3款的情形,回復所有權主張可能在無補償的情況下成立,否則上述立場仍然適用。第3:86a條第4款則是對補償范圍及時間的進一步說明,即補償應當包括原所有人依本法第120、121條所虧欠占有人的費用,且補償必須于移交文物時支付。在荷蘭加入1970年公約后,《荷蘭民法典》增加了同樣關于適用善意取得規則的第3編第86b條,規定了對基于公約主張所有權之權利人的特別保護。〔48 〕與此同時,在受讓人已盡審慎義務情形下的合理補償仍是題中應有之義,對于盜贓物場合的例外規定,以及對于補償范圍及時間的說明,也與第3:86a條保持一致。〔49 〕
基于上述介紹,《荷蘭民法典》上對于善意取得的構成,主要規定了“對價”、“買受人為善意”、“交付”三大要件,這與不少大陸法系國家對于善意取得要件的規定并無不同。除此之外,《荷蘭民法典》清晰地展現了立法者對于盜贓物是否適用善意取得的態度——不同于德國法否認盜贓物之善意取得的立場。荷蘭法與法國法類似,均認可適用善意取得的可能性,只是所有人有三年的時間可以重新主張所有權。〔50 〕這三年的時間可被認為是“等待期”。不過,“等待期”的規則在買家并非專業人士,且于專業賣家的營業場所購得標的物時并不適用。亦即,這種情況下的買受人可依善意取得制度的一般規定,直接繼受取得所有權。〔51 〕
回到本案,荷蘭藏家1996年在荷蘭具體的交易情況我們不得而知。可能導致法律評價結論發生變化的幾個關鍵事實,包括該藏家“是否支付了對價”、“是否接受了移轉占有”、“是否善意”、“是否消費者自經營者處購買”等。其中,關乎盜贓物的最后一項已無討論必要——因為不管是否適用“等待期”規則,結論在佛像獲得于1996年的語境下已毫無意義。針對“對價”、“交付”、“善意”三大要件而言,“對價”與“交付”恐怕皆無懈可擊,唯獨“善意”一事可再細究。值得一提的是,國內有些文獻提及了買受人的審慎義務,認為“要求作為文物商的購買人必須盡到盡職調查義務,否則不能稱自己為善意購買人”。〔52 〕不過,調查義務并不完全等同于審慎義務,前者主要是在一定場合用以判斷善意的構成;而《荷蘭民法典》規定審慎義務的第3:86a、86b條,卻只是針對受《歸還文物指令》、《文化遺產保護法》以及1970年公約保護的善意受讓人而言,在已盡審慎義務的情況下獲得合理補償。其中前兩項法律對于文物有明確的界定,本案所涉之肉身坐佛,以及作為原所有權人的村民集體并不在上述兩部法律的保護范圍之內,而1970年公約的溯及力問題則使第3:86b條也無用武之地。〔53 〕
就“善意”這一要件來說,幸好,《荷蘭民法典》第3:11條提供的定義為阻卻其構成留下了一線生機——即對物上有他人所有權的合理懷疑便足以阻卻善意之構成。就本案的情形而言,藏家表示其知曉上一個所有人乃從香港入手佛像,而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的香港是我國文物被非法販運出口的主要中繼站,文物市場魚龍混雜、亂象叢生;此外,“肉身坐佛”這類文物因其特殊的形成過程與內藏祖先遺骸的重要意義,即便在文物市場上也幾乎不存在通過合法手段獲取的機會。這兩點加在一起,為推出“買受人在入手此類商品時,應存在合理懷疑”的結論提供了可能性。〔54 〕
然而,通過排除“善意”來阻卻善意取得制度的適用對于追索文物來說遠非足夠。這是因為,除了善意取得之外,還有一項《荷蘭民法典》上的法律制度,可能導致藏家在不滿足善意的情況下同樣可以獲得肉身坐佛的所有權——即上文所提及的時效制度。
五、具體規范之二:時效法
對于荷蘭藏家來說,其依善意取得獲得所有權的主張以受讓時的善意為前提。正如前文所述,相關客觀事實表明,想要排除一切對于肉身坐佛屬盜贓物的懷疑,似乎也不是那么容易。過分依賴于以善意為前提的法律制度,對藏家而言并非上策。事實上,《荷蘭民法典》也確實為他提供了另一種思路,即通過不以善意為前提的時效制度來獲得所有權。
時效制度中與本案有關的條文同樣被規定在《荷蘭民法典》第3編。根據第3:99條第1款,對于非登記動產及票據權利來說,若占有人為善意,則在其不間斷地占有物三年后,可獲得所有權;對于其他財產,該期間則為十年。第3:118條第1款在第3:11條的基礎上對“善意占有人”進行了界定,即合理信賴自己是所有權人的占有人。該條文同時規定,一旦占有人被認定為善意,則該狀態具有持續性。〔55 〕此外,占有人的善意是推定的,不構成善意則需要證明。〔56 〕與涉及善意取得的條文類似,第3:99條第2、3款規定,此規則對文物并不適用。非常遺憾,此處所謂“文物”,仍有前文提及之范圍限制——即只有《文化遺產保護法》、《歸還文物指令》、1970年公約所明確保護的文物,在適用限制條款的保護范圍之下。
倘若占有人非為善意,則有第3:105條、第3:306條的適用空間——前者規定,占有人即使非為善意,仍得于因時效期間屆滿而導致終結其占有的訴權 〔57 〕消滅時,獲得所有權。對于“期間屆滿而引起訴權消滅”的時效而言,第3:306條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以外,訴權在二十年期間屆滿后消滅。根據學者的觀點,這種語境下的“二十年期間”其實包括了取得時效與消滅時效兩種制度。其重點在于,實踐中存在下述可能性:消滅時效期間屆滿導致重新主張所有權的訴權業已消滅,但是取得時效卻有可能由于沒有占有人而并未啟動,因此原所有權本身并沒有消滅。〔58 〕
對于消滅時效的起算來說,《荷蘭民法典》在第3:306條以下對各類請求權適用的時效類型進行了分別規定。其中,第3:310a、310b及310c條規定了文物返還語境下的時效問題,不過仍然與其他對于文物的特別規定一樣,這些條文的適用范圍僅限于《歸還文物指令》、《文化遺產保護法》及1970年公約所保護的文物。第3:314條第2款則是對所有權返還的時效規定,根據該條文,對于終結欠缺所有權之人的占有狀態而言,該訴權對應的時效期間應起始于該人成為占有人之后的那一天,或是能夠主張該持有占有狀態應立即停止之后的那一天。
對于這則條文的理解,需要結合前文所介紹的“被盜名畫案”一同進行——該案不僅具有國際私法上的重要意義,同時也是荷蘭司法史上關于時效最重要的判例之一。在“被盜名畫案”中,原告主張舊民法典中“時效應自原所有權人非自愿喪失占有時開始計算”的規則不應適用。其理由在于,法律最基本的合理與公平原則決定了,消滅時效的起算不應早于權利人有能力主張其權利之時。但是,這樣的觀點并沒有得到荷蘭最高法院的認同。最高法院認為,荷蘭司法判例早已確認,重新主張所有權的時效期間,應開始于“原所有權人之外的其他人對物實施占有行為”。換言之,上述期間的起算并不取決于原所有人知曉其應當向上述提及之“其他人”重新主張所有權的時點。雖然有反對意見認為,如此一來原所有人的權利甚至可能在其有能力主張之前已告消滅,但是,這種價值與法律的確定性相比,不具有決定意義,而法律的確定性恰恰是時效制度所意圖達成與要求的。〔59 〕
顯而易見,這樣的立場得到了現民法典立法者的認同——對于消滅時效期間的起算來說,原所有人的主觀狀態毫無意義,期間的起算唯獨取決于所有人之外的其他人開始占有物的時點。事實上,消滅時效不考慮權利人主觀因素的立場。在各國立法例規定最長消滅時效的條文中并不罕見。〔60 〕值得注意的是,消滅時效與取得時效的分立,也使該“其他人”是否是“可依取得時效獲得所有權的占有人”的判斷不再重要。換言之,即便現占有人乃剛剛接手失竊數十年的盜贓物,甚至現占有人就是竊賊本人,他仍有可能根據第3:105條,在原所有人的訴權因時效期間屆滿而喪失時,立刻獲得該物的所有權。由此,第3:105條也被認為是具有“竊賊變身所有人”效果的法律條文。〔61 〕
在這樣的語境下,“如何有效中斷時效”對于原所有人來說便顯得至關重要。《荷蘭民法典》中關于時效中斷的條文,被規定在第3編第316條以下。其中,第3:316條主要是關于通過啟動訴訟或其他司法程序的方式中斷時效,該條文第1款特別提到,以此種方式中斷時效須由原權利人為之。第3:317條第2款則說明了非主張履行債務的債權人的其他權利人,亦可通過發送書面警告的方式中斷訴訟時效,但在此之后的6個月內,仍應啟動本法第316條規定的司法程序。而第3:318條則規定,對于訴權所保護權利的知曉,能夠中斷向該知曉者主張的訴權的時效。在這三則條文中,第3:318條與財產權相關,但其中斷的對象,以條文之的文意來看,應屬善意占有人的取得時效,在占有人非善意的場合恐怕并不適用。
回到本案。在所謂財產權保護“動的安全”與“靜的安全”中,荷蘭法明顯傾向前者。雖然與善意取得一樣,荷蘭藏家欲主張取得時效則必須面臨“善意”要件的詰問,但是取得時效并非荷蘭藏家在時效法領域的唯一選擇。申言之,消滅時效期間的屆滿將導致《荷蘭民法典》第3:105條的適用——一旦自失竊之日的第二日起滿二十年,陽春村村民作為佛像所有權人在荷蘭法上的訴權將歸于消滅,而荷蘭藏家作為其占有人將直接獲得所有權。幸運的是,如果確如村民所說,佛像失竊于1995年12月15日,則二十年期尚有數月方才屆滿,在此期間仍有中斷的余地。那么如何在2015年12月16日前依《荷蘭民法典》相關條文中斷時效,則成為目前追索文物的又一關鍵。
以下,筆者將結合目前為止所有由私法路徑出發而作出的分析,就追索肉身坐佛進一步提出實踐建議。
六、追索肉身坐佛的實踐建議
考慮到我國學界對于荷蘭法相關規定的介紹相對單薄,筆者之前的分析框架主要是由私法路徑的基本邏輯入手,圍繞著《荷蘭民法典》上的條文、相關判例,逐步探討了追索肉身佛像過程中的重要法律制度。而在本章中,筆者將以這些制度為基礎,進一步探討追索佛像所涉及的一些周邊問題,并提出更具可操作性的實踐建議。
如前所述,如果我們的目標是根據《荷蘭民法典》上的條文,以主張所有權返還的方式追索肉身坐佛,那么“系爭物件確為被盜文物”、“起訴主體確為所有權人”,是須以關注的兩大基本前提。
就前者來說,就是首先需要證明,荷蘭藏家所持有的肉身坐佛,就是陽春村丟失的“章公六全祖師”全身佛像。〔62 〕這一點已經有法官在撰文中提及。〔63 〕而就目前的情況而言,國家文物局有關人士對此也釋出了積極信息,認為“現已基本確定該‘肉身坐佛’就是大田縣陽春村1995年被盜的宋代章公祖師像”。具體來說,除了其化身享年與西方研究結論相符,主要證據還包括當地遺存的照片、族譜、衣冠、坐轎等證物、相關證人證言,以及章公祖師誦經修行之地留下的佛子格、佛插記等遺跡。〔64 〕有報道稱在匈牙利與佛像一并展出的還有一個完整的坐墊,上面則清晰記載了“章公六全祖師”的字樣,〔65 〕同時也有照片證明這一點。此外,村民提出佛像修補痕跡、頸部裂痕可供核實,佛像上的字跡可供比對,〔66 〕這些信息可以說對證據提供極有好處。
就后者而言,則包括兩層含義:這不僅涉及到訴訟主體適格的問題,也涉及實體法上若干制度的具體效果——正如先前所介紹的,根據荷蘭法,只有所有權人能夠主張所有物的返還,且中斷取得時效者,亦須為所有權人。因此,通過上述提及的證物及證言,證明陽春村村民系肉身坐佛失竊前的所有權人,同樣至關重要。〔67 〕值得一提的是,陽春村村民在我國《物權法》與《文物保護法》的語境下屬于集體所有權人,〔68 〕對文物享有所有權,并不存在疑問。不過荷蘭法所有權體系中并無集體所有權一說,這種所有權形式可能會被看成共有的一種。根據《荷蘭民法典》第3編第171條第1款,任何共有人都有權啟動對所有共有人而言均帶來收益的司法訴訟,或請求司法裁定。因此,欲啟動追索肉身坐佛的司法程序,由作為共有人的任意陽春村村民提起訴訟,均屬適格主體,同時也能實現中斷消滅時效的效果。
除此之外,針對“善意取得”制度與“消滅時效”制度的兩大核心問題,“善意”及“喪失占有之日”同樣需要給予特別關注。
就“善意”來說,荷蘭藏家稱其已有近三十年的收藏中國藝術品的歷史。換言之,在入手佛像前收集中國藏品亦有十年之久——在這樣的語境下,面對來自香港的肉身坐佛,對該藏家在交易當時“是否足以產生合理懷疑”的論證,將是判斷是否存在“善意”的關鍵。就此而言,雖然難度極大,但絕不可忽略。對于“喪失占有之日”而言,如前所述,荷蘭法上消滅時效的起算期間開始于原所有權人喪失占有,因此喪失占有的日期愈晚,訴權消滅的時間也便愈晚。倘若如荷蘭藏家所主張,文物1994年便出現在香港,〔69 〕那么二十年的消滅時效期間便已屆滿,即他已經可以主張依據《荷蘭民法典》第3:105條而獲得所有權。因此,“文物確于12月15日失竊”,對于這一點的證明同樣關鍵。〔70 〕對此,我國專家指出,需要證明這一事項,則最好能“搜集到當時被盜后的出警記錄、警方勘查記錄,及被盜前后關于宋代章公祖師像同一角度的清晰照片”等等。〔71 〕這樣的觀點值得肯定。〔72 〕考慮到荷蘭法上的具體規定,陽春村村民作為所有權人被證實仍然占有佛像的時間越晚,為追索文物留下的行動余地就越大。
結論及余論
綜上所述,筆者得出結論如下:首先,肉身坐佛屬人類遺骸類文物,我國福建省陽春村村民的追索行為在私法上屬于行使基于文物所有權的返還請求權。其次,就此類法律關系而言,作為文物所在地的荷蘭法院具有管轄權。根據《荷蘭民法典》第10編的沖突規范,荷蘭法應得適用。第三,雖然在荷蘭法的語境下有1970年公約、《文化遺產保護法》、《歸還文物指令》等保護文物之制度的適用空間,但本案肉身佛像并不在上述立法的保護范圍之內,故能夠適用的只有《荷蘭民法典》上的規則。第四,行使所有權返還請求權的前提,在于作為占有人的荷蘭藏家還未取得所有權,因此首先需要阻卻善意取得制度的效果。根據《荷蘭民法典》第3編相關條文的規定,荷蘭法上的善意取得適用于盜贓物,且須滿足“交付”、“對價”及“善意”三大要件。其中本案陽春村村民所可能主張的,只有藏家購買時,因存在合理懷疑而不構成“善意”。第五,即便藏家不具備善意,但其仍可依荷蘭法之時效制度在所有人訴權消滅時獲得所有權。根據有關規定,該消滅時效之期間自原所有權人喪失占有的第二日開始起算,該期間為二十年。故陽春村村民欲追索所有權,則應在期間屆滿前通過提起訴訟等啟動司法程序的方式中斷消滅時效。
結合上文的法理分析,追索過程中必須證明以下事項:(1)系爭佛像系失竊文物;(2)陽春村村民系該佛像所有權人;(3)司法程序確由陽春村村民啟動;(4)荷蘭藏家入手佛像時不具善意;(5)佛像失竊次日至啟動追索程序時尚不滿二十年。
當然,通過啟動跨國訴訟等私法途徑肯定不是追索文物的唯一路徑。現有文獻中已有不少提及,政府間的交涉恐怕是更方便、更實際的解決辦法。〔73 〕此外,也有我國著名古董藏家在傳媒節目中分析,認為若陷入訴訟,由于取證等問題曠日持久,恐怕荷蘭藏家需要支付的訴訟相關費用就會遠遠高于其當初購買時所支出的費用。〔74 〕而這一點,對于作為所有權人的陽春村村民同樣適用——訴訟所帶來的高額成本,恐怕也是不得不考慮的問題。所以動用經濟手段,由有關人士或善人進行回購,也是可行手段之一。
不過,友好協商也好,外交斡旋也罷,知己知彼方能百戰不殆,不管追索文物最終采何路徑,如果對訴訟適用的相關法律制度不進行一番了解,則會使得該權利主張陷入困境或茫然之中。更何況,這些法律規則背面,往往蘊含了人們業已形成共識的價值考量。
比如,據荷蘭當地媒體《NRC Handelsblad》的報道,肉身坐佛現收藏者表示,如果能夠證明其占有佛像確系陽春村失竊佛像,他愿意將佛像歸還陽春村。不過,他只會在佛像原先所在的村落追索時歸還,而不會將之歸還于我國的國立博物館。〔75 〕這一點和荷蘭法上對于“主張所有權以及中斷消滅時效須以所有權人本人行使為前提”的立場完全一致。此外,《荷蘭民法典》上對于已盡審慎義務的買受人亦持應予補償的態度,雖然這些條文在訴訟中未必能得適用,但其中精神值得在追索時遵從——既然對方已釋出善意,自有禮尚往來的道理。對方為修復、研究佛像已有不少支出,對于這些費用的補償也應當在我方權利人考慮的范疇之內。〔76 〕
最后,一則看似無關的新聞,也值得權利人關注。阿姆斯特丹阿拉德·皮爾遜博物館近日面臨兩難境地:他們在“克里米亞危機”之前從克里米亞博物館借來展覽的考古發現,現在遭到了來自烏克蘭與俄羅斯所控制的克里米亞兩方面的歸還請求。可他們并不確定應當向哪方歸還——這是因為,不管還給誰,恐怕都會帶來后續的一系列棘手難題。由荷蘭人的視角看來,歸還文物的過程中,如何規避可能的法律及政治風險也是必須被納入考量的因素。如果我國陽春村村民以及背后的智囊團,能夠將這類顧慮也照顧周全,無疑將再度增加追索成功的幾率。
讓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