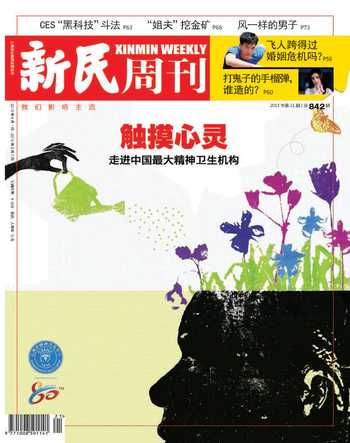養老機構與老人收容所
劉洪波
5月25日夜晚,河南平頂山市魯山縣一個老年康復中心發生火災,導致38人死亡。這一重大慘劇,足可作為防火安全警鐘長鳴的最新例證,但應該引起的思考絕不能止于此處。
發生火災的老年康復中心,有床位200張,年檢結果合格,法定代表人曾被評為道德模范。不出事故,它完全是養老事業的一個樣板。但現在出了事故,我也不準備說它就特別惡劣。老人在這里住的是鐵皮板房,安全保障肯定也確實大有問題,但這家民辦養老機構的主持人被評為道德模范,定然比類似機構更好,甚至它可能是當地民辦養老機構的獨苗,而社會投入養老產業是個鼓勵方向,因陋就簡先辦起來,可能也符合政策。
我們正在進入老齡社會,“老年”本身卻不僅成了社會問題,而且成了人生問題。從社會問題來說,老年人的增加帶來了社會活力、養老負擔、資源分配等多方面壓力。從人生問題來說,“老年”已經成為負面意義的人生階段,步入老年意味著人生意義的降低,這是前所未有的。今日討論養老問題,很大程度上是作為社會問題、經濟問題對待的,而被“養”的老人的人生意義未被認識,也就是說,人們看到的只是老年社會的危機,而沒有注視過老年人生的危機。
傳統上,在中國,步入老年,意味著人生進入收獲期,德高望重,而且在子孫滿堂和兒孫繞膝中體驗到幸福,這賦予人生晚境以一種“大成”的意義。現在,情況變化了,子孫滿堂很大程度上不可能,兒孫繞膝已因社會節奏的加快而可能性降低;人生幸福已從兒孫鏈條中剝離,由生死一場的個人來定義,老年就成了接近終點的悲涼階段,而且新的人生觀共識是對老年進行貶義化的,老年人因創造價值或為社會作貢獻的可有性降低而不再獲得贊譽。無論從社會共識還是從個人體認來看,老年都失去了幸福的依據。
老年人體弱,容易多病,這是客觀事實,但更重要的是,“老年”本身已經被視為一種疾病。人生的階段,童年代表成長,青年代表未來,中年意味著忙碌的付出和相應的回報,老年則意味著退場和成為負擔。誰能成為人生幸福的體驗者呢?幾乎沒有,人們或在為報酬而做艱苦的準備,或在為獲得報酬而辛勞因而無暇體驗收獲的幸福,而到了老年,人們就被拋進“無用”者的行列。
今天,我們講到養老機構,頭腦中出現的其實是一個“老年人收容所”。那里將老年人收集起來,被收進養老機構的人是同類項,都在預備人生終點。人們頂多關心那里吃喝怎樣、醫護如何、是否虐待老人、有沒有電視或者高級一點有沒有網絡,但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養老機構是一個社會嗎,老年人在那里能夠“社會化”嗎,老年人集中在一起會產生怎樣的人際問題、心理問題?這就不在一般考慮之中了。
養老機構的第一指標是“床位數”。這個概念,跟人們說到醫院或旅店時是一樣的。這就是說,老年人進入養老機構,那里并不是家,而是醫院或者旅店。人們不是該住在家里的嗎,為什么人到老年反而失去了住在家里的資格呢?大家都認為老年人入住養老機構是一個方向,大家的共識是人老了,就應該住進養老院,不該在兒女面前添麻煩,兒女們很忙很辛苦,出錢送老人進養老院就夠了。在這種共識下,老年問題順利地變成一個經濟問題。由此,老年這個人生的夕陽階段就順利地架起了作為朝陽的養老產業。
老齡社會不可逆轉地到來,老年是什么,老年人是什么,原應得到深入認識,但現實是認識更加淺表化了。將老年人從社會中抽出,將老年從人生意義中抽出,視老年類似垃圾時間,將老年人集中收容于養老院,就成為讓其他人更有效率地工作和生活的社會保證機制,而且具有商業開發價值。這就是價值規律在人生上給出的答案,其荒謬性并不因這種命運人人不免而減弱。